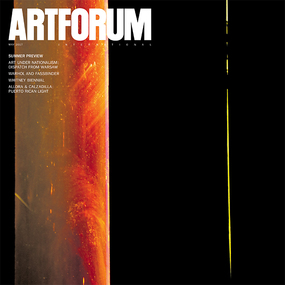迪拜在全世界的文化想象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很多人眼里,它是终极的“无处之处”,是极端失真之地,空洞的全球化现身之所,纯粹的资本在这里凝固为玻璃和钢筋。驱散上述陈词滥调是住在这里的人最喜欢的消遣,他们知道,这座城市多语种混杂的特征——住在迪拜的外国人比例高达83%——常常构成新身份的基础。
对于生在华裔家庭、在迪拜长大的艺术家谢蓝天而言,这座城市的混杂性是一座素材的宝库。他在装置、手稿和素描作品中质询记忆、公民身份与社会性之间流动的互动关系。迪拜成为了一个理想的主题:“在这里长大,”谢蓝天说,“我周围不是旅居海外的阿拉伯人就是旅居海外的西方人。再没有别的方法描绘住在这里的人了。”这既是一个观念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谢蓝天这一代的居民虽然从小在阿联酋长大,却没有这里的永久居留权,因为该国的公民身份及其伴随福利几乎仅限于阿联酋家庭出身的子女,移民很难拿到,就算你从一生下来就在这里生活也没用。对国籍身份的这种严格控制决定了阿联酋内部深刻的不平等,哪怕由此形成的社会肌理远比很多西方观察者能够想象的更加错综复杂。
谢蓝天用迪拜过去的历史让人看到,起源和真实性是无法确证的。在最近科钦-穆吉里斯双年展上的装置作品《吊扇,野狗在叫,塔》(Ceiling fans, stray dog barking, burj Ali, 2016)中,他放了一张素描图,上面画的建筑看起来好像是迪拜著名的阿拉伯塔朱美拉酒店(又称帆船酒店),实际上却是旁遮普邦的一座模仿该酒店外观改建的农舍。在为海湾地区提供了大量劳动力的北印度,帆船酒店俨然已成为财富与成功的象征。阿拉伯塔朱美拉酒店也以幽灵般的形式出现在了谢蓝天之前的系列作品“芝加哥海滩酒店”(Chicago Beach Hotel,2014–15)里。回溯该酒店建筑历史的两张素描图刻画了1893年为风城(芝加哥)世博会参观者而建造的豪华酒店(现已拆除)。阿拉伯塔朱美拉酒店问世之前,其所在地有过一座同样名为“芝加哥海滩酒店”的建筑;之所以叫“芝加哥海滩”,是因为给当时繁荣发展的石油业提供基础设备的芝加哥桥梁与钢铁公司往海湾地区运送钻探设施就是通过这片海滩。那座酒店同样也早已被拆除,“芝加哥海滩”变成了“朱美拉海滩”,只有极少数人还记得这段前史。
对口述记忆的这种珍藏和铭刻多少带着一点儿感伤色彩,但上述作品同样讨论了阿联酋内部严重的分裂:一边是官方叙述——内容大多来自城市品牌建设和文化遗产组织,其关注重点往往仅限于阿拉伯文化——另一边则是住在此处的人们体验到的文化现实。谢蓝天常常把一个地方不可见的种种特质置于作品的中心位置:比如,照明或气候。2014-15年,他在迪拜Grey Noise画廊的个展“Hassan Matar”上展出“芝加哥海滩酒店”系列时,展览照明就用了当地南亚和东南亚移民合租房里最常见的惨白的日光灯。在《吊扇,野狗在叫,塔》中,科钦地区典型的老式吊扇保持着展厅内部的空气流通。温度和照明里都是政治:大多数人还是享受不到中央空调的凉爽和白炽灯灯光的温柔。
谢蓝天关注酒店,也是因为在一座由于气候和习惯双方面原因而缺少街道和广场设施的城市,酒店大堂变成了某种公共空间。同时,作为阿联酋少数能喝到酒精饮料的地方之一,它们也表明,迪拜为兼顾阿拉伯身份和全球标准两边所做的尝试实际上矛盾重重,暗示迪拜著名的世界主义在部分意义上终究流于表面。迪拜在世博会和贸易展会上经验丰富;那里的“地球村”像艾波卡特中心一样搜罗了全球各地标志性建筑缩微模型,在当地一直人气很旺。然而,谢蓝天提醒我们,国际主义始终都要经过本土的中介。《大都会酒店》(Metropolitan Hotel, 2016)系列由十五张素描组成,画的都是遍布世界各地(从新泽西到宾州,从开罗到迪拜)的同名酒店;尽管酒店名字完全没有显示任何在地性,但每座建筑本身的风格都明显带有所在城市的地方特征。
谢蓝天将代表阿联酋参加本月即将开幕的威尼斯双年展似乎合情合理。他为阿联酋馆展览“石头,剪刀,布:活动位置”(Rock, Paper, Scissors: Positions in Play)所做的作品题为《一段杂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A rumble interrupted our chat):艺术家写下剧本,安排一群由他本人挑选出来的参与者每天的活动,比如早上在咖啡馆的聚会或者晚上在实习生公寓里的派对。这件作品探讨了个体与其所在城市肌理之间的关系,检验了有关居住和互动的标准及预期。
谢蓝天的工作并不仅仅是为了确证本土知识,还暗示了这一知识跟拥有它的人不能分开,就像一段不应该,或者不可能暴露的密码。他的叙述实践中一个反复出现的物件是Hassan Matar——这种在迪拜无处不见的三明治完美地体现了此地身份中的多重矛盾:“每家咖啡馆的做法都不一样,”谢蓝天告诉我:“没人知道Hassan Matar到底是谁!”
梅丽莎·葛朗蓝德(Melissa Gronlund)是一名现居阿布扎比的作家,也是《当代艺术与数码文化》(ROUTLEDGE, 2016)的作者。
文/ 梅丽莎·葛朗蓝德 | Melissa Gronl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