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一年一度的“艺术北京”如期而至,但当日去博览会看作品兼顾社交的人群明显被“分流”:一部分人被林冠画廊傅丹(Danh Vo)个展的开幕所邀请,去Temple吃高大上的晚宴,另一部分人则在为稍晚艺术家张鼎于香格纳北京空间的“一场演出”做着摇滚的准备,故在家养精蓄锐。继而,这种分众效应所影响的不只是“2014艺术北京”,当晚整个北京艺术圈的人流都似乎在“多”与“少”之间进行着某种颇有意味的涌动。
在博览会现场“难得”见到一家韩国画廊(PYO GALLERY),展位里摆出了金准植(Kim Jun Sik)在高丽纸上画的照片级写实油画,其中一幅将“喜羊羊”同“猫和老鼠”放到了一块,虽然两者都是扭曲儿童世界观的好伙伴,但看后还是令人捧腹外加不寒而栗。与画廊工作人员几分钟的聊天里,免不了谈到韩系画廊的生存现状,高频词都是“都走了”,“也快了”,以及“那他们去哪了呢”,“他们去了另一个地方”。凯撒贝塞什(亚洲)艺术中心占据两个展位,入口处在播放蒋志的“阿娇”录像。后来听一位艺术家介绍说,这个具有地中海古典名称的艺术机构其实是做新工笔起家的。“以前做新工笔,当时还比较便宜,运气好,收了不少,现在再做点别的。”由于我们的对话中多次用到“做”,而这种“做”又能在“艺术北京”上找到相应的现实结果,故而排比的听觉快感使人产生了造句的冲动:博览会上,机构(画廊)可以做一批作品,可以做一批艺术家,也可以做一批作品以及艺术家;既可以做艺术家的作品但不做艺术家,也可以不做任何作品只做艺术家。

碰到杨画廊的金澎,不禁问道:“杨画廊怎么没参加?”答曰:“杨洋想要那种大的,两个展位的,但是没给到位,就算了,我们去香港。”真有趣,大家见面都说去香港,香港目前是迈阿密,不过你赶得上17日下午飞往上海余德耀美术馆的飞机吗?碰见马芝安(Meg Maggio)后与其兴奋的聊起艺门北京空间最近的两个展览。马芝安称赞余力为和赵亮“super smart”(很聪慧),“他们全自己拿主意,不需要我们的帮助,看当时那地上的灯光打得有多棒。”转到最后,注意到的依旧是:国外展商看起来只有一成——“艺术北京”前三届有一半的展商都来自国外),不过这几年这种“墙外不开花”的情况大同小异。外资画廊还在爱北京,但内心里也许已经默默的绝交了。而一些本土展商平时听不到什么响动,仿佛永远在“后台”开展着工作,但一到“艺术北京”就齐齐出现,看起来海外与本土势力似乎都在玩着“在”与“不在”的游戏。
九点坐上从“艺术北京”开往香格纳画廊的免费大巴,到达时刚好赶上第二支乐队的演出。张鼎这回“一场演出”的现场比2011年在H空间的“开幕”还要牛,稍微瞟一眼,估计现场至少有上千观众。“艺术北京”的人越少,这儿的人越多。“这儿的人还不够多,”中场时,张鼎帅气的表示,“颜峻帮我找到了刘立新,军械所乐队的吉他手,然后老刘就帮我介绍了这些乐队。”看起来这些乐队的粉丝也来了,表演时唯一在台下叫嚷的大概就是这些粉丝,“就是这儿的观众,都太温了,太温了。”
远看墙上好似挂有巨幅绘画,但“这个跟音乐很有关系”,因为它们是有烧灼痕迹的吸音海绵。等这个开幕结束了,“大家就看这个现场,这个舞台,还有(今天的)录像。”张鼎为现场做了吸音板,灯光,舞台,包括舞台上的异形音箱。不速之客乐队的主唱Voolcanoo(杨子)在休息时向我科普了几句:“这是在复制1991年莫斯科的那场演出,我们翻唱的是黑乌鸦(THE BLACK CROWES),属于(美国)南部摇滚。当时那场演出很轰动,苏联刚解禁,但还是有很多军队参加到保安工作,现场有直升机和坦克,观众和国家的军队有些冲突。”

张鼎在和陆兴华的聊天中讲到:“我俩在多次的交流中逐渐发现颜峻是个谈判者,我是个制片人。”在此处,策展人(颜峻)和艺术家(张鼎)似乎真正达到了可以交换身份的地步,这也在于颜峻为这个展览的发生做了不少实质性的工作。专程前来看展的陆兴华说道:“这演出很残酷的,他们(乐队)会感觉不舒服,美术馆(画廊)就是压迫演出的,就把它当‘作品’一样来放,”但好在“颜峻和张鼎跟他们好好沟通过,这也是重金属摇滚乐和当代艺术的首次跨界,有意义。”他又补充道:“国外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美术馆最终会走向哪里?如果只能提供party就太文明了,有时需要一些具有反抗性的表演才能在今天立足,所以美术馆需要这样一些乐队来为自己辩护——我是重要的,我是可以成为广场的。”如今众人欢聚一堂意淫那场遥远的演出,除了耳朵麻木之外并不会激活我们“复仇”的欲望,将画廊变成公共空间的努力一直在当代艺术家中持续着,但这种从原生地移置来的表演并不会轻易地将残酷变幻为“高大上”,也难以使超正经的白墙画廊(美术馆)变得像草地一般开阔。颜峻在名为《金属不死》的前言里讲到:“是说占领美术馆吗?这大概并不是张鼎的本意。没有了美术馆和画廊,他靠什么生活?格罗伊斯和所有的汉斯,靠什么生活?何况那些披着大长头发的黑衣人,哪里都不会去占领……”最终占领美术馆的还是艺术家张鼎,没有张鼎的艺术家身份,这事也成不了;而美术馆(画廊)也只能留给艺术家来占领。尴尬的现状是:艺术家需要通过不断变换方式来持续重新占领美术馆(画廊),美术馆(画廊)则在被不断被占领中默默提高或改变对艺术家的门槛要求。艺术家与美术馆(画廊)的攻受关系在不断互换,过程中也许能达到彼此提升的效果。不过,怎么听起来像艺术家与美术馆(画廊)之间在共同布置一个长期的、大范围的、“变态”的局?但也许并不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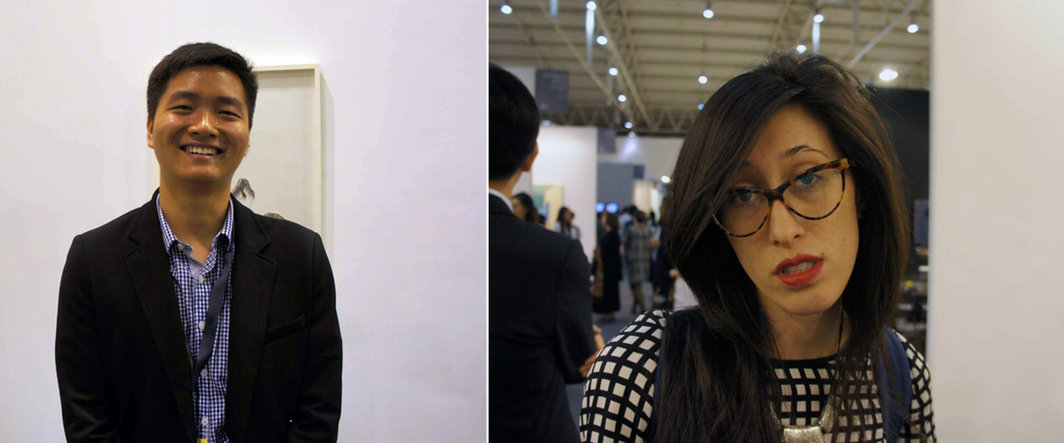
文/ 陈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