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看到乔希•布兰德(Josh Brand)那些大小适中构图简洁的作品,人们不禁对这些作品是如何制作完成的而产生兴趣:作品的那些抓人的色调浓淡度和对比性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实,和他的同代人如里兹•德舍纳(Liz Deschenes),马库斯•埃姆 (Markus Amm),艾琳•昆兰 (Eileen Quinlan),沃夫冈•提尔曼(Wolfgang Tillmans)一样,布兰德在创作过程里,不过是运用了一些自创的花招。更特别的是,他采用的是眼下正慢慢被数码摄影取代的暗房和冲印技术,这令人想起了九十年代,艺术家一度回归16毫米胶片,因为其产生的质感和形式与数码录像是不同的。布兰德采用了这些神秘的技法却又对其进行了再创造,探讨了那些似乎是反本能的抽象和摄影方法。
布兰德曾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学习电影与摄影,2003年毕业后,他来到了纽约,在不同的洗印室做商业冲印工。下班后,他就将工作之地变成即兴创作的暗房,从那时起,布兰德开始以简单的姿态和开放式的构成模式进行试验,一切得归功于他对音乐上合作的兴趣,慢慢的,他创作了很多与序列性和记录性的常规摄影不同的作品。
布兰德独特的图片作品(几乎都未命名),几乎都是快速完成的,而没有使用照相机,通过快速的曝光,勾勒出了感光面的一部分。他通常使用的都是身边唾手可得的东西,比如一个盒子,一片柜子碎屑,一张纸等等,根据手头的物品和感光面的关系进行不同层次的表达,他把这些材质贴近光面划出一道痕迹,或者将某件物体悬浮其上,形成若隐若现的阴影和可感觉得到的色泽浓度。
布兰德的这些分布着轨道线的作品表现了一种行为上的即时性和对桌上摄影的敏锐性,它们既多重复杂,又充满隐喻性和游戏性:红色与亚麻色相间的图案打造出了一个现代主义的图像,半透明的光则令其免于刻板;在对汉斯•阿尔普(Hans Arp)即兴拼贴画的模仿中,光的线条通过打孔的纸泛起了涟漪;曝光步骤仅两步,却勾勒出了某种构图考究的浅紫色和蓝色图案,这种形状人们可以在包豪斯大师约瑟夫•亚伯斯 (Josef Albers)的色彩实验图中看到;四条裂缝又将一张相纸单一的黑色分裂开来,这明显是对鲁西奥•芳塔纳(Lucio Fontana)的致敬;一只暗哑的桃形轻易地就扭曲了画面上的图形和背景。

布兰德的另一类作品令他的即时创作复杂起来,这些作品倾向于一种对阴影的把玩,层层的光泽和特别的几何图形随着时间的发展偶然地出现在了纸面上。在这些作品中,空间上的位置并不确定,感觉上的模糊性加重。例如,绿色、粉色和红色的阴影就好像是乱画出来的或随意弄脏的一样,背景被弄得一片晦暗,从观众角度去看,一个不完整的长方形向别处倾斜。
分成三角形的交叉线将头图旋转般地向上拉起,看后人不禁产生短暂的眩晕感。
客观的存在与心理上的影响之间的不一致与布兰德的创作过程紧密相关的,他将感光纸放到室外,暴露在自然光和人工光的下面。于是,纸面甚至不用进入暗房就可以捕捉到逐渐模糊的、层层重叠的光线。跟油画上料的工序一样,这些底材通过日常的必然与偶然而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动,与外界产生更深的联系,在接下来的多重步骤中,产生出了一系列的效果。通过密触版印的变化和软化-将划痕暴露在光线下,在下面的纸上留下了痕迹—这种环环衍生的印刻方法,将印迹和阴影的细微差别逐渐显现出来。布兰德纵沟纹般的线条直接在相纸上刻画,根据特定的构图,在肯定和否定之间交错变换。无论是否运用暗房技术,布兰德将黑影照片和对彩色洗印配比的把握,使他模糊了客观的印刻和抽象的形状之间的界限。
这种黑影照片做为一种廓影,简单地被认为是一种摄影式的图片,把一件物体直接放到感光纸上,将其表面形态结构直接曝光。与下面的纸张无法直接接触的物体的任何部分,只需要侧面进针的光就可以投下影子。这种发展不完全的制作工艺作为一种十九世纪的创作方法在克里斯提•谢德(Christian Schad), 曼雷(Man Ray)和纳吉(Laszlo Moholy-Nagy)的艺术语境中被复原,如今又在布兰德的手中再次被激活,对无数晒印照片的勾画与转印,产生了近期那些具有动感的作品。《无题》(三,2008)表现了艺术家是如何将作品面向一种系列性的表达而转向电影可能性的。托布雷式的表面被漂白,被镌刻上刻痕和弧形碎片,以浅蓝色表现出来,然后通过旋转影响和与对比明显的阴影和色彩直接触印,进行转化。最终,产生出一部入闪烁电影的连续动作,两个画面被一张黑色照片上的黑点分开,形成一幅三联画,然后加入了过度曝光或洗印过程的“疏离”产生出的结构上的停顿。令人想起胶皮画幅中的间歇,也扩充了汉斯•雷切尔(Hans Richter),维金•艾格林( Viking Eggeling), 哈利•史密斯(Harry Smith)的DA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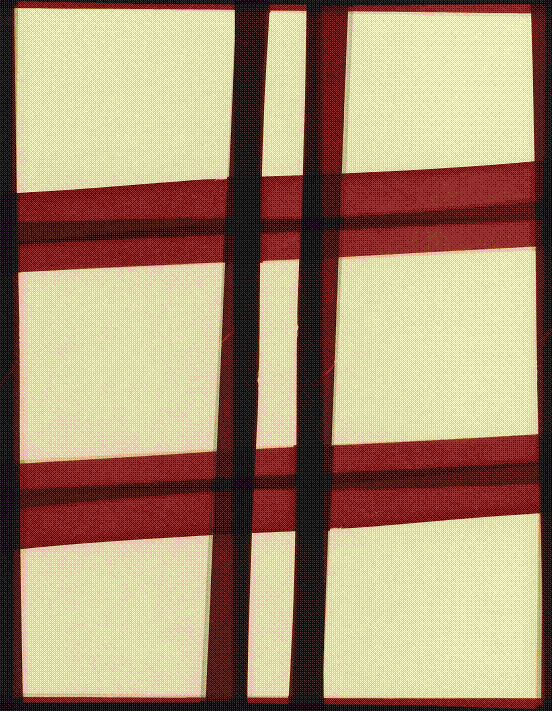
布兰德超越了单一的框架,将作品扩大化,很多照片呈现出了一种流动性。在另一部未命名的作品中,桌上台灯直接投下来的紫色光晕呈现了一种离心的旋转效果,跟杜尚的《贫血电影》(1926)似的,画面上方则全是一片黑色,使得这张图片就像画的一样。这是那一系列没有出现具体物体的照片中的一幅,表达了一个偏移而未决的现成品。《绿,黄,黑,白》(2008)中,双重的光圈为环绕着一片绿色进行运转,如宇宙的星际运动,在这件作品里,作者试图能将所表现的图像在实际生活中找到参照物。源于邻近角度的双重曝光镜头和常规洗印的过程,这种形状取自一个废弃大鼓的外形轮廓,搬家时,布兰德偶然注意到了它。挂在那里挂了几个星期后,大鼓的外形落到了纸上。
但是布兰德的方法并不仅仅限于一种完全依赖于黑影照片的观念性教条上。像詹姆斯•惠灵(James Welling)一样,后者多变的制作工艺已经产生了知名的Degrades系列(1986-2006),以及源于其他图片的抽象图,布兰德对形式上的拘泥是反对的,他有意采取了不同的技艺,由此产生更多更开放的选择性。同一个鼓轮廓的特写抓拍将半月的形状头放在了条纹化的背景上,浸染在玫瑰与青绿的笼罩之中。
在布兰德与画家理查德•埃德里奇(Richard Aldrich), 彼得•曼德拉杰夫(Peter Mandradjieff)和萨克•普利考普(Zak Prekop)这些人所做的项目排练空间中,一根九英尺长的棍棒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棍棒被拍摄下来,作为一根黄色的圆柱留下了纪念。起先,这根柱子用来支撑着天花板松动的瓦片,天光从中照射进来,后来,它很快成为小组的一个轻松的图腾,在他们工作室的墙边伫立了很久。
布兰德并未完全按照物体本来的形状进行描摹,他将柱子的阴面放大并洗印了两次,将带阴影的线条变成了抽象的图案。从演奏音乐时加长或缩短的时间中获得灵感,这件作品以光学将完美的旋转与空间的统一表现出来。在《光的年代》(1933)中,曼雷写到了他自己的“光线摄影图片”(rayograph), 布兰德的很多图片是从经验中攫取,“在感情交流时,在视觉分离的片刻被捕捉”。与曼雷对摄影证据确定性的微妙而强烈的回应是一样的,“对于所运用媒介接踵而至的违反破坏是作者最具信念的表现。对于所运用的材料的鄙薄是必须的…” 作为一种自动写作或潜意识的震颤,曼雷被摄影所吸引,而布兰德则在直接性和距离性,索引和抽象,标记和密码之间运用了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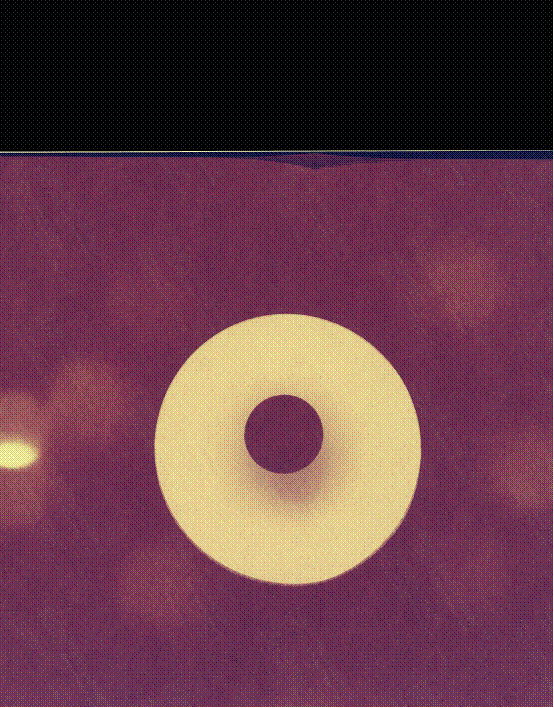
他对摄影洗印现象逻辑上的探索,可以说,是对摄影的挪用流传和图片复制的反抗。他的图片并非对后观念主义框架的反对,相反遵循着这一框架。布兰德的作品巧妙地从借用了现代主义的“忠于材料”的要求,对材料和摄影作品光学幅度之间操作上的张力进行着游戏。他的图片既不是对消逝景象的怀旧,也未忽略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光学上的衰退,而是在张力和引力着自如运转着,令人在视觉上从不感到厌倦。
作者菲奥妮•米德 (Fionn Meade)是纽约的批评家和策展人。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