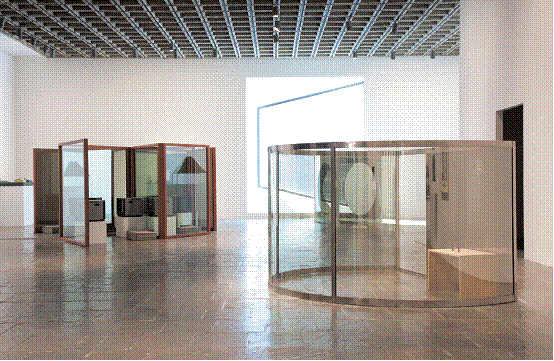
《丹•格雷厄姆:超越》2009展览现场、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纽约。
左起:《展示录像的空间》(1995)、《女孩的化妆间》(1998-2000)。
丹•格雷厄姆
在美国所有六十岁以上并仍然活跃的艺术家中,丹•格雷厄姆也许最受年轻一代的尊重。尽管他的名气从来不像罗伯特•史密斯森(Robert Smithson),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等同辈艺术家的那么大,但如今的格雷厄姆,如艺术批评家约翰•米勒(John Miller)所言,已经赢得了一群“回顾性质的观众。”为什么会这样?由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本内特•辛普森(Bennett Simpson)和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的克里斯•艾尔斯(Chrissie Iles)策划的这场出色的作品展“丹•格雷厄姆:超越”(Dan Graham: Beyond)就对该问题做出了充分解答。
如果说极少主义是战后艺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标志着独立绘画的现代主义范式完全终结,在社会空间调动真实的身体这一创作实践领域彻底打开,那么其潜力仍然有待进一步开发,而格雷厄姆和他的同行们完成的正是这项任务。(雷亚•阿纳斯塔斯[Rhea Anastas]在展览画册里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历史时刻。)“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对极少主义艺术的批判,”格雷厄姆在与艺术家罗德尼•格雷厄姆(Rodney Graham)的有趣访谈中(同被收入本次展览画册)指出,“它从极少主义艺术开始,但讲的是观众如何观察他们自己以及如何被他人观察。”因此他的作品多采用如下几种形式:两名表演者之间的互动;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反思自身诞生之空间的电影和录像;让观众走进隔间,镜像和/或录像里的装置;建筑模型;以及半透明反光玻璃做成的亭子。
对于格雷厄姆来说,需要质疑的第一个对象便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存在——极少主义过去似乎极力希望达到的目标。他通过不同作品展示了这种存在如何摆脱不了时间和运动,媒介和技术的纠缠,也无法忽略记忆的持续与他人的在场。尽管对极少主义影响至深的现象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曾经详细阐述过自我与形象,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差距,也讨论过他人在场所造成的离心效果(让-保罗•萨特和雅克•拉康有关他者注视的重要理论就以此为基础),但他有时也似乎承诺在“世界的血肉之躯”中能够获得一种存在的整体性。格雷厄姆向这一意识形态软肋发起了系统进攻。
举例来说,早在《投影仪项目》 (Project for Slide Projector, 1966/2005)里,格雷厄姆就对是否有可能与感知对象建立任何直接联系提出疑问。艺术家从多个不同的位置用不同焦距拍摄一组套在一起的玻璃盒子,得到的照片经过整理再用投影仪放出来。由于各个部分不断聚焦和失焦,成形的物体永远无法显现。在另一件为时一分钟的双屏投影作品《滚动》(Roll, 1970)中,格雷厄姆再次动用了上述主客体之间的不协调关系。两面相对的墙上播放着两部影片,一部是艺术家拿着摄像机在地上打滚,另一部是他打滚时拍到的东西——一段缓慢翻转的风景图。观众可以将两者联系起来,却无法缝合中间的裂隙。格雷厄姆通过他的行为,对话和装置作品(再次充斥着隔断,镜子和/或录像)进一步质疑了自我与他人对感官的透明性。其中最令人震撼的作品之一是《延时处理中互相面对的镜子和录像监视器》(Opposing Mirrors and Video Monitors on Time Delay, 1974/1993):两面覆盖整墙的镜子,两台录像机,两台彩色显示器面对面地摆放在一起,观众被永远困在互相争斗的镜像世界里,倒影和延迟使任何空间内连贯的自我感知变得不可能。此类装置采用的建筑模型和小隔间也增加了现象学体验的复杂性。这些玻璃构造常常用到双向镜子,让人感觉隐约有点儿哈哈镜游乐宫的味道,观众的身体形象被扭曲,有时甚至连基本的空间区隔都变得模糊不清。值得强调的是,格雷厄姆并没有将他的作品局限在艺术领域以内,而是把宣布或制作的场所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中产阶级住房(如《对一座城郊住房的变更》[Alteration to a Suburban House, 1978]),市区建筑(《三个连接的立方体/空间展示录像的室内设计》[Three Linked Cubes/Interior Design for Space Showing Videos, 1986]),以及公园(《椭圆亭》[Elliptical Pavilion, 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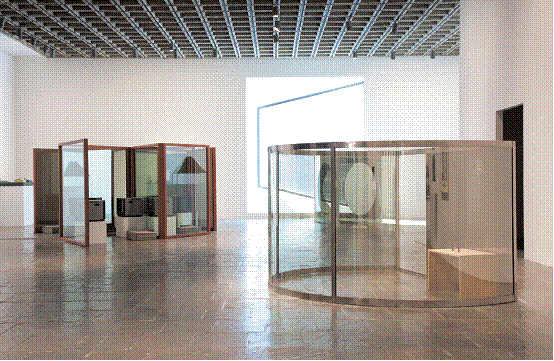
这样,格雷厄姆穿越极少主义的兔子洞,进入了一个扩大的创作世界。他再次与同一时期的其他艺术家一起使现象学体验对社会和历史语境开放,将“媒介”重设为一个时空介入问题,而“空间”和“时间”则是话语质询的问题。这一重设催生了他早期发表在杂志上的一系列作品,如《美国家庭》(Homes for America, 1966–67)。这组有关美国郊区独门独户样板房的照片看上去不动声色,却能让你感到拍摄者冷面的幽默。以上作品把出版物的内页变为艺术创作的场地。同样,这一重新定位的思考后来还促使他写了很多有关摇滚乐,电视剧,花园历史,公司中庭和后现代建筑的文章。这种对文化“社会经济框架”的关注使格雷厄姆不仅区别于大多数观念艺术中的重复叙事(他在2008年和音速青年成员金•戈登[Kim Gordon]的采访中把观念艺术斥为“学术狗屎”),也不同于大多数机构批判的纠结关系(机构批判往往选择留在分析对象所划定的范畴内部活动)。他的座右铭一直是“艺术乃一种社会符号”。
六十年代以后的美国艺术,极少主义和波普艺术各成一派,区别明显。但格雷厄姆从一开始就跨越这两条主线,并让两者的对立暂时短路:和瑙曼一样,他所表现的情境常常暗示了身体与图像,空间与媒介。(三十年前,罗莎林德•克劳斯[Rosalind Krauss]曾勾勒出一份“扩展领域内之雕塑”的结构主义地图,尽管非常精彩,但事实证明还不够不完整,因为我们无法从中找到格雷厄姆的位置)。另外,格雷厄姆还指出,诸如身体,空间,图像,媒介一类的概念并非丝毫不受性别影响;例如在行为作品《两个意识投影》(Two Consciousness Projection(s), 1972)(本次展览中以录像形式播放)中,一个女人坐在电视屏幕前,一边看着屏幕上自己的图像,一边说出自己目前的意识内容,而旁边一个站着的男人则一边拿着摄像机拍摄一边描述镜头里女人的样子。(后来改成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性别意味就更强烈了。)虽然格雷厄姆并没有像瑙曼(更不用提维托•阿孔奇)那样顺着此类行为作品发展出某种心理学戏剧,但他的确预见到了女性主义艺术中即将出现的趋势。“问题在于,”格雷厄姆在展览画册中指出,“从七十年代初开始我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
也许这一点已经足够说明为什么格雷厄姆会如此受人尊重;然而,这场展览也对他的创作提出了若干问题。有时候,他的部分创举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座实验室,观众在里面既要当科学家,也要当小白鼠。例如,在开场的“亭子”作品《公共空间/两名观众》(Public Space/Two Audiences, 1976)里,隔音构造被玻璃板分成两间,其中一间的后墙上装着镜子。观众必须选择一间进入(每间都有一扇门),然后根据指令在里面待三十分钟。(在如今这个容易分神的时代,三十分钟着实太长,所以规定时间缩短到十分钟。)制作这件作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看每个空间能够生出怎样的社会性,或者说玻璃窗两边会产生什么样的敌意,如此一来就有些斯金纳(B. F. Skinner)的味道了;格雷厄姆希望“把行为主义和现象学结合起来”,这一事实并不能安慰我们全体实验品。有时候,这种操纵控制的意味令作品的“平等性”和“民主性”(如艺术家本人和策展人所宣称的)大打折扣。
在格雷厄姆的推动下,现象学体验对社会和历史语境开放,由此产生了各种更加重要的影响。“二十年前,‘文化研究’还没有正式成为一门‘学科’时,”本杰明•布赫洛(Benjamin H. D. Buchloh)在1993年出版的格雷厄姆文集《摇滚我的宗教》(Rock My Religion,收录了艺术家1965至1990年间的文章和艺术项目简介)封底介绍上这样写道,“丹•格雷厄姆就已经将其作为艺术介入的一种模式。”这一人种志学的转向再次带来了丰富的成果;格雷厄姆与史密斯森及其他艺术家一起,提出对视觉艺术的文化资源进行重新梳理,其激进程度丝毫不亚于五十年代的独立团体(Independent Group)。除了《美国家庭》(Homes for America)之外,最好的例证就是录像《摇滚我的宗教》(Rock My Religion, 1982–84)。这部“虚构纪录片”回溯了从震教徒(the Shakers)到摇滚朋克的一系列从迷醉中寻找信仰的宗教团体(顺带讨论了包括苏族印第安人“鬼舞”在内的多种表现形式)。影片表现了出色的洞见:摇滚以其对狂喜状态的性别化彻底颠覆了宗教,在俄狄浦斯式的反抗中将女性边缘化;等等不一而足。(我最喜欢的一段是杰瑞•李•刘易斯[Jerry Lee Lewis]讨论他的音乐是上帝的作品还是魔鬼的作品。)《摇滚我的宗教》不仅符合文化研究的特点,还带有新历史主义的色彩(新历史主义支持对史料做创造性的蒙太奇拼接,同样在八十年代占有重要地位);它也预见到了如今许多当代艺术作品的档案库模式。但有时候,《摇滚我的宗教》因为无法被归入其他类别而成为艺术品(它不能算做历史,所以一定是……)而且尽管影片展现了创作者自学成才的惊人智商,但这种自学模式难免会在片中留下其独特的烙印。的确,在格雷厄姆和史密斯森开创的这些古怪的文化历史叙述中,隐约有些“呆子复仇”,“少年挑衅”的意味(“不好意思,我们讨厌杜尚,”格雷厄姆在2006年与艺术家尼克拉斯•挂尼尼[Nicolás Guagnini]的采访中说,“我们那时候喜欢的是Speer”)。格雷厄姆始终对成年人主观性的常规模式持怀疑态度,一直支持年轻艺术家和音乐家的工作,最近他与托尼•奥斯勒(Tony Oursler),罗德尼•格雷厄姆(Rodney Graham),洛朗•伯格(Laurent P. Berger),布鲁斯•奥德兰(Bruce Odland)和Japanther乐队合作完成了一部动用了木偶,录像投影,录音和现场音乐的摇滚歌剧,名字叫做《不要相信任何三十岁以上的人》(Don’t Trust Anyone Over Thirty,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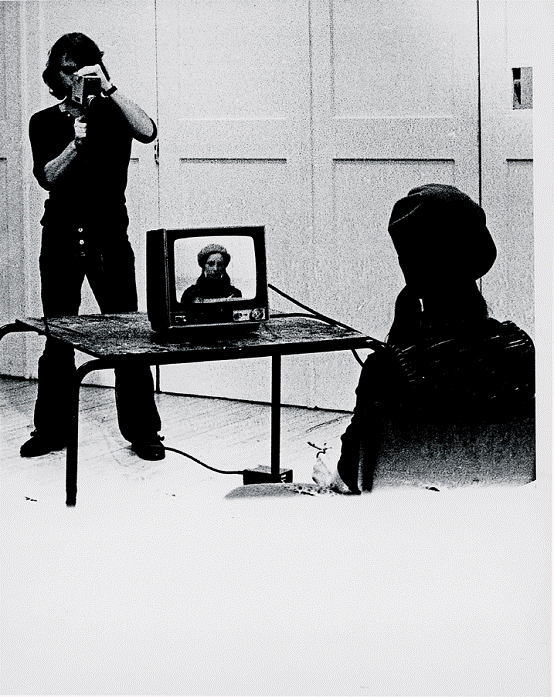
“我总是试图把两样完全不搭调的东西凑到一起,”格雷厄姆告诉我们。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在《摇滚我的宗教》里是安•李(Ann Lee, 震教创始人)和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在他的文章里是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迪恩•马丁(Dean Martin)。这种搭配的确起到了陌生化的效果,而格雷厄姆在展览画册中也引用了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维克多•什科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有关陌生化的理论。然而,在什科洛夫斯基来看来,把传统陌生化是为了推进艺术——用他的原话说,艺术以“骑士的步伐”前进——而格雷厄姆有时则走得太远,几乎消失在其他世界里。(展览名“超越”可能无意中道出了这层含义。)也就是说,我们很难跟上他的骑士步伐,而他的文化指涉在力度上也越来越倾向于共时,而非历时。虽然他的作品面向普通对象和公共场景开放,但这也提出了一个可读性的问题。他的指涉母体到底有多客观?其逻辑体系是否只存在于格雷厄姆一个人的头脑当中?他说他的艺术是“一种狂热的爱好”,显然他的作品就来自这股热情。但一名艺术家的DIY历史是否适用于另一名艺术家?他的这些“杂交作品”是不是无论对他本人多么富有生产力,对其他人却毫无意义?
本次展览让我击退了这种怀疑。格雷厄姆率先开始的这种跨学科创作并不仅仅是文化冲浪,事实证明,许多年轻艺术家都从中汲取了灵感。(如果没有格雷厄姆,迈克•凯利和米勒的亚文化调查就变得难以想象。)格雷厄姆对Orchard–Reena Spaulings(纽约的两家画廊)那帮人的影响就像安迪•沃霍尔对所谓的“图像一代”(Pictures generation)发挥的作用一样——只不过,部分来讲,正是因为有了格雷厄姆这样的人,艺术史才似乎不再以这种朝代更替的方式向前发展。尽管受惠于前人,格雷厄姆并没有深入参与“问题-解决-问题“这类沃尔夫林式(Heinrich Wölfflin,瑞士著名美术史学家)的辩证法当中。无论他在艺术上可能抱有什么样的俄狄浦斯情结,最终都消融在他广泛的文化兴趣和引证之中。他相对不太受“影响的焦虑”困扰,本次展览上的新作《影响我的艺术和建筑作品》(Artists’ and Architects’ Work That Influenced Me, 2009)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件投影作品向多位前辈表达了敬意,从克拉斯•欧登伯格(Claes Oldenburg)到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再到丹•弗莱文(Dan Flavin)和罗伯特•曼戈尔(Robert Mangold)从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和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到蓧原一男(Kazuo Shinohara)和长谷川逸子(Itsuko Hasegawa)。
惠特尼美术馆的布展做得很聪明,简洁明快,但又不死板,外观诱人,内容也很充实(比如,如果你愿意,可以把格雷厄姆在杂志上发表的作品《模板》[Schema, 1966年三月]十二个不同版本都读一遍)。因此,我们得以了解这种创作实践的不同框架和利害关系。展览画册做得也很好。除了策展人和其他人的各色文章,还有不少古怪搞笑的采访(大部分是其他艺术家做的),格雷厄姆的文章,以及由野々村文宏( Nonomura Fumihiro)和谷本健(Ken Tanimoto)创作的漫画“格雷厄姆入门”(单凭这部分,这本画册就值得一买)。最后,我想少见地向主办机构表示感谢。过去几年,洛杉矶MoCA和惠特尼美术馆已先后合作举办过了史密斯森(2004),戈登•马塔-克拉克(2007)和劳伦斯•维纳(2007-2008)作品展,本次格雷厄姆个展也属于这一系列。尽管以白人艺术家居多,但对于那些欣赏格雷厄姆等老一辈的创作,但苦于找不到第一手资料的年轻人来说,这些展览的确是一份绝佳的入门教材。董事会成员也许会担心举办这类非大片级的展览是否划算,但我们其他人真的应该心存感激。
“丹•格雷厄姆:超越”将在纽约惠特尼美术馆展出到10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到2010年1月31日,展览将移至明尼阿波利斯的沃克艺术中心举行。
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是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学教授。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