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BOOKS

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和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在他们尝试重新改写人类历史的《万物的黎明》(The Dawn of Everything)中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我们的史前祖先并不是头脑简单不会思考的野蛮人,而是有自我意识、个性各异的社会组织者,生活在“如嘉年华般多样的政治形式”中。如今我们可能会用“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专制主义”或“平等主义”这样的词来描述他们的活动,但这种语言实际上无法传达出每个案例独特的不规则性,比如没有中央政府或农业的大城市(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跨越大陆的部落国家(卡霍基亚,Cahokia)、社会住房项目(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以及随着季节的不同在水平主义(horizontalism)和专制统治之间切换的族群如南比夸拉族(Nambikwara)、 温尼贝戈人(Winnebago)和努尔人(Nuer)。考古学家温格罗和已故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行动者格雷伯提出,四万年来,人们一直在反复构建各种形式的平等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建立等级制度或将其拆除。两位作者认为,与现在的人相比,无国家社会中的人们反而政治自觉性更高。那我们是如何被困住的呢?
对格雷伯和温格罗来说,要接受“旧石器政治”(paleolithic politics)就是要理解,人类长期以来一直在实验各种组织自己的方式,而且社会变革的道路并非线性的,并从这些历史事实中汲取力量。实际上,这本书最大胆之处就是对我们当前境况的目的论观点提出质疑。书中认为,人类最初的30万年提供了一个既多变、暴力又充满希望的过去——而且比我们对其一贯的扁平化描述要有趣的多——所以我们的未来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个想法令人振奋,但它的意义才刚开始被重视。虽然夸梅·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等学者认为格雷伯和温格罗他们的资料中得出的“宏大”结论需要被更仔细地审视,但我认为这不会改变什么。面对日益逼近的气候灾难、政治两极化和社会崩溃,这本书的乐观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挑衅。

考虑到近几十年来出现了大量模糊艺术和社群行动主义界限的作品,这本书能给艺术界带来什么?艺术史中充满了乌托邦式的思考,但《万物的黎明》将这种冲动重置于漫长的社会重组的语境中,早于“关系美学”和“社会实践”等词汇的诞生数千年。当然,我们不能将艺术家实验性的小规模临时项目——比如布朗克斯的托马斯·赫希洪(Thomas Hirschorn)、皇后区的塔尼亚·布鲁格拉(Tania Bruguera)和东京宫的提诺·赛格尔(Tino Sehgal)——与我们上一个冰河时代的遥远祖先直接进行比较。虽然新闻稿、展墙文字和评论中不乏激进主张,但人们日趋一致地认识到,当今最有抱负的社会实验发生在与传统艺术活动相距甚远的地方。与非营利机构、博物馆和双年展所展示的那些得到机构认可的艺术作品相比,2011年的“占领”运动、最近的互助行动,以及全美各地的罢工和工会运动浪潮与温格罗和格雷伯笔下史前祖先的世界构建(worldmaking)有更多共同之处。但或许,我们应该去思考一个更具时间、地理和学科丰富性的关系艺术史。我们之所以不称这些祖先为艺术家,是因为当代框架在理解人类想象力上的局限性,而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创造力。两位作者认为,社会实践并不像现在包装的那样是当代艺术的一个小众类型,而是人类政治活动的命脉。
今天,我们很容易把艺术领域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研发部门,或者是对真正的革命的缺乏热血、“体验经济”式的模拟。然而,在阅读《万物的黎明》时,你会感受到政治意识即艺术意识。这一观点让我们能够以一种新的乐观的态度来看待艺术作品,将它们视为通向替代性生活方式的小窗口,而不是“人造地狱”(artificial hells)。格雷伯和温格罗将“复杂的象征性人类行为”(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的首个证据追溯至10万年前。他们不但将雕塑、洞穴壁画和土方工程作为创造性表达的证据,更将其看作根据生产需要不断变化的社会形态的反映,例如,大规模动员熟练和非熟练劳工创造哥贝克力石阵的两百个独特的动物石柱,或者米诺斯克里特艺术中母系社会的痕迹,其中所有权威人物都以女性形象表现。但该书对艺术更深刻的影响是哲学性的。“我们正在再次与强大的现代神话交涉”,作者们在谈及当今主导的历史叙述时说,这种叙述认为我们当前的境况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神话不仅是在告知人们要说什么,更是在确保某些事情能够隐秘地发生。”和艺术家一样,格雷伯和温格罗也在根据新的物证来制造反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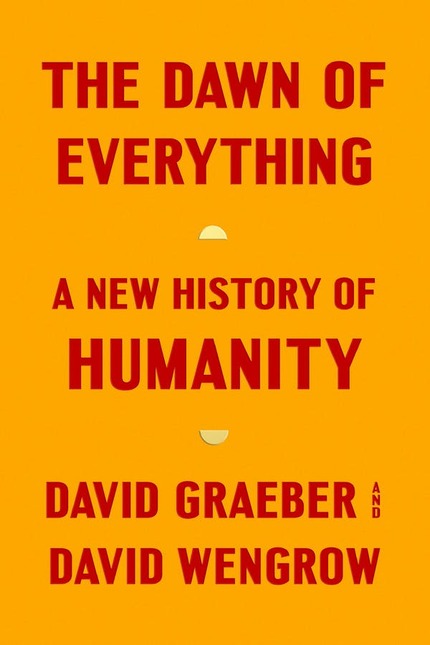
这本书还将艺术置于一个更广泛的人类活动领域中:玩乐。并非所有新石器时代的创造都是为了生产目的:早在新石器时代之前,人们就发明了陶瓷,用于制作艺术品和小雕像,后来才出现了烹饪和储存器皿;希腊人就曾发明蒸汽机,但只是为了让神庙的门打开,唤起神的力量;中国的科学家首先发明了用于烟花爆竹的火药。“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仪式玩乐领域既是一个科学实验室,而且对于任何特定的社会来说,也是一个知识和技术库,而且这些知识和技术不一定应用于实际问题。”
玩乐的启发也延伸至该书对社会形式的分析中,例如“国王游戏”(play kings)或“警察游戏”(play police)。比如位于今天的路易斯安那州的纳奇兹(Natchez)社会中,“大太阳”(the Great Sun,即神圣君主)在王村(royal village)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这个村庄只是一个位于毗邻神庙的巨大泥土广场上的小屋,统治者的权利仅限于此。在王村之外,臣民如果不愿意服从命令,就可以无视它们,或者搬到附近拥有独立商业活动、军事装备和相互矛盾的外交政策的更富裕的地区。纳奇兹人进行的一种仪式性的战斗中也掺杂了游戏元素:每年,平民们都会假装伏击、俘虏并准备杀死国王,直到第二支模拟战队介入救援。而在欧洲入侵期间,君主主权与臣民的革命游戏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发展为真正的敌对行动,一些地方选择与法国人结盟,另一些拒绝。此外,每当狩猎水牛的敏感夏季到来时,居住在现在的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的曼丹·希达萨人(Mandan-Hidatsa)和克罗人(Crow)就会建立一支拥有强制力的警察部队。但在寒冷的冬季,这些实体将被完全解散,临时的“酋长”和“警察”将被剥夺所有权力。虽然君权并不会因为是暂时的而失去效力,但这样也许是为了“玩乐”的集体性社会实验倾向,使得自觉的政治转型几乎持续不断地发生。

《万物的黎明》对人类历史的改写与艺术机构近期在重新思考经典作品及其线性叙事上所做的努力是相似的。在这一方面,这本书一开始关于“原住民批判”(Indigenous critique)的章节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追溯了美国原住民思想对启蒙传统的影响。这一章节关注于休伦-温达特族(Huron-Wendat)政治家康迪亚隆克(Kandiaronk,化名为阿达里奥,Adario)在1703年一篇由驻扎在加拿大的法国贵族拉洪坦男爵(Baron de Lahontan)撰写的有影响力的文章中对欧洲社会作出的评价。“我花了六年时间思考欧洲社会的状况,我仍然想不出他们有哪个行为不是非人道的,”拉洪坦男爵在一段批判欧洲性格的悲哀和痛苦,它的竞争性以及对财产的痴迷的段落中引用了阿达里奥的话。“想象一个人可以在金钱的国度里保住自己的灵魂,就像想象一个人可以在湖底保住生命一样。”长期以来,阿达里奥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道具或修辞角色,而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但作者认为有确凿的证据相信,这几乎完全是以康迪亚隆克本人为基础的。而且,像温格罗和格雷伯那样把康迪亚隆克称为一位“美国知识分子”也是对这个称呼发起的一场革命,因为这表明在欧洲和美洲文明接触之初就发生了激烈的智性辩论。
那么,最终该如何看待这本书在“人本”(humanness)上的坚持?当许多艺术家、策展人和学者都渴望在他们的作品中“去人类中心化”的时候,《万物的黎明》邀请我们去做一项(更难)的工作,也就是重新构建人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到底是什么的复杂问题。在书的结论部分,格雷伯和温格罗用另一个问题补充了他们最初的问题,即我们是如何被困住的:基于统治和暴力的关系是如何被正常化的?两位作者在修复人性上的慷慨态度表明,我们可能并不需要超越人类的概念,而是需要记住更古老的想法。
文/ Simon Wu
译/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