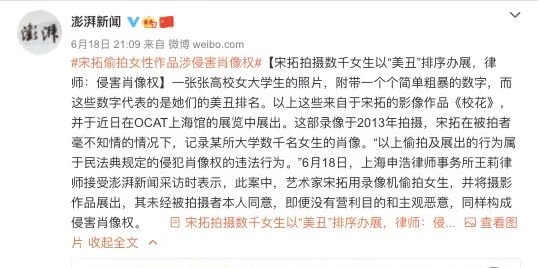
重访“校花事件”
宋拓的影像作品《校花》(2012)于2021年6月在OCAT上海馆展出遭遇的网络抗议及撤展引发了社会最大范围的围观、议论与争端,在近年的当代艺术生态中实属罕见。这一方面反映了性别议题在媒体讨论中的热度和随之引发的公众态度的决定性转变,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公众对当代艺术现场越发高涨的参与度。不过,向来标榜走在时代思潮前沿的当代艺术界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扩大的观众群和社会氛围改变带来的冲击?
事件中的网络热议既包括对这种创作是伤害而不是艺术的严厉质疑,也不乏镜像式的人身攻击和报复性创作提案。这些展厅外的争议最终迫使艺术机构公开致歉并撤展闭馆,而这一过程中,艺术家则处于全面隐身的状态。多家主流文化媒体迅速刊登了立场相异的业内评论:澎湃思想市场题为《冒犯的艺术,谁的同谋》的文章呼吁整个艺术界承担此次事件带来的公众失信,而随机波动与界面文化的两篇评析均强调尊重艺术自由,并呼吁思考撤展以外的其他方案。作为一个社会事件,到此似乎已经终结,但作为一个艺术界的现象,后续讨论却并未真正展开。本文意图以艺术生产和舆论流通的双重视角重访《校花》,通过透析其内部逻辑和流通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矛盾,提供一种理解该事件的可能路径。
我们不妨先来观察一下《校花》的艺术生产逻辑。艺术家从社会现象中抽取出当前观念下被认为是“小恶”的行为——对他人(女性)外貌进行评判和排序——并在艺术生产的空间中对之进行放大性演绎。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