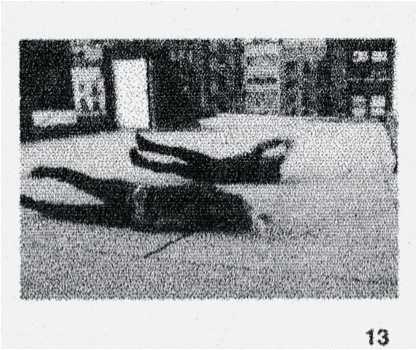我的俏皮情人:《已经给出》
《已经给出》——杜尚秘密创作了二十年之久的杰作——是二十世纪艺术界最大的谜团之一,其令人困惑的戏剧效果与艺术家一贯反视觉的立场背道而驰,作品的意义也引来无数争议和猜想。在本篇文章中,策展人/艺术史学家海伦·莫勒斯沃霍(Helen Molesworth)将为我们盘点费城美术馆近期的展览“马塞尔·杜尚:《已经给出》”,细数她自己与该作品长期以来爱恨交加的复杂关系,并为这件谜一样的杰作提出一种惊人的解答。
“你是我最爱的艺术品……”
要看马塞尔·杜尚在费城美术馆的作品《已经给出》(Étant donné),必须走过一条很长的过道,过道尽头正前方就是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的《大浴女》(Les Grandes Baigneuses, 1906)。毫无疑问,《大浴女》是一件重量级的艺术作品,但同时也是一幅怪诞的画。巨大的规格与其表面声称的主题并不十分吻合:裸体人像在一片田园风光里嬉戏玩耍。裸体人像(我们要不要称其为女人呢?)或坐或立,不断繁衍;他们仿佛在风中摇曳的大树一样朝彼此弯曲,围绕画面中心形成一个括弧,但这个中心却别无他物,出奇地空洞。该空白暗示着这幅画里某些东西让塞尚觉得荒唐。简直就像他已经知道一切都完了:风景画里的裸女?真的假的?1906年?
在塞尚的作品前,向右转,沿着长长的拱顶大厅往下走,现代主义画卷在你面前徐徐展开。说实话,费城美术馆的二十世纪艺术品馆藏在国内堪称一流:阿瑟·德夫(Arth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