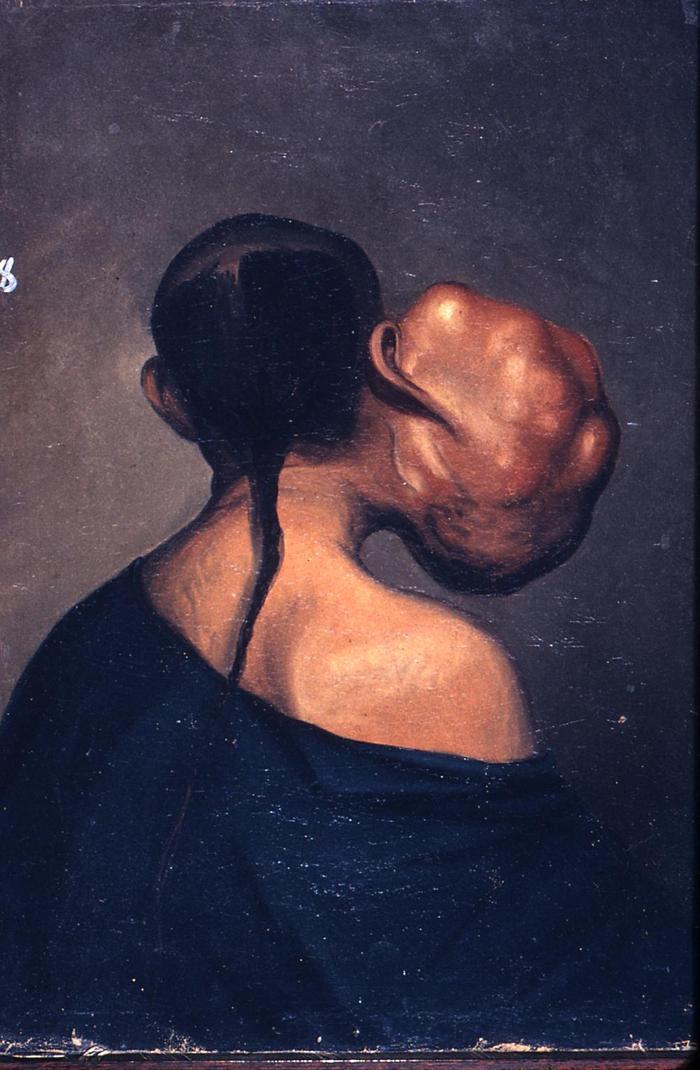Déjà Disparu
“Déjà Disparu(已然消失)”是个难得的展览,估计对于很多观众来说,这是他们首次看到这些九十年代香港艺术代表作的原作。对我来说,特别注目的是黄志恒(Sara Wong)的装置作品,曾经从照片中看过Sara的充满精巧细节的装置作品的话,应该都会希望一睹其原作。至于鲍蔼伦(Ellen Pau)的录像旧作似乎在Videotage的档桉库是可以看到的,但在电脑上看和在展览的陈设中看的录像艺术,实在是两回事。所以,这确是一个很有历史回顾意义的展览。
展览的题目借用Ackbas Abbas在1997年的经典着作《香港:文化与消失的政治》(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中的一个提法,它试图描述的是后殖民香港在身份认同的缺失下的文化政治状况 ── 香港文化是一种“Déjà Disparu”(「已然消失」)的文化,一旦看到,它已经消逝了,一切都是浮动的,暂借的,不求永恒的。这个感伤而浪漫的论述十分著名,于香港文化论述影响深远。这个展览再一次提到Abbas的《Déjà Disparu》,却似乎没有提供阅读这个着名论述的新方式,既没有延伸,也没有颠覆它,而有点像用展出的作品为这个早已不新的理论作一些视觉阐述。
这个延伸或颠倒阅读可能是什么?或许是:以解释香港文化状况,典型的后殖民流离失所心理固然合理,却过份笼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