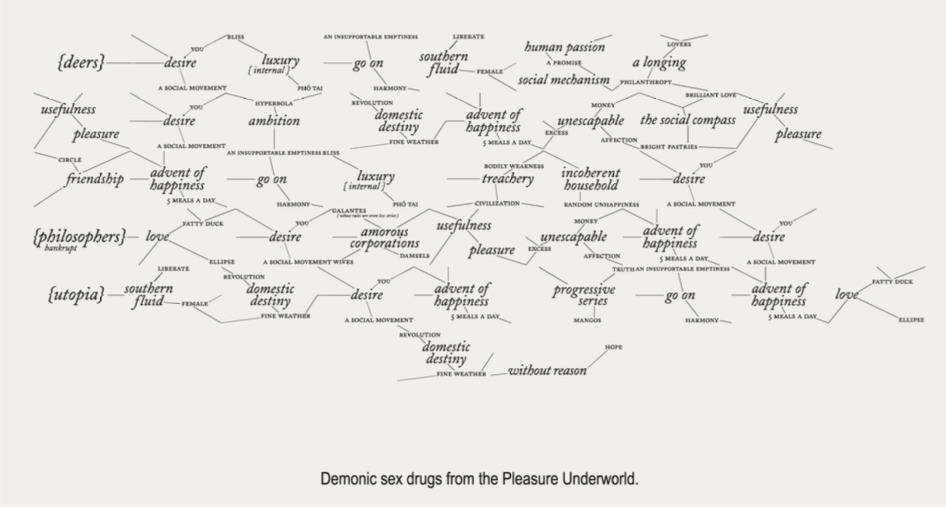
斯芬·吕提肯(Sven Lütticken)的《文化革命》
[[img1]]
历史前卫艺术——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构成主义——的驱动力之一便是融合艺术与生活的决心。众所周知,通过全面接纳新的媒体和移动技术,包括马里内蒂、汉斯·里希特(Hans Richter)、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在内的艺术家们利用各种手段希望弥合“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距离:倚重群体运动和宣言的某种形式的直接行动主义;偶发艺术;对偶然性和巧合的引入。同样重要的还有针对艺术机构本身的口头、甚至身体攻击。“我们将毁掉各种博物馆、图书馆、学院……放火烧掉书架!引河水淹掉博物馆!啊,看到那些光辉一世的老旧画布飘在水上,颜色尽褪,不成形状,该是何等痛快!”1909年《未来主义宣言》如是说。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情况又如何呢?我们没有按照当初玛里内蒂的要求把美术馆变成工厂,相反,我们把工厂改造成美术馆——以极快的速度和极大的数量,从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到巴塞罗那的开夏美术馆(CaixaForum),从赫尔辛基的电缆厂(Cable Factory)到伊斯坦布尔的santralistanbul,更不用说遍布柏林、苏黎世,甚至几乎每座欧洲城市的“文化酒厂”。
表面上看,这一逆转与其说跟前卫艺术有关,不如说跟“晚期资本主义”的关系更加密切:全球化对廉价劳动力的逐底竞争,制造业工种从发达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