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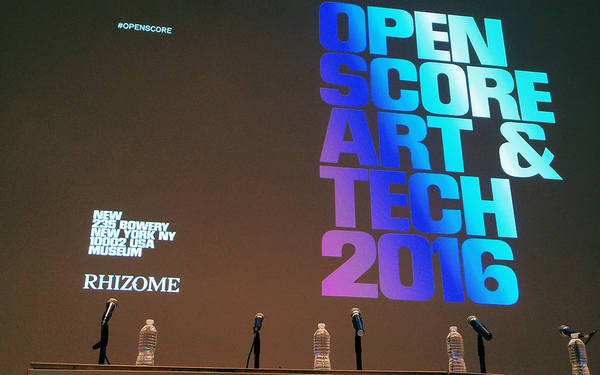
已经2016年了,人们说起互联网来还好像它有自己的思维一样。有关“数码”如何作为“历史主体”(更糟糕的说法是“自成一体的空间”)的讨论就像一个家庭产业。艺术这块儿,讨论内容从哗众取宠的流言(Instagram如何扰乱艺术市场)到长篇大论的著述(Melanie Bühler,Phoebe Stubbs,以及最近的Lauren Cornell和Ed Halter都写过数字艺术及其“后网络”命运)无所不包。
近期,新美术馆和Rhizome也加入了这场混战,两个机构联合策划了一场名为“开放计分”(Open Score)的年度研讨会,探讨艺术与技术现状。研讨会题目取自系列表演“九个晚上:戏剧与工程学”中的同名作品,作为这场标志Robert Rauschenberg和Billy Klüver“艺术与技术实验”(E.A.T.)项目爆发点的活动的五十周年纪念。一直以来,艺术与技术都有互相重叠之处,但如今,连接无处不在,“软件正在吞吃整个世界”,至少某风险投资人是这么说的(参见《华尔街日报》2011年8月20日报道)。
四场专题讨论汇集了数字领域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代表人物。新美术馆馆长Lisa Philips的开场介绍听起来像硅谷建筑师们写的零和程序脚本,期间提到“数字技术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这种技术决定论,我们得持保留态度。当你是一家受到数字网络挤压的文化机构时,夸张的修辞自然是你最好的朋友。)如果早期的艺术-技术合作还带有独立实验的装饰,如今我们的网络早已浸透了政治。我们也许跳进了一个“民主空间”,但身边还带着资本主义这个小伙伴。正如Cornell和Halter在《大众效应》(Mass Effect)一书的序言中所言,最近的一批艺术家是“第一拨不把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介,而是当成一种真正的大众媒介来予以回应的人。”数字网络的扩张要求超越艺术实践长期以来固守的媒介具体性。
第一场专题讨论“你世代”(Generation You)由Andrew Durbin主持,与会者包括艺术家Simon Denny,Juliana Huxtable,Jacob Ciocci以及诗人Cathy Park Hong。社交媒体对他们自我品牌定位的要求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们如何应对其中无处不在的商业压力?Ciocci第一个对社交媒体已变为常规和景观的他者化提出疑问。他认为,技术指“可以组织或拆解现实的任何东西。”这里面无甚新鲜可言。第二位发言人Denny则毫无保留地拥护社交技术。他回述了自己对斯诺登泄露出来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幻灯片的调研,以及他如何利用LinkedIn和Behance等社交网络找到了David Darchicourt—NSA幻灯片“超烂设计”背后的创作者。在Denny看来,Darchicourt的作品象征着某种崇高性,而他在威尼斯双年展新西兰馆的展览上把Darchicourt与提香、丁托列托并置于圣马可图书馆,以此拉出了一条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一直到今日社交网络的信息掌控再现的谱系线索。

你也许知道—信息过量也影响着诗歌。“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诗人们就已经习惯过量的信息,”Hong指出。但面对广袤无垠的数据库,诗歌反而开始变得简单化了。Hong认为,互联网上的诗歌“难度”降低了,越来越讲求效率,越来越简化为倾向于顿悟或告白的“内容”。对此,她的态度比较犬儒,将这种诗歌跟“用户界面友好”的软件设计标准放到一起:“格特鲁德·斯泰因要是活到今天,在Tumblr上肯定没什么人关注。”
当我们反思这个被称作“互联网”的杂乱技术星丛时,时间是一个矢量、一根轨迹、一条线路、一个储存记忆的部分性容器。除却这一点,它就是无数连得上或者连不上的服务器。反作用已经全面显露。Huxtable谈及她无法在保持自身与社交网络之间批判关系和对社交网络既“必要”又“无处不在”的切身感受之间找到平衡。她指出,针对网络内容的历史化操作也许会向其民主化性质的表象提出挑战。谷歌“档案库”诞生于某个具体的时间点,Huxtable认为:互联网不仅仅只是一片无时间的汪洋大海。接下来的讨论不断回到互联网内在多样性这一话题,作为对其单一隐喻状态的反击。
数字平台也许可以让人更容易地获取信息,但其设计构造对批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第二场“赞与评”(Liking and Critiquing)由Ed Halter主持,四名(广义上的)艺术批评实践者参与了讨论。超文本成了新的典范,作者们现在必须直面他们跟平台主的封建关系。几年之内,我们就从“谷歌正在把我们变成笨蛋”走到了“给facebook用户开工资!”当然,我们对之如此感恩戴德的社交网络,其背后的管理者—吓一跳吧!—并不是来搞慈善的。Kimberly Drew不认为自己是一名批评家,也不像其他人那么被这个问题困扰。作为把平台放在Tumblr和Instagram上的“黑人当代艺术”
(Black Contemporary Art)的创始人,Drew对于上述平台的特殊形式保持乐观。“清单体(listicle)为什么一定是个坏事儿呢?”她问道。
这一观点在其他世代也能找到共鸣。Jerry Saltz称他的社交媒体言论生涯几乎始于偶然,其契机是他几年前在facebook上一条有关Marlene Dumas展览的天真评论。但现在,他对纯粹意见的喜爱,以及对“学院教育里晦涩术语”的鄙夷让他跟线上讨论多对多的意见交换形式站到了一边。Drew和Saltz说得不无道理:某一天我们也许会发现,一篇专家文章里的主要论述放到facebook对话框的商业终端可能可以得到更好的呈现。
对于很多批评家来说,社交媒体比专题论文经过深思熟虑的表述来得更加灵活,既可以对开幕发表礼貌的评论,又可以传播之后在附近酒吧听来的八卦。但Brian Droitcour和Laura McLean-Ferris怀疑这种写作对持续、严谨的批评话语将产生何种影响。在McLean-Ferris看来,艺术批评家真实生活里的社交关系在线上平台被人一览无余,这会导致他们很难保持客观中立。Droitcour则认为,经数字技术中介的新的艺术批评形式只是辅助手段。其性质更接近言说,而非文本。Droitcour的观点非常独特:他给Yelp开的艺术机构推荐单和他作为编辑供职的《美国艺术》杂志上的评论文章共生共存。“就像艺术批评只不过是在肯定现已存在的这些权力结构,” Droitcour认为我们想要在网上分享自己经历的欲望也只不过是肯定了大量社交平台的存在而已。

最后一场“互联网艺术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ternet Art)追问了随着互联网的主流化,网络艺术实践发生了何种变化。Rhizome艺术总监Michael Connor开头便提出这种艺术形式里很少被人意识到的(加州式)意识形态。艺术家Constant Dullaart则提醒我们:“网络艺术产生于对大众传媒的纯粹绝望。”有一阵子,我们似乎看到逃脱大公司控制,获得自由的零星希望。但作为一种本来建立于有关数字技术的模糊隐喻基础之上的艺术类型,网络艺术只是在弥补损害。在后斯诺登时代,我们显然不可能还想当然地认为“网络空间”是一个独立、去体制化的边疆地带。(Dullaart称今天的社交媒体平台为“新帝国主义”。)
Triple Canopy总监Peter Russo讲述了他的“地方性机构”如何穿梭于线上权力结构之间:“一次小小的浏览器更新就可以搞砸整个项目。”但Triple Canopy价格不菲的定制式出版平台并不对所有人开放。大部分艺术家用的还是开箱即用的网络产品。艺术家Shawné Michaelain Holloway讨论了她所用媒介的空白画布—空无一物的浏览器界面。“这是我工作的地方,”她解释道。“我可以从哪里获取权力,同时,又有哪些权力被加诸于我身上?”尽管还存在缺陷,Holloway和Colin Self两人的项目都利用消费类网络产品为LGBT群体提供DIY服务,将这些平台变成了某种解放的工具。
所以,当人类信息交换的速度快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时,会发生什么?“开放计分”捕捉到了数字艺术实践在2016年的困局:我们一边想要保留虚拟材料的特殊性,一边又不得不承认它们正迅速上升进入商业媒体食物链。值得庆幸的是,艺术家们正在积极对这一被称之为互联网的情感现象进行重新想象,而技术决定论的大潮也可能正在退却。时间正好:评论者已经开始审视我们对互联网文化定下的狭窄框架。在《大众效应》中,Cornell和Halter对他们的书在二十年后是否还有使用价值表示了疑问:“到时候,与互联网有关的某种具体艺术模式这一概念本身是不是会变得毫无意义?”也许,现在已经是了。
文/ Mike Pepi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