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Pace北京” 两千多平米的空间在798艺术厂区开幕的当天上午,各路人马开始为穿什么而感到惶惶不安了。“你穿高跟鞋还是拖鞋去?”北京的画廊果们在MSN上彼此询问着。 一个高古轩的人发来短信问:“北京画廊夏天开幕的话,穿短袖去合适么?” ;“我们能不能带我们的两岁孩子去?”《纽约太阳报》来北京报道奥运的记者问道。这些难题似乎有些可笑,但这些问题似乎契合了奥运开幕前心跳的时刻:我们是不是把这场活动当成了发生在纽约的一场类似的隆重活动呢?还是说,我们是否还是处于边缘地带,一切规则都可应人而变?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把北京太当回事了呢,即使知道现在这个城市把自己弄得也很隆重。

我决定不让自己在这方面被弄得团团转,采取了一个妥协折中的方法,带上我那穿着Manolo高根鞋的朋友坐上了出租车(要是画廊在单号那天开幕的话,我们就能自己开车过去了)。 798——做为奥林匹克年六个官方旅游景点之一,大修之后呈现出一派华丽的新气象,保安戴着崭新的印着北京2008的棒球帽,为一群群的参观者们指引着道路,花儿摆放在路口,摄像头监控着门口。要是有一天就像 Marc Glimcher在《纽约时报》说的那样,“798现在比切尔西的来客还多”的话,那么今天正好印证了他的这番话。 我先是参观了一些之前错过的展览,由于交通限行,这些展览此前我都没有去过:有林天苗在长征的展,在那儿,一脸迷惑的村上隆排在我们身后等着进入一间布满绸缎的房间里;又去了王度在唐人的展,当时,以演警察和黑社会老大著称的演员孙红雷,正拿着画廊提供的刀,去切艺术家的33尺高的图片烤串儿;而常青的群展上, 参观者们则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碰到孙原和彭宇的带轱辘的垃圾车,车在画廊里随心所欲地开着。我们礼貌地聊完天,直接向被奔向了Pace的空间,我的朋友可是得谢谢这用石头铺好的新路。

对于这场以“东—西”为理念的展览,该怎么说呢?中国艺术家的作品遭遇到了给过他们启发的欧美艺术家作品,一些人曾经设想过这样的碰撞交融,但是在此之前,还无人有资金去实现它。在弯曲的“包豪斯”式的半拱形下的临时白墙上,王广义遭遇到的是沃霍,刘炜碰到的是巴斯奎特, 张晓刚碰上的是昆斯。在村上隆价值上百万美元的Skeleton的画作几尺外,两位中国艺术家吵吵起来。似乎没人认出他们来,当Pace的一个工作人员让其中的一个离开时,典型的过度爱国谣言开始嗡嗡起来,开始谈论着殖民者们是要来赚钱来着。“遭遇”,正如展览的题目那样,总是令人吃惊的。
太阳在创意广场慢慢落下,我们觉得是吃饭时间了。我们和一些美国画廊家穿过靠着尤伦斯中心正门超级大干杯餐厅(原江湖餐厅),一行人来到了咖啡馆。老牌画廊家Jack Tilton、Chip Tom 和 Jeff Poe坐下来喝着科罗纳,对于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的艺术大牌,语调中混杂着妒嫉和高傲。

在咖啡和餐馆中间的路上,恰好与某些人不期而遇。我跟尤伦斯的馆长杰罗姆·桑斯 (Jérôme Sans) 打了招呼,他在街中央和盖伊·尤伦斯本人开聊呢。村上隆和画廊家Tim Blum(他看起来不愿意让他的艺术家离开他视线半步)是另一伙。东京SCAI the Bathhouse(俗称“澡堂画廊”)的创始人Masami Shiraishi, 走过来和桑斯打招呼,不过他没认出尤伦斯,嘀咕着说:“村上隆,我给他做过首展呢。”边说边问这个比利时人是谁。做为回应,尤伦斯男爵迅速地指向他左边的美术馆说:“看见了没,我的地儿!”我很快返回去,和美国人坐到了一起,他们谈论着没落的帝国,以及奥运周不可思议地合理的飞机票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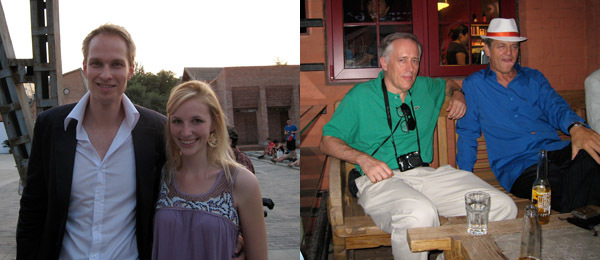
我们结了账进了餐厅,尽管纽约的总部一再邀请确认,但是桌边的位置,依然留给了Pace的人、拍卖场上春风得意的画家和心急的收藏家,他们围转着Pace北京的总监冷林,此外就没有给别人留出多余的座位了。我们得按照当地规矩办事,冷的助手、当天晚上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还有席位,但来不急写名字了,可是对于我来说,没有名字就不应该入座。当所有人开始落座时,我离开了,想起了2003年德梅隆来到国家体育馆参加破土动工仪式时,被工地的一位女保安拦在了外面——这可是过去五年里,关于中国的一个恰当的小寓言,而现在,这样的事似乎在不起眼的“闯入者”身上,还起着作用,比如一场画廊晚宴。我们走出了798, 回到了主路上,想起2002年,这里的首家画廊开幕时、新航站楼、 鸟巢、cctv新大楼,当时不过还是幻想中的蓝图呢,而现在呢?还好,此时此刻北京还能打着出租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