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FILM & VIDEO

本次对谈基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艺术跨域研究所“做作他人——(非)关田调工作坊”中“朝向他人之二:1930s-50s・风车诗社”整理而成。
黄建宏:首先很高兴邀请到黄亚历导演来与我们交流。《日曜日式散步者》是一部非常特别的纪录片,一方面它讨论的是三零年代台湾的一个诗社,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这部影片的影像中看到很多物件或者书写的文字,这与我们通常认为的纪录片导演或者艺术家所做的田野调查非常不同——他们再现或关注的对象非常明确的是还活着的人,或者说是一个现存世界里的人,而亚历导演处理的是三零年代台湾的艺文人士。接下来我想先请亚历导演跟我们谈一下他制作这部影片的相关想法以及他为此进行的调查。
黄亚历:我想这部影片目前为止应该放过至少五、六场,每一场一定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拍这部影片?其实就姑且说它是一种缘分的召唤吧,大概在2012年的下半年,我因为在准备一个跟超现实主义有点关系的座谈,搜寻资料的时候连结到其中一位诗人,也就是风车社里的一位诗人,林修二。我当时觉得太惊讶了,从来没有想过台湾居然在三零年代有这样的一个团体存在,所以决定有朝一日要来拍这部影片。但这个时间一直不确定,而且大概也跟自己的生活状态有点关系,所以拖了一年半,一直到决定要拍摄之后,我已经陆续经验了所谓的“田野”这件事情,开始时读一些有趣的翻译文献,而且是别人整理过的。但当那些东西渐渐读完之后,我开始思考还要读些什么,因为东西没有想象的多,但知道有很多重要的文献等在那里,而且你不知道到底在哪,一切都是未知,就是等着你什么时候开始。同时我也必须找资金,必须开始联络家属,进行很多的口述历史纪录。
我对那个时期真的觉得陌生,这个陌生的程度大概是与我一直对日本没有兴趣有关系,比如我欲望出国的选项里从来没有日本这个国家,所以当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去日本找资料的时候真的是不太开心,那到底要去几次、花多少费用,一切一切的预算像滚雪球一般涌出来。所以我今天可能会不断的回头提到预算加诸在我身上的压力,仿佛它永远跟随着你一起田调——我一直觉得就算有一天拍完影片,田调这件事好像也无法结束,资金这件事当然也就没有结束。在田调以及与学者的访谈过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我看到台湾文化相关的研究学者,他们在多年前用力发掘出风车诗社,让它浮现台面,而且努力赋予它们一个历史的定位。尤其是全台湾在当时可能大概有98%以上的人并不知道这个团体的存在,所以在咨询学者的过程中,除了在恶补功课之外,我也会使用到例如建宏老师提及的“感性田调”:试着去设想学者的位置,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以及如何试图令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团体被定位。
我们知道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些作者某种程度也被污名化过,或被盖棺定论为“某一种”作家等等,所以我们多少会感受到,为了让风车诗社浮现出来,这些学者必须設想一套对策来说服在不同研究基础上的其他学者。但是在设想的过程中我仍不免开始有点疑惑,如果说需要一些不同瑜过往的关照点让它被谈及,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些新的诠释有可能失真(又或者反推出过去的诠释是失真的),那么所谓的“真”到底在哪里?这个诗社最老的一位诗人1908年出生,最年轻的一位1915年出生,去年过世了,连这一位我都没有办法亲口听到他说话——他最后是躺在床上的状态,所以能夠看到他我就已经很高兴了,虽然没办法听他亲口说出他所有过往的一切,顶多看到他含着泪水的眼睛,但这个场景就足以让我有很多的想象。
中间另外两位就是李张瑞和林修二,林修二1944年二战结束前就因肺结核早世,李张瑞则因为白色恐怖也在1952年就被枪决了,所以刚刚说到的那一位最老的成员杨炽昌,就是笔名“水荫萍”的那位,活到最老,1994年时才过世,但距离现在也已经差不多二十年。所以,我一点一滴地望着这些人的照片,看着他们的文字——一堆日文,然后透过翻译来转述跟再认识等等——那个感觉很奇怪。对我来说,这些人比其他的台湾人都陌生太多了,所以接触这些在书本里或报上出现的人的动态,我真的有一种非常“莫名”的感觉,就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理解这样一群曾经在台湾生活过的人居然会有这么大的距离?这是这个追寻一开始的某种相当奇异的感觉。
所以或许可以说这是从看见所谓的“他人”,开始进行想象“他人”的一段经验。“看见”这件事情好像很简单,但是进入它的内在时你会觉得很害怕,因为你开始觉得你是不是要帮它诠释和表达什么。而且这是一部纪录片,它有一个前提在,就是你认为它是某种真实的再现,即使这个再现未必是写实,而是一种重新诠释的可能。所以我觉得除了刚才说的一直背在身上的资金压力外,另外就是帮他人诠释的痛苦,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荷,因为你非常害怕说太多,而且说错了可能没有人知道。我好像对墙壁丢一个回力球,它不停的丢出去又弹回来,丢出去又弹回来,而这个弹回来的声音是我自己的,不是他们的。所以,从“看见”然后开始“想象”,开始进入“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他人”的过程是一件随时都感到不安的事情,而且非常惶恐。当我跟这些家属无数次的访谈之后,有些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慢慢长出血肉,描绘中的那些诗人的样子开始变得比较立体,有生命,不是悬浮在书和报章里面那样。而且他们留下的照片又这么少,所以很多时候你会不停的建立他们的“动态形象”,而那个想象也包含了他可能怎么说话,他可能怎么看事情,他的脾气和性格可能是怎么样的等等。但这里面也形成了一个拉扯,就是说我并不希望影片是一种剧情性的组织,也不希望它像一部“资料片”,这两端我都不要;但我又希望他们说过的话语或生活样态,即使很少,依然可以被连结进来。
在这为期三年的拍摄期当中,在私访的家庭里也陆续有人过世,甚至因为过世之后导致家人对这部影片、这个计划出现了不同的想法,而这些东西刚好又卡在我选择的一些虚构搭景里,所以大概就是在那个期间,真的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复杂,也不断思索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办法更好的呈现。我对书情有独钟,也认为这是当时对于风车诗社来说极为重要的精神介质,必须要把它呈现在影片里面,所以我也付出了一些相对的代价,就是要四处去寻找这些数量相当稀有的珍本,台湾没有的话我就到日本找,能买的就买,不能买就借,所以又会涉及到跟另一批人借时,你必须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借,为什么你要做这些事情,进入不断的解释以及翻译的过程。其实也因为这樣的过程,开始与日本学者有接触,开始去想日本人到底怎样看台湾这样的团体的存在。尤其当我发现日本学界目前为止对风车诗社也几乎一无所知时,我太惊讶了,因为风车诗社浮出台面到现在也有三十几年了,居然没有日本学者知道台湾三零年代有现代主义这回事。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也希望透过这部影片让殖民的宗主国意识到殖民地的人当时到底在做什么,反思这些过去的殖民地人民留下了什么。
大概是这样一个前提吧,田野的部分我们就发现资料十分匮乏,但从这些匮乏的资料要延伸、折射出去的范围又变得非常的大,因为它甚至可以折射到西方前卫艺术的部分,也可以折射到日本,甚至成为超现实主义的某种延伸性诠释。再回到台湾来,你突然觉得要把这些东西整合在一部影片里面,除了依赖匮乏的资料之外,还要面对非常大量的间接资料,所以这个过程中一直在反复筛选与回想,这些朴素的资料到底要怎样被转换到一个纪录片里面,而且这个纪录片还要跳脱过往的传记电影或者资料电影的模式,那么,这些访谈是不是能夠都不要呈现?资料的引用是否能转换成影音的元素?在这些考量过程中同样焦虑的是以最少知识背景或咨询式的內容來铺陈,会出现什么问题,以及观众可不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看纪录片?
目前为止,一些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给我们的回馈是“很难接受”,很难接受不标注来源出处、不放解释说明,这样让他们觉得浑身不对劲,而且他们甚至会质疑到底有没有做过访谈,以及这些访谈为什么没有放进来。我可以很放心的说,一部正常的传记影片该做的工作我们都没有少做,但一般的纪录片没有办法做的我们更努力去做了。所以我想这样影片的出现,也许反映出一段时间以来纪录片扮演的角色可能渐渐被定形了,也可能指出在这样的定形背后,是人们常常以为会在访谈中看到历史全貌的期待,或以为说只要找几位学者来访谈,呈现几个资料画面就可以被盖棺定论说这是所谓的“历史真相”。我在这个田调的历程中发现太多的未知,而未知是不是能被接受、并放到一个纪录片里面?这是一个关于保持开放性、需要观看者去再思考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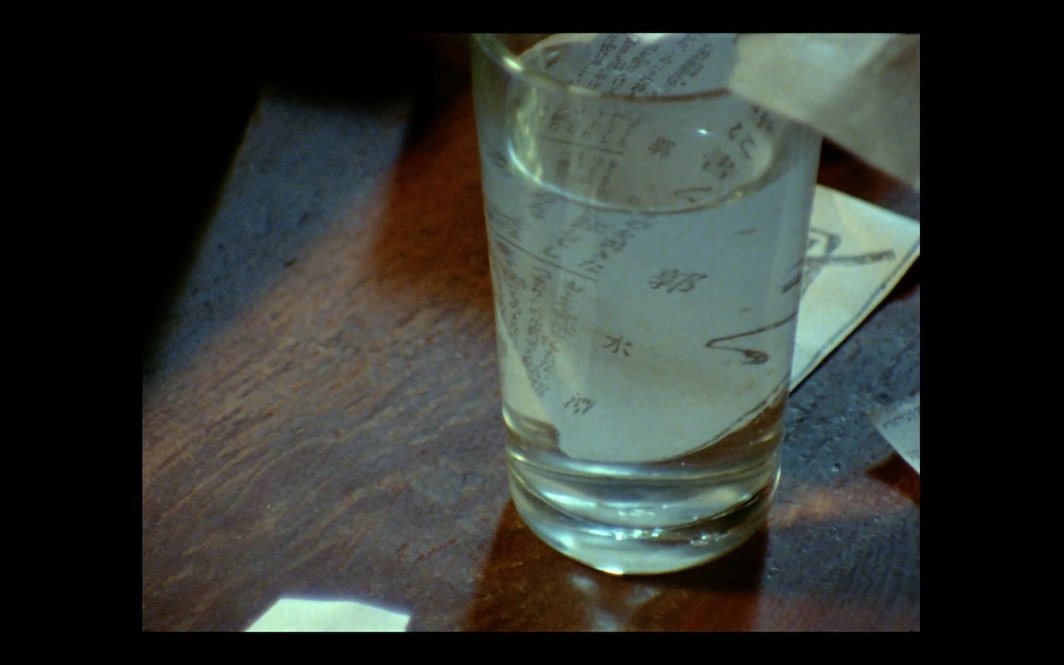
黄建宏:刚刚亚历导演大概跟我们讲了一下他做这部影片的历程。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导演设定了一个非常难解的问题:如果要去追寻风车诗社的痕迹,或许并不一定会那么困难,因为其实有一些研究者已经进行了一些工作,然后,他们也有一些家属健在,也可以从他们的话语里去获得这四个台湾詩人的相关痕迹。可是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亚历导演似乎有一些想要去探寻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其实非常模糊的游移在你读过的资料或者说你见过的家属之中。所以最后你的影片没有直接放入访谈,也没有直接以访问相关学者或引用学者的论述来作为画外音,我认为这与你的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观者可以在你的影像、所使用的音乐、图片中看到我们跟世界的某种结构或层面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我们在观看影片时会发现影片要拍的不止是风车诗社——我觉得这个搞不好是今天纪录片更为核心的问題:我们到底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的真实,如何需要找到新的起点,发明不同的方法。
另外一个则是在取镜以及这些图象里,我们可以感觉到好像交织着一个日治时期文人的生活样貌,以及他们碰触到的物件,虽然是虚构、重演的,可是也在诉说着那个时代的氛围;另一方面也会有一些相对遥远的图象,比如说普鲁斯特、波德莱尔的头像,或者红磨坊的照片,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它们似乎与欧洲三零年代,或者更早,一零、二零年代,比如雷尔内·克莱(René Clair)的《巴黎屋檐下》(Sous les toits de Paris,1930)那样的影片存在一种关联。这样的图象提示底下其实是复杂的,一方面好像是非常欧洲的想象,另一方面又存有日式阴暗空间状态下文人的作为,这个连结似乎在暗示这里面有某种“台湾经验”存在的可能。我不晓得你决定图象的原则是什么,以及当时你是怎么去思考这些问题的。
黄亚历:“跟真实说再见”这件事情其实很矛盾,在追寻的过程中我真的巴不得知道真实是什么,也就是说我希望不要用一个“符合写实”的方法呈现,但我又非常想要知道当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关心什么,他们处于現代性崛起的新时代下,写作的心境可能是什么。在影片已完成的几个月后,突然有一天我想到,假如有一天我突然看到诗人站在我面前,那不是太奇妙了吗?那是多么令人喜极而泣的一刻!这段期间对他们的某种想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情谊”。虽然这份情谊很单向,是因为我不断投入这件事情而慢慢发生的,它好像建立在我们可以看到的他们的那些东西之上,那些东西让你觉得某种程度上你们好像是“平行于同一时空”的,但它们却发生在一个受殖民的时代,所以其中的复杂性是汇合了众多层面的。在影片的创造性中把“真实”这件事情抛弃,以及不断尝试去追求某种真实,这二者在某些意義上其实是相当接近的,但似乎又能夠各自独立不相违背,这當中最重要的汇聚点或许就是來自对于主题本身的敬重。所以我想这也是纪录片在反观真实的面向里一个很迷人的部分:你跟真实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相扣的,而且甚至你知道有些东西永远无法企及,但你还是会努力去逼近。也许就是这样逼近的过程,许多的感受和对影片素材的判断,会逐步地累积下來。
刚才也提到有一些相关研究,但那实际上仔细去比对,你会知道就是“断简残篇”,这些东西随时各种未知的因素消失,消失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不见了,此外就是战后也蛮长一段时间禁止使用日文以及销毁日文档案,在这些过程里面,台湾失去了太多太多可以更了解那个时代的一些基本资料。所以就像老师刚刚提到说我到底用什么标准来判断、呈现,这其实也是许多观众好奇的问题。我记得建宏老师前一阵子跟我见面,他说现在的状态就是我放什么大家就信什么,但其实在几场放映中就有人告诉我说“你放的我都不信”,这个“不信”背后也许有很多的因素,例如:可能因为他是一个研究者,他的疑问包括“你为什么不放某几首诗”?“作为一部关于风车诗社的纪录片,你怎么可以不放那几首诗?”我觉得很有趣,相较于多数大众,这样一个团体跟学界的互动性是更高的,因此引起了很多台湾文学研究者的关注,我在几次放映上听到了很多不一样的观点。但学界的权威性是不是会和这部影片产生某种冲突?这里并没有不敬之意,而是说大家可以各自反思。
如果回到风车诗社的年代,我们会发现它不是一个单纯文学学科的事件,它处于一个各种表现领域都在蓬勃萌发的时代,不同领域的撞击自然会敲进这些现代主义作者的心里,所以我当然会因此考量应该放入什么影片素材,特别是作为一部纪录片而言,“电影”这件事是不可能抹去的。我也想知道当时的电影到底怎样触动这些作者。电影作为“着力点”可以支持我的表达,具有延伸性,所以我便把那个时代的一些影像放进来,比如《巴黎屋檐下》。其实之前我还蛮喜欢这部影片的,但看到杨炽昌的文章里提及这部影片时时我真的有点惊讶,没想到他们也看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与考克多(Jean Cocteau)的关系,对于他的偏好和迷恋,甚至偶像崇拜,这些事情也令人感到非常奇妙。尤其是我看到林修二去横滨的码头送考克多这一幕时,其实真的蛮感动。这些诗人跟电影的关系好像因此变得很密切,虽然我没有办法从他们的资料里得知他们到底看过考克多的哪一部电影,或者纯粹就是看他的文字、听他的唱片,但我可以进行延伸,帮他们做某种程度的“图像编织”,基于我自己的想象,而所有的想象都建基在某一些基础点上——影片中大部分的表达,主要是建立在相关的口述记录或文献上,以及建立在对他们曾经表述过的文字的想象上。
有的朋友反映说,“看完这部片觉得没有观点”,我真的大为吃惊,不知道“没有观点”是怎么样的一种观点。我想这也跟我们长期习惯纪录片里面存在一个不断告诉我们、引领我们下判断的主导声或陈述有关。我在想这是不是也回应了纪录片表达形式的某种惯性,或者是长期以来被要求以某种形态来进行诠释,进而才能符合所谓“典型”纪录片的样子,所以我也欣然接受这些批评,但更希望藉此开启一场对话:到底一部纪录片应该具备什么特质或铺陈方式?集结了众多影音特性、生命经验、历史情感或政治立场等各种复杂因素之后,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纪录片的想像会演绎出什么样貌?帮助我们诠释历史、文学的纪录片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的?
对于这部影片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虚构的部分要表达到多少才不会“越线”,也就是不去做太多“过分”的判断,尽可能根据相关访谈里提到的內容进行虚构。拿捏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耐心的考验,出于对于当时历史状态的尊重而决定到底要“推测”到什么程度,因为在这部影片里我认为“不越线”远比“过分武断”来得更重要——与其说看起来好像有非常高的创作自主性,但其实从头到尾我前所未有的感到不自由。这也跟过去的拍摄一般短片的经验截然不同,在拍摄过程中我常常意识到,以前是那么自由,想要拍什么就去创造出來,但这部影片不是,每创生一个东西出来都要有充足的合理性去支撑它,甚至你必须反复去询问家属是否确定就是如此,不停地确认。大家应该可以想象这些家属年纪也蛮大的,所以他们的记忆也常常会有一些变化,上次问他的事情可能下次就会说“我没有这样说过”或“好像不是这样”,所以“真实”一直在以一种不完全确定的记忆中变化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提醒着我们,三零年代的历史对于当代来说,其实已经非常急迫,那种急迫包含了记忆力的流失,是生命的流失,很多东西也许未来十年就找不到了。我们还有多少没有被注意到、被埋没在历史灰烬中的故事?还有多少也许在短暂几年内就会再也听不到的声音,以及被再度转述的可能?
影像命题对我来说是一种历史诠释及其与影音关系、创造性的结合,所以有时我希望让创造性先行,有的时候我希望以历史问题先行,这个拉锯和拿捏的过程很有趣,既快乐又痛苦,这些隐藏在结构中的判断标准也说明了这部纪录片的种种观点。我也必须说,自己甚至想过用更绝对的方式来处理,就是让作者的直觉先行于所有的历史素材,但后来发现做不到,这个想法在计划的第二年、第三年就逐步放弃了,反倒把对于历史素材的尊重推到最高的地方。我想这也是一个跟过去的拍摄经验具有非常大差异的地方,这是一个不断反思、不断面对的过程,例如说引用的很多素材是别的作者的素材,那你要如何处理使用别人的创意这件事?所以我认为在影片里出现的作品都是心血的结晶:让它们在我的影片中出现,某种程度上成为我的诠释,因此在使用这些素材时我特别小心,甚至希望可以征得还能联系得上的作者的同意。
文/ 黄建宏 黄亚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