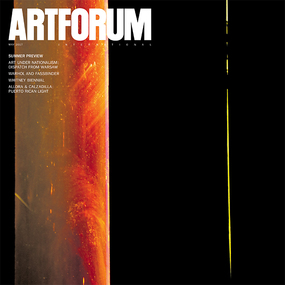将于5月13日开幕的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是在各种地缘政治的湍流中展开的——物件、思想和自我的生产都在经历着巨大的转变。策展人克里斯蒂娜·马塞尔(Christine Macel)和艺术论坛主编郭怡安(Michelle Kuo)就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展览的工作过程和脉络展开了对话。

郭怡安(MK):你策划的这届双年展的主题“艺术万岁”(Viva Arte Viva)从字面上看也真的是把艺术(Arte)放在了生活(Viva)中间。
克里斯蒂娜·马塞尔(CM):这个展览是把艺术和艺术家放在首位。这是所有一切的开始。
大部分的双年展不是这样,一般都会是从一个主题开始,然后挑选出一批艺术家。我觉得大部分时候展览概念都会过于宽泛,于是展览也就变得无比宏大;威尼斯双年展的场地面积加起来有50000平方英尺,所以让展览看起来有连贯性就变得更难。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你选择了一个很具体、明确的主题,就会让艺术家失去创作的自由度,他们和策展人之间也很难产生真正的对话;整个过程变得很专制。
所以我没有选择一个单一主题,而是和艺术家紧密合作,去进一步思考他们自己的实践,他们创作的方式,他们所选择的立场,他们的创作环境——包括从材料到工作室再到智性思考:他们的灵感来源、知识、研究,以及受到的影响。
我请每一位艺术家都提供给我一些档案:图像、书单,甚至包括个人阐述。我就是这样开始着手展览和画册的调研工作的,最后我请每一位艺术家都制作了一个关于他们自身实践的视频。从二月份开始,我们开始在双年展的网站上陆续发布这些视频;展览现场你也可以看到这些视频。
所以整个展览都是在密切地关注和探索艺术家所处的位置,他们的工作室、历史、环境等等。跟这些创作者在同一个层面工作,在他们各自的创作范畴内一起工作。
MK: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是在展览现场重现艺术家的工作室。
CM:你说的对。实际上展览的第一个部分是邀请艺术家就工作室这个概念来创作作品,让这个概念变得可以为人理解。
MK:所以是对这些情境的思考,而不是重现它们。
CM: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多恩·卡斯帕(Dawn Kasper):她的很多作品都很明确地是和她的工作室实践相关。
MK:她的表演作品很多是在呈现她的创作过程。
CM:实际上她提出要在威尼斯住上六个月,这太疯狂了,你可以想象。她搬了过来,她也会把她住在这里的经历变成视觉化的呈现。再比如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他会展出跟他的巨型工作室和实验室相关的同样巨型的一件作品。这个部分是关于对生产的不同切入角度。
MK:或者非生产性。
CM:我很感兴趣艺术家在生产和自我反思之间的生活中的张力,那些“悠然”(otium)的时刻。“otium”这个拉丁词常常被翻译成“休闲”,但实际上它指的是一种闲暇时间,一个无所事事的时刻,一种非活动状态,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有生产性的,这个时候你实际上是在吸取营养。
在古典传统里,“otium”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须,和“negotium”保持平衡,这个词现在常常被不精准地翻译成“事务”,但实际上它指的是一个城邦的世界。崇高意义上的政治:对公共生活负责,为大众的利益服务。
这种内和外、非活动和活动、个体和社群之间的辩证关系——你如何去平衡这相对的两端——是现在每个艺术家都在面临的问题。举例而言,弗朗茨·韦斯特 (Franz West)就很明确地宣称犯懒是必要的,游游荡荡,跟人聊天,什么“正经事”都不做。“otium”这个概念挑战了与资本主义系统下工作及其后果相关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定义。它质疑了工作作为社会核心活动的地位,也质疑了休闲或者娱乐的经验——虽然不是工作时间但也毫无疑问地被资本化了:那就是花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想法和奥奎·恩维佐(Okwui Enwezor)2015年的那届双年展有一定的相关性。
MK:这种闲暇时间的形式是对抗今天生产的速度或者加速的。展览里有卡斯帕这种花六个月时间在地创作的艺术家——项目展开的时间跨度是很少见的。
CM:会有几个艺术家或者是艺术团体在威尼斯待比较长时间。比如李明维也会组织一个长达六个月的表演。这个展览不是只集中在单个的活动,而是非常关注基于时间的实施过程。
MK:你还策划了一个活动叫做“Tavola Aperta”,或者说开放餐桌,定期在户外和艺术家一起用餐,任何人都可以加入。
CM:我刚刚接触艺术圈的时候,你会随便走进一个餐厅,坐下来聊艺术,这很常见。但现在这个传统似乎消失了。所以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每个周五和周六,我们都共进午餐。几乎所有艺术家都答应参加,这点挺棒的。天气好的时候餐桌会摆在户外,在主题展馆外面的花园里。还有一些会安排在军械库里我们重新整修过的房间里。我也邀请了所有国家馆的艺术家参与。这变得有点类似去拜访艺术家工作室,帮助我们和艺术家建立起联系,不仅是作为策展人的我,包括普通大众也可以听到艺术家们的声音。这是一种试图改变展览和艺术家、艺术家和观众之间权力不对等关系的努力。
我不认为这些活动只是为了了解这些艺术家的生平和工作。我觉得它们可以生产出可供进一步研究分析的材料。如同建立起一个在展览后仍可持续的档案库,让我们有更多方式可以去了解影响了这些艺术作品生产的实践的多样性。

MK:环绕在周围的一切。
CM:这也是作品的一部分。你不能把作品和日常实践区分开。这也是为什么我最终是把这个展览构建成一个从内部走向无限的通道:九个展馆从情感上最为私密的过渡到最有距离的,通往精神性和科学。
我希望这个展览是一段旅程,一次演进。我希望在看完展览后你能感觉到自己内部发生了一种转变。
MK:这和你提的“新人本主义”(neohumanism)相关,或者说是对人本主义的再创造,这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个走向,和反人本主义(antihuman¬ism)以及后人本主义(posthumanism)背道而驰。
CM:我认为它是对文艺复兴以及1960、70年代乌托邦想象的失败的承认和反应。一个世界的失败,以及被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描述成“液态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的通往一个新世界的通道。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稳定感激增的时代,一种现代性的无序版本。现在,“液态”的人必须时时作出选择,不停地适应新的环境,成为没有实在坚持的流浪者。
为了挑战这种现实,我决定着眼个体艺术家是如何在历史中发展的,以及我们可以如何发明出更多透过历史的眼睛看待当下的路径。每个展馆里,我都选了一些人作为历史性的骨架:一些被过早遗忘的艺术家,可以被再次讨论的艺术家,或者是和当代思想以及艺术家产生共鸣的艺术家。比如在艺术家和书籍馆(Pavilion of Artists and Books),我选的是约翰·莱瑟姆(John Latham),他所有关于出版物的作品;在喜悦与恐惧馆(Pavilion of Joys and Fears)馆,我选了Tibor Hajas——一位杰出的匈牙利艺术家;大众馆(Pavilion of the Common)里是意大利艺术家Maria Lai,我曾经在2015年于西西里巴勒摩(Palermo)策划的“中间的中间:地中海地区的当代艺术”(In the Middle of the Middle: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Mediterranean)上展出过她的作品;在土地馆(Pavilion of the Earth)里是日本的艺术小组The Play。
与其简单地去挖掘历史,对我来说问题更像是,我们做过什么?现在我们可以做什么?
MK:哪些模式可以再次被激活。
CM:不仅仅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也包括个体经验。
MK:这有点像是说,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谈的都是反人本主义,现在我们必须找到一条不同的路来思考个体的问题——这并不意味要回到那些旧有的、过分天真的有关主体的概念,而是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类依然存在。我们还在这里,而且我们显然还在通过我们自身主体性的棱镜来体验这个世界。
CM:是的。我们现在可以如何理解去个体性以及具有个体性的主体?我们如何在一种人本主义失败之后重新发明一种新的人本主义?我相信强个体性,这就是为什么我选的艺术家都很不一样,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带来一股独特并且强烈的能量。
MK:在土地馆,你把这个问题放大了,探索个体如何和土地的广阔发生关联,或者更准确地说,如何和人类世(Anthropocene)发生关联。
CM:我设置土地馆是因为我选的所有艺术家在某种层面上来说都很关注这个议题。他们中一些是行动主义者;一些只是把自然当作创作的环境。我们会重新激活一些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的的实践。其中一组核心作品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艺术小组OHO(成立于1966年,一直到1971年都工作和生活于克拉尼和卢比安纳)。在那个时期,他们组成社群并且生活在大自然中——创作了一些表演作品,并且关注一系列生态问题。他们大概可以算是某种嬉皮。虽然后来这个小组解散了,但是所有的成员之后都还是在关注同样的议题。这对他们来说不是一时的风尚。他们希望可以在自然和社群之间建立连接,并且坚持它和个体间的平衡关系。它不属于大地艺术。他们是以一种更加神秘和精神性的方式同自然发生关联。

MK:他们有搭建什么吗?
CM:他们的作品是那种短期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是季节性的。我会展出他们的“夏季项目”(Summer Projects, 1969),这是他们夏天的时候在野外做的一个项目,把塑胶袋甚至卫生纸缠在树上。很不正式,而且也从来没有生成任何确定的物品或者其他纪录形式。类似地,The Play将要重现他们1970年代的一件作品。他们会在军械库那儿搭一个房子,让它在运河上漂流。
还有更年轻的一位艺术家山姆·勒维特(Sam Lewitt),他的作品和电力以及能源有关。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ENEL)是双年展的首位赞助商,他们同意出借一批他们早期的灯具供艺术家扫描和制模,这会是一件很有活力的作品。
MK:这些作品重现和贯穿双年展的新的表演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CM:开幕几天里每个钟头你都有东西可看。包括安娜·安普林(Anna Halprin)、埃内斯托·内图(Ernesto Neto)、蒙德里安粉丝俱乐部(Mondrian Fan Club)、Mariechen Danz、Nevin Aladag、Paulo Bruscky等人的表演。这些都会在双年展的网站上同步播出,也会在军械库的一个房间里播放。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实时地看到,而且之后也可以在我们的档案里找到。
时长本身也是展览的终章所关注的,那就是时间和无限馆(Pavilion of Time and Infinity)。这里很多作品都将是基于过程的,就像是伊迪丝·德克伊恩特(Edith Dekyndt)的作品,她非常着迷重复和变异,记忆和差异。她的表演作品会是一个人试图把尘土摆成一个长方形,但这个长方形是由不断移动的光画就的。六个月的时间里,表演者会不断地试图重新画出这个长方形。于是在展览结束的时候,你会遭遇无尽的循环——一种永恒的回归。
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艺术万岁”将由5月13日持续至11月26日。
文/ 克里斯汀·马塞尔 | Christine Macel,郭怡安 | Michelle Kuo
译/ 郭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