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B大道和C大道之间的东二街外面是曼哈顿最大的露天毒品市场。平常这里一片死寂,只能听到毒贩们此起彼伏地叫卖各种名字的毒品:“3-5-7,3-5-7”,“厕所,厕所。”站在Kenkeleba的台阶上,望向对面的毒品注射场地,可以看到一排排黑黢黢的窗户和砖砌的外立面,仿佛没有门的入口,通往阴间。毒贩子是怎么进去的?街上几乎没什么车。Kenkeleba门口两侧的柱子背后出人意料地藏着一座以前的波兰婚礼礼堂,现在,这座优雅的残破建筑属于波西米亚黑人夫妇科伦·珍妮斯(Corrine Jennings)和乔·奥福斯特利特(Joe Overstreet)。

画廊一共五个房间,从街面上看不到,其中一间黑魆魆地如同洞窟一般,再加上过道,要把整个空间都用上实在是一项挑战。这个场地对于“中产阶级黑小姐”(Mlle Bourgeoise Noire,译注:八十年代初,格拉迪在其最著名的行为表演中扮演的角色,艺术家身上挂着很多白手套,拿着一根九尾软鞭,突然出现在展览开幕,在现场朗诵诗歌,批评当时温驯的黑人艺术以及艺术机构存在的种族隔离现象)野心勃勃的策划活动来说简直再合适不过:三十名艺术家参展,一半是白人,一半是黑人,作品也只有黑白两色。色彩的剔除强调了共性,抹平了差异。在当时依旧“黑白分明”的艺术圈里,这将是第一场黑人艺术家在数量上与白人持平到可以对话的展览。开幕的突然意味着我们只有三个星期的时间准备。当然了,钱是没有的。但让·米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的作品像吉祥物一样被选进惠特尼双年展更让人觉得雪上加霜。除此以外,驱使我走下去的还有每天经过那片街区必需的勇气,那里就连空气都非常诡异——黎明的感觉就像黄昏。种族不会写在标签上。那么它会出现在墙上吗?如果是,又以何种方式?我想亲自找到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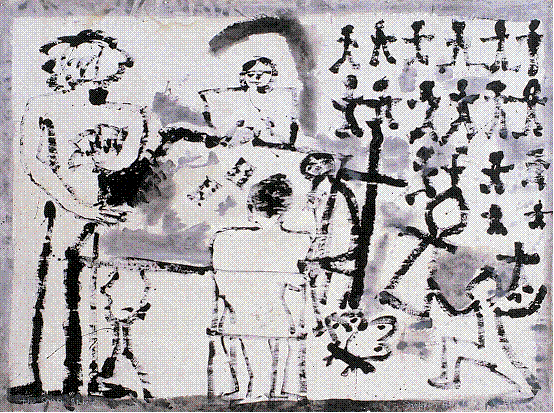
凯斯·哈林(Keith Haring)旁听过我在视觉艺术学院(School of Visual Arts)讲未来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课。我先给他打了电话。然后找了巴斯奎特,当时只能用电报跟他联系。再给那孩子一次机会!但巴斯奎特一开始答应为展览创作两幅作品,后来又中途退出了。还是布鲁诺·比绍夫贝尔格(Bruno Bischofberger,译注:与巴斯奎特关系紧密的画廊主)的需求更重要。沿着东二街走下去就像穿过一堆一堆被搁置的梦想。我找来壁画家约翰·费克纳(John Fekner),希望他能把展场内部和外部连接起来。纽约下城区有各种各样的人才和创作流派,其中一些被急着进来套现的大军忽略。展览最后召集到二十八名艺术家,他们当中很多人还在担心一夸脱的镉红颜料批发价要三十二美元这种问题。每天我走到附近的时候都会想,“我要的壁画呢?”开幕前一天,壁画上墙了。约翰凌晨四点起来画的,四点,连毒贩们都还在睡觉。
画廊内部的效果也令人满意,虽然汇集了这么多不同的风格,图像仍然传达出一种清晰可辨的语言。但谁会来看呢?和Kenkeleba比起来,Gracie Mansion和Fun Gallery(译注:八十年代初纽约东村活跃的两个实验性艺术空间)简直就是SoHo。也许东二街和东十街之间的距离太大,根本无法弥合。答案是那些了解“圈内人”不会打搅“普通百姓”的朋友和东村人士。找艺评人来看展比登天还难。只有《东村观察》(East Village Eye)登了短短的一段话报道这次展览,除此以外就再没别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参展艺术家后来的职业命运差别很大。有的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有的消失得不留一丝痕迹。其中一部分人让我忍不住想,如果当初有人愿意出钱或者关注这些作品,他们的创作又会变成什么样?每时每刻都有这么多不同的趋向同时存在。在当下压缩过去的过程中,我们丢掉了什么?当我们将过去用丝带打包以便向未来进发的时候,什么东西消失了?那样的结果是必要的吗?又是真实的吗?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