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是一家独立的研究机构,位于德里北部树木葱郁的街区一隅,在这里的图书馆墙上,挂着一只奇怪的时钟,钟面上没有数字,取而代之的是在令人不安、稀松平常和富有启示性之间摆动的一连串情感名词:焦虑、责任、罪恶感、淡漠、敬畏、疲倦、怀旧、狂喜、恐惧、惊慌、悔恨、顿悟。
该中心成立于1963年,专门支持协作性和跨学科研究计划,很多项目都跟进步的社会运动有关。中心的研究旨在挑战“任何关于现代性的单一概念以及发展与进步的已有模式”,同时强调“在多样、另类的现代性形成过程中,对本土传统的创造性运用。”将上述时钟放在这个机构储存知识的核心地带,既宣告了这些研究项目的及时性,又表明了它们的脆弱,突出了一个历史性时刻的焦躁特征,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文化身份的稳定坐标似乎完全不存在。钟表记录着当下对知识的创造性使用所包含的情感风险,因为它很可能被任何志同道合的用户群体分配和分享,也就是说流通于当代不同的公共资源库之间。如此看来,这个钟表在Raqs媒体小组(Raqs Media Collective)网站主页上也占据了显要位置就毫不奇怪。1992年,理论家、媒体实践者、艺术家吉比什·巴什(Jeebesh Bagchi), 莫妮卡·纳如拉(Monica Narula),以及舒德哈巴拉特·森古普塔(Shuddhabrata Sengupta)三人在德里共同创立了Raqs媒体小组(当时三个人还是国立伊斯兰大学传媒系的学生),在他们的创作中,艺术的集体性与公共资源本身的命运是分不开的。而这只脱离了实体研究机构,同时也不再受到重力束缚的电子时钟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了Raqs的标志,面向德里知识界以外的群体,提示我们关注在不同“地方”以及在线上不同群体之间生产和共享的知识今后将面临何种前景。
若要理解这些前景——以及Raqs的项目整体,就有必要以更广阔的视野去看待艺术和集体主义之间的联系,以及后者在今日语境中的不同含义。在艺术界对所有“政治”事物的持续关注中,集体是一个常用不衰的套语,其意义可以关涉到共同享有的资源、实践和目标。但尽管其在前卫艺术中的谱系建立于1920年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俄国构成主义)与1960年代(艺术工人联盟),如今重新收复失地的集体却不再具备任何旧时共产国际风格的美学特征。虽然它们的行动主义使命可能还保存完好,但今日的集体对公司逻辑的模仿可能更胜过对合作社的模仿,智库给他们带来的启发可能更胜于工厂车间——就像是通过代理追踪自由市场的不规则流动。如果说我们不幸处在包括路德维格·梵·梅塞(Ludwig von Misers)和肯尼斯·阿罗(Kenneth J. Arrow)在内的经济学家所说的“消费者主权”时代——客户兼市场掌控一切的新自由主义梦想国——那么此类集体活动的迅速增加也就不需要解释了。即便如此,这类新的集体的出现——它们往往倾向于批判地挪用与官僚主义议程相一致的组织形式(比如the Yes Men, the Center for Land Use Interpretation, Bureau d’études)——仍然代表了一种显著的转变,偏离了我们原来对集体与其意识形态立场之间的关系的历史想象。
集体主义早期模式和如今的做法之间是存在不同的:一般而言,过去的集体利用的是支持或反对某个特定政治规划的表象,可见度是他们的战略武器之一,而如今的集体实践往往在本质上是晦涩的,在共同利益的协商上是隐秘的,对代表性政治本身抱有深刻的怀疑。当然,鉴于当下形势,这也可以理解。公共领域——任何公共资源概念的基础——被消费者选择的风气掠夺得越厉害,“用钱包投票”的心理对参与性民主语言的侵蚀越严重,集体的命运就越显得利害攸关。于是,集体vs.个人的古老剧情又有了新的发展:在该叙事的最新版本中,消费者主权个体——个人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的化身——经由法令认可统治公共资源。而集体则讽刺地拒绝共享该过程。但这种拒绝并不等于承认消费者主权个体的圈地哲学,而是试图绕过,从而重新想象资源共有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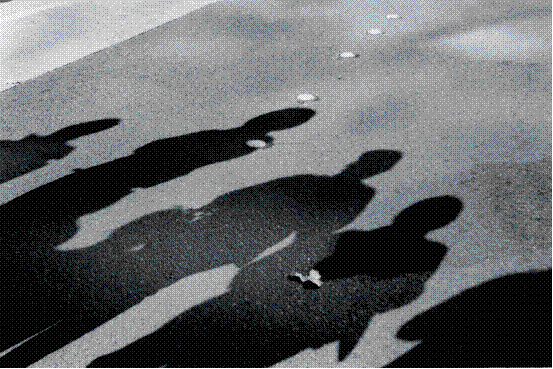
Raqs媒体小组就是如此。Raqs是英文“很少被问到的问题”的首字母缩写,精辟地反转了无数网站都有的“常见问题”(FAQs)页面:对于该小组来说,这些问题指向的是分享什么,以及如何分享。“占有某物的方式只有一种,但分享它的方式可以有无数种。”2006年,巴什、纳如拉和森古普塔在他们图文结合的文章《一个共产主义者哀叹的碎片》(Fragments from a Communist Latento)中这样写道。换句话说,公有物的多样性挑战了占有物(财产)的单一性。显然,这一主张区别于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1968年发表的文章《公共资源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中的新马尔萨斯宿命论,哈丁在文中简述了即将到来的人口爆炸和资源枯竭的灾难。他以牧民放牧的公地为例,论证了控制公地的必要性。Raqs则表明,我们离这个模式已经走出了多远。该小组的实践在公地的领地要求以及限制进入公地的所有权保护措施之内和之外同时展开。在动用大量新旧媒体的装置作品中,三人小组惯常处理的议题包括数字公共领域,全球化压力下的通讯与传播,异步的现代性经验(比如2007年的装置《时间书》就用了四个废旧的工厂时钟,令人想到按小时、分钟、美元计数跟踪工人生产力的工业化任务),以及与之相关的移动与错位的政治(比如2017年的作品《计划有变》[There Has Been a Change of Plan] 就是四张飞机的照片,其中一张上的飞机机头不见了,如同一次航空斩首)。尽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Raqs的艺术仅限于这些主题。恰好相反:该小组的回应是完全开放的,正如他们的视觉修辞是简短晦涩的,也验证了学者劳伦斯·莱辛格(Lawrence Lessig)在《思想的未来:互联世界里公共资源的命运》(2001)中所说的,“不知道资源将如何被使用”未尝不是件好事。
与这种多样化和开放性相一致,Raqs媒体小组——尽管近十年他们已成为国际双年展的主力军,2002年参加文献展,2003年和2005年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而巴什、纳如拉和森古普塔还是去年宣言展的六人策展团队的一部分——的实践也跨越了艺术界内外。三人也是新媒体计划Sarai的活跃成员,该计划是他们1998年跟瓦苏德文(Ravi S. Vasudevan)和桑德拉姆(Ravi Sundaram)共同创建的,后两位都是媒体和都市主义研究的学者。而小组名称的延伸含义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不同活动领域之间边界的模糊。Raqs,除了意指“很少被问到的问题外”,也是一个波斯语、阿拉伯语和乌尔都语单词,表示“跳舞”,但更多地表示托钵僧人转经时的状态。考虑到这个团体所居住的重叠和嵌套空间——德里散乱延展的城区、数字公共空间的虚拟领域、全球艺术界高大上的展场——这个名字是对媒体循环递归漩涡的绝妙比喻,而媒体既是他们作为艺术家工作的平台,也是他们的探索对象。
Raqs的成员会告诉你,艺术界对集体主义的迷恋是对一段波澜壮阔的过去的感伤怀旧,投掷石子和冲击路障的图像无法抓住集体主义在当代化身的平凡而隐秘的面向,及其激发的对公共资源的重新想象。一方面,受媒体驱动的集体性也许跟维基百科或脸书上的诸众一样平凡;另一方面,支撑此类社会网络的规则有其黑暗的一面。正如近期关于新纳粹社交网络站点的报道所示,共和党里的极端分子几乎和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一样精通技术(后者经常被Raqs指认为无首领分散化组织的典型代表)。或者想想文件共享这种无处不在的做法,对一些人来说,这种做法可能与重新分配GNU源代码一样具有行动主义或社区精神;对另一些人来说,它与表达文化混合的艺术平台一样具有创造性;对其他人来说,又或许跟Napster上的P2P网络一样具有被控告或导致分裂的风险。由于这些媒体的用途,以及它们表面的开放性和透明性,上述例子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作者身份、使用和分配、控制和创造力的政治伦理问题——这些问题与公共资源和公共领域的根本性转变息息相关。上述一切都仅仅是这一转变所涉及的巨大法律问题的冰山一角。包括莱西格的“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和“公共版权运动”(Copyleft ovement)在内的各种活动都挑战了版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的局限性,使人们普遍意识到围绕代码私有化的辩论及其对信息-平台和内容的垄断和控制的影响。
对于上述宽泛的议题,Raqs采取了间接而多层次的处理方法。首先,快速过一遍Raqs作品就会发现,传统的公共空间被撤销了,就像影子和模糊、找到又丢失的东西、被屏蔽的信号、秘密特工、无法进入的空间等看似难以捉摸的图示结构所传达出来的那样。在这个时代里,个人被简化为“生活方式共识”的仲裁者——也就是消费者主权个体——似乎是为了回应这一时代现状,Raqs令其艺术中充满大量幻影,如同鬼魂在公共资源被掏空后的废墟上翻找残留物。在《丢失的新鞋》(Lost New Shoes, 2005,)中,是成堆的空球鞋,主人不知所向——矛盾地以非常干净的手法概括了被迫移民和集体剥夺的地缘政治反常状态。在录像和声音装置《A/S/L(年龄/性别/地点)》(2003)中,印度呼叫中心的女员工成为远距离沟通的中介,做着口技表演,试图融入英语的口语节奏。《鬼故事前言》(Ghost Story, 2005)是一系列黑白图片,讲述了“一个不知名的公民”跳楼自杀后留下一份给“影子聚会”的“临时档案”的故事。而在《候车室里的冒牌货》(The Impostor in the Waiting Room, 2004)中——这是一个由灯箱、投影、声音和一封1831年印度改革派民族主义者拉姆·莫汉·罗伊(Ram Mohan Roy)抗议其法国签证第十三次被拒的信的摹本组成的装置作品——由一个戴着礼帽、背对观众的人物占据的候车室的形象,暗示了一种与现代性的潜在相遇,门外的大军急于想进来。
所有这些作品都在诉说一种不安分的存在,不是完全在那儿,也不是完全缺席,而是游走于某个未知的中间地带。这种美学与代表公共资源传统智慧的透明性、直接性和可及性逻辑相反;但它也暗示了这种阴影可能可以为工作和生存的提供掩护。当然,Raqs的创作呈现与其他艺术家团体偶尔表现出的好战形象是不一致的,其中一些团体给人的印象是,在他们集体努力的背后有一个自负的(甚至是英雄主义的)代理人。Raqs并不认同这样的模式,但它也没有浪漫化支撑其主体的边缘性的条件。相反,这类作品预示了Raqs实践另一个侧面的分散性和分布性——即他们在Sarai的工作。如果说Raqs的主题开始看起来是神秘的,甚至是玄奥的,那么Sarai的项目则揭示了一种媒体方法,潜在性在其中确实胜过了显像和宣言,而公共资源在其中既是分散的,也是共享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描述Raqs和Sarai的分工,那么可以说一个提出主题,另一个则致力于实现。Raqs相当于其成员基于媒体的探索在艺术界中的代理。只有与Sarai合作,通过Sarai,在Sarai内部,Raqs才得以于媒体和技术精英投下的长长阴影中重塑公共资源空间。

Sarai位于Raqs时钟安置的研究机构——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的地下室,这是一家非盈利组织,它把自身定义为一个“关于当代媒介和城市聚落的研究、创作和对话空间。”桑德拉姆和瓦苏德文这两位学者担任总监,他们和巴什、纳如拉、森古普塔一起创办了该空间。Raqs和Sarai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架构上都密不可分:“Raqs”意为鲜被关注的问题;Sarai则为集体性思考提供一系列实际和虚拟的空间。这些场域包括在CSDS的实验室,那里接待来自南亚和国外的学生以及访问研究者;创办了关注如“公共领域”和“日常生活的城市”等议题的年度专题出版物,其中既有知名学者的文章,也包括新晋思想家的写作;与其他以媒体为基础的计划之间展开合作,比如阿姆斯特丹的Waag Society;以及——在公众资源领域内——通过免费软件的应用和开发产出用户生产性内容。
虽然Raqs早在Sarai之前就已经成型,但通过描述前者如何催生了后者的出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Raqs是“集体性”的。Sarai这个词指的是在莫卧儿时期为商队和旅客修建的驿站。对于一个研究德里都市生态学的项目而言,这是个十分恰当的名字——不仅让人联想到将德里城市内外不同社群有效连接起来的网络式建筑,同时也反映了数字媒体的流动特性。Raqs的成员在1990年代时是纪录片和传播学专业的学生,他们对于在整个城市发生的“媒体空间的重新整合”印象深刻,并将其视作一个关键性的时刻。1998年,德里街头发生了自发性游行,抗议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试验,但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同样重要但更为隐秘的都市变化也在悄然萌生。2006年,Sarai在与Mike Caloud的一场对话(最初发表在Rhizom.org上)中回忆道:“公共电话亭将自身变成了街角的网吧,独立电影人开始组织论坛性质的活动,更不用提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开放资源和免费软件社群….电子公告板。”
无论对于Raqs还是Sarai而言,这一叙事的关键在于混乱是酝酿创造性的温床。人、技术、空间和事物之所以能够快速汇集,恰恰是因为缺少规范。Sarai对这一时刻的描述中充溢着某种突然迸发的即兴感知力,他们称之为“再生经济”(recycled economy)——媒体的重新功能化使得旧与新交替循环,也凸显了被剥夺反而孕育出创造力的一面,通常是通过剽窃等行为。换言之,这段历史体现了围绕着获取媒体使用权及物质资源的赤裸裸的不平等,而这一切正是南亚地区时时刻刻在发生的情况。当然,这并不是一个Napster 式的故事。Sarai也不是那个无人不知的故事里偷偷下载Metallica音乐的十三岁美国郊区小孩。也许“数码落差”(digital divide)是欧美关于数码文化的对话一个看似不可避免的结局,但是,是否拥有这种特殊资源的问题几乎无法与印度的现实状况相联系——无论班加罗尔(Bangalore)作为硅谷次大陆解决方案的形象是多么深入人心。
Sarai的历史表明了通过网络空间转译的公共话语发生了更深远的转变。在《公共资源的悲剧》中,哈丁认为,曾经的田园生活会变成悲剧,不仅因为资源的匮乏,也是因为对自由的滥用。矛盾的是,恰恰是自由给公共资源造成了破坏,而哈丁对此类危机充满争议的回应中包括了如人口控制等令人反感的提案。但是,对于他今日的一些读者而言,“自由”意味着扩大一个人获取共享资源的特权;对资源的控制——现在是通过对私有化的疯狂追捧——被认为是与公社式愚蠢做法相逆的唯一道路。(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发展中国家水资源私有化背后的恶性逻辑,以及如国际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对此给予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当我们面对的是数码媒介这种无限更新的物质时,自由的测算标准就变得大为不同了。正如莱辛格在他2004年出版的《自由文化:创造力的本质和未来》(Free Culture: The Nature and Future of Creativity)一书中详细论述的,信息不仅“想要获得自由”——据正在崛起的信息时代的权威们所言,而且他们还将其理论化为“后匮乏”时代的乌托邦战争。免费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的创立者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思想的未来》中引用了他的话——说得更为直白:“Free”的意思“不是免费啤酒,而是言论自由意义上的”。在消费者主导的时代,公共利益被妖魔化为福利国家的等同物,让人不免想把这种说法再往前推一步:自由并不意味着自由市场,而是意味着自由的文化。
莱辛格和他突破性的“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组织为自由文化运动提供了合法性,而且预见了创新和互联网的双重未来——其所依赖的正是对编码的使用权。掌握了这个资源的政府还是市场并非重点。问题是通过目前通行的版权法的形式所实行的控制是否对媒体有意义,其递归属性必然超出了这些版权限制,其合作和共享的文化也是其技术发展的开端和结构性基础。在《未来的思想》中,莱辛格讨论了Unix类操作系统的发展历程,以Linus系统为例——这是此类操作系统中的“黄金标准”——促生了互联网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些变革,这些发展之所以能够出现,不是因为源码是被管控的,而恰恰是因为它是开放的。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对互联网实施管控只会成为创造力的障碍,无论是技术上的更新还是新软件的传播,再或者新的文化形式的生成。莱辛格写道:“这是现代民主的不变规律,即,当你创造出一套管控机制,就意味着你创造出了一个被影响的靶子,而当你创造出了一个被影响的靶子,那些占据了有利攻击位置的力量都会集中火力对准那个靶子。”
似乎为了疏通这种特定的逻辑怪圈,Sarai在多个不同的项目中都采用Linux作为创造数字公共资源的工具,以“Cybermohalla”(2001-,mohalla可以翻译为社区)项目为例,这或许是探索德里城市秘密角落和街头符号学的最为成功的尝试,借用Sarai自身最偏爱的说法,其独一无二的“媒体城市”(media city)。他们还与德里的的NGO组织Ankur(替代性教育组织,Society for Alternatives in Education)合作,在贫民窟设立了四个媒体实验室,在那里,Ankur与人们建立联系,提供技术训练,并以此支持对这所城市本身的研究和探索。
在这个光谱的另一端,Raqs构想了一个名为OPUS(无限意义的开放平台,Open Platform for Unlimited Signification)的平台,并与Sarai的几位研究员合作实现,以一种更明确的对数字公共资源进行结构化的方式激发创造力。OPUS“试图与全世界的媒体从业者、艺术家、写作者和公众一道,建立一个创造性的公共资源库”,他们如此阐释他们的目标。“人们在这里展示他们自己的作品,并且开放修改的权利,而且可以通过引入新的材料、实践和视角来干预和改造他人的作品。”OPUS,换言之,使得艺术作品本身成为了一种公共资源,“资源(编码)……在这里是录像、图像、声音或文字……可以被自由地使用、编辑或者再传播。”
这番话传达的精神令人印象深刻,既是扩张性的,同时又有乌托邦色彩,尤其是OPUS首次亮相的场合是第11届卡塞尔文献展——可谓国际性展览中最为重要的展览之一。也大约是从此时起,关于全球化的话语开始在艺术圈内成型,巴什、纳如拉和森古普塔开始被看作代表“当代印度艺术”的不二人选。这种现象中不乏一种荒诞的符号化——一个艺术家群体如何代表十多亿极为不同的个体?而且将Raqs简化为印度当代艺术代表人物也是对该群体自身历史和实践内在的集体性和公共性的误读。
重要的是:尽管所谓的“新类型”引发热议,“新媒体”也暂时入住了博物馆和画廊,OPUS仍然不是会出现在传统艺术界市场驱动领域内的那类作品。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从理论上来讲,它属于大量的在线用户;至少从收藏和展示的一般标准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根本不构成一件“作品”。OPUS激发的互动里产生的那些独特的、丰富的摩擦,一个为匿名大众创造的开放性资源,与卡塞尔文献展——一个有史以来都只针对知名艺术家和圈内人的活动——的并置,似乎是Raqs这个项目的重点。简言之,OPUS所处的位置恰恰在文化生产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之间”:一个是自由文化运动的虚拟平台,另一个是全球艺术精英阶层。跨越这些不同的世界——一方面强化自己的不同,另一方面又保留了融合的可能性——也许就是这种实验的意义所在。毕竟,在一个消费者主导的时代作为一个集体存在,就意味着在被各种公共领域瓜分得所剩无几的方寸间行动。
帕梅拉•李 (Pamela M. Lee)为耶鲁大学艺术史教授。
2020年由卞小慧重新校对。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