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现代主义在近几年的当代艺术和建筑中有复苏迹象的话,那么可以说,人们对包豪斯和它的支持者们的兴趣可谓有增无减。这家极具传奇色彩的设计学校,在老家德国魏玛迎来了九十岁的生日,今年,在欧洲和美国举行了很多不错的展览,庆祝这所学校成立九十周年,这些展览有:在五家魏玛学院机构里举办的《来自魏玛的包豪斯》(4月1日—-7月5日),在Providence的Rhode岛设计学校的《马歇尔•布劳耶:设计和建筑》展(4月17—7月19日);柏林Martin-Gropius-Bau举办的《包豪斯:一种观念上的模式》(7月22日-10月4日),法兰克福西恩美术馆举办的《拉斯娄•莫霍利•纳吉》(2009年10月8日—2010年2月7日)。近期,《包豪斯1919-1933:现代化的工作坊》于11月8日在纽约MoMA开幕,借此之际,《Artforum》邀请了建筑史学家迈克•海斯(K.Michael Hays)撰文,探讨包豪斯在对艺术和设计的每个领域产生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影响后,究竟应该给我们带来什么。
目前,关于现代主义的问题类似哲学上的关于自我的问题而慢慢终结:我现在是谁与我曾经是谁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怎样才知道对于不同的环境我是否采取了相同的演绎和评估?意识又意味着什么呢?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问道:“何时可以说,现在的我和意识中过去的某个我是一样的呢?”想到自我,我们并没有认为现在就是过去简单而不可避免的延续,过去转回来只不过是为了证明现时的身份。现时,是通过在难料的事件中多重联系的实现而促成的一种状态,对行动的方式上,产生了和过去不同的效力。想想自我本身,再想想现代主义,我们面临着一种必要性的矛盾,为了现在我们能看清楚问题的要害,我们必须将其作为不可挽回的过去而进行审视和理解。现代主义是我们的遗产,为了能继续沿着它的足迹向前,我们有必要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并展现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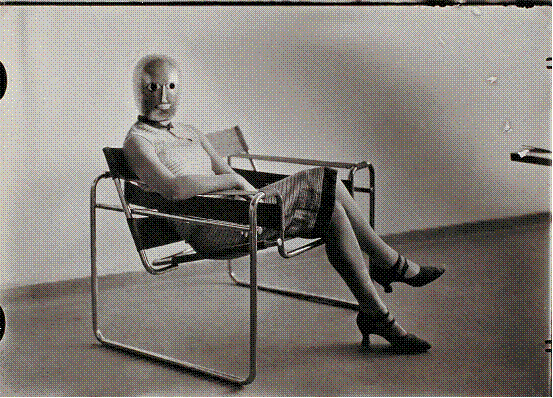
在现代建筑与设计领域里,关于包豪斯的问题将这种矛盾焦点化,其尖锐性就如在Dessau的著名工作室分支的悬臂玻璃角一样。包豪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持续时间非常长。当时的建筑评论家阿道夫•贝恩(Adolf Behne),认为包豪斯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国际性的市场化和先锋的明星实力;到1923年,它已经将当时的很多名人吸引过来,其中的教职员工有约瑟夫•亚伯斯(Josef Albers), 约翰•伊顿(Johannes Itten), 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保罗•克里(Paul Klee), 莫霍利•纳吉(Laszlo Moholy-Nagy), 奥斯卡•施莱默(Oskar Schlemmer)这样的人。建筑史学家如亨利•罗素•希区柯克(Henry Russell Hitchcock), Nikolaus Pevsner 这样的人,将学校和它的成员奉为圣徒。1938年在纽约MoMA举办的展览《包豪斯:1919-1928》,为战后美国对包豪斯风格化的吸收打下基础。后来,它的那些主要教育家在全美的学校做出了努力性的工作,包豪斯的理论和技术才得以传播开来。莫霍利在芝加哥领导了新包豪斯;米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包豪斯(1930-33)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校长,在芝加哥的Armour Institute创办了新的项目(现在的伊利诺伊技术学院),在那里,包豪斯摄影师沃特•皮特汉斯(Walter Peterhans)加入进来,他于1929年到1933年之间在包豪斯任教,之后去了纽约的工业设计学校,后来来到了伊利诺伊技术学院,教区域规划;在北卡罗那,亚伯斯和桑迪•沙文斯基(Xanti Schawinsky)将包豪斯的教学理论介绍进来。与此痛死,在德国,一位包豪斯的学生马克思•比尔(Max Bill),成立了Ulm设计学校,从1953年到1968年期间,这所学校一直延续并发展了包豪斯的教学传统。其他的很多学校也采用了包豪斯的一些教学理念,有很多到今年都没有进行什么大的改动。在欧美,可以说,没有哪个设计师脱离这一框框。包豪斯就是设计本事,它监督着我们的设计本身,并将一切还给设计。

它的“将所有的当代性归纳进来”的宣言,体现了先锋艺术实践的原本学院化与环境和日常用品的设计、制造、传播和市场化的完全融合—-这对我们今日的设计理想表征,算是个不错的概括。如今,我们如何又是否坚持了那所神圣机构所留下的一切呢?在包豪斯和我们自身之间,不同之处又是什么呢?首先是技术。格罗皮乌斯(Gropius)在技术上的教育理念是以早期的理论家如高芙雷•森帕(Gottfried Semper)为基础的,强调的是决定建筑和日常用品的材料和过程,此外还有赫尔曼•穆特修斯(Hermann Muthesius), 鼓励室内设计的标准化。同时,格罗皮乌斯也充分发挥了国际当代艺术家的绘画成就,在首批的八名教职员工中,有七位是画家。格罗皮乌斯努力将两种看起来似乎并不一致的教学方式融合在一起,Werkmeister式和Formmeister式。著名的包豪斯的预科,就是为了将两种方式的区别消解而设计的,1923年学校的口号是《艺术与技术:一种新的融合》。
绘画在格罗皮乌斯的包豪斯中,起着一种自我矛盾的作用,因为从理论上讲它在艺术领域的成就最高,而对技术的进步却又非常排斥。这些方面,格罗皮乌斯对莫霍利•纳吉(Moholy-Nagy)的作为非常深刻,1924年,莫霍利•纳吉在柏林的Der Sturm画廊展示了一些“用工业方法做成的漆画,”这些画通过教“一个盾徽店老板”做图的方法而完成。
莫霍利写道:“1922年,一个做图标的工厂给我打电话,要我画五幅上瓷漆的画。根据工厂的色彩表,我在图纸上涂涂画画。电话那头的工厂监督员将同种的纸,分成了方形。在正确的位置上,取下规定的形状。”这是一个被认为是彻底受到干预的制作过程以及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简单比方,格鲁皮乌斯希望在包豪斯的教学实践中能实现,这一轶闻也表明,当时的设计实际上和技术的距离有多大,包豪斯的理念对传统艺术的真正否定又是何种程度。即使是当代的评论家都将这个事例认为是“结构主义作为应用艺术被重新创造”,它的意义与汉斯•阿尔普(Hans Arp)和埃尔利西斯基(El Lissitzky)看似相同的文章有略微不同,这篇文章发表在《艺术的主义(The Isms of Art)》(1925)上:“随着绘画中方块的频繁出现,艺术学校为每个人提供了创作艺术的方法。如今,艺术的制作已经被简化,人们可以打电话向一个在家工作的画家订画,而画家可躺在床上接电话。”后来的文字暗示了对个体艺术家以及他具体化的思想和技艺,莫霍利的椅子告诉我们,艺术可以妥协,但同时也可完全在艺术家的掌控范围内,抗拒技术外在的凌乱后,创作者仍可处于主导地位。

在瑞士马克思主义建筑师汉斯•梅耶(Hannes Meyer)担任总监期间,传统的艺术创作被完全摒弃了。施莱默对梅耶的任职这样写道:“包豪斯将在建筑、工业生产、技术的知识性影响上重新开始,画家作为一种必要的邪恶力量,是可以被接受的。”在新的管理下,技术不仅是对材料和技术的探索,同时也是对人类主题的科学性的重新概念化。梅耶坚持认为:“建筑是生物学的活动。”对他而言,通过技术进行的设计以最大的全球性组织结构将最小的分子元素和互动整合到一起。建筑是“组织:社会,技术,经济和心理上的组织。”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因此进入了学校的课程中。项目的发展依据的是心理和社会效果,而不仅仅是它们的视觉影响。当时,梅耶任命了一些重要的年轻建筑师,印刷专家,摄影师,他们扩大并超越了传统的创作方式,将美术和商业设计、建筑和领土规划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一些客座教师发起了理论性的讨论,包括哲学家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 赫伯特•菲戈(Herbert Feigl), 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 以及剧作家厄内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 电影人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教学以集体性、合作性的“纵向小组”和“合作性单位”为方式进行。从而回避了艺术的个人主义。梅耶写道:“我可从没单独做设计。所以,我觉得选择合适的团队是为建筑进行创造性工作的最重要的一步。设计小组的能力越不相同,它的实践力和创造力就越强。”
格鲁皮乌斯认为,技术意味着对由新的可用性材料做成的标准化物体的个人化和艺术性控制。对于梅耶,技术则是“社会主义”的代码词汇。在两种看法里,技术对包豪斯来说,在概念上都起到了消失着的传递者的作用——-一种推动性的合成的思想从未得到真正的表现。在我们的时代,正好相反,技术似乎太易得了,处处可见,在我们的用品上,周遭环境里,无一不挑战着古老的行为,决定着新的动作,影响着我们的心情,组织着我们的日常活动。
今日的设计师无需为一种还未完全发展的现代技术找到精确的表达,他们可以将现有的技术的做为一种表现性结构,从而产生另外的效果—-一种超现实的动画般的表面,使我们领略到了各种各样的美丽与奇妙。也就是说,当下的技术是和我们的能力分不开的,这种能力不仅将我们的客体也将我们自身,我们在世界上的居住地,我们本身的主观性全部概念化了。
包豪斯主观性的最终表达,是形式上的抽象。艾尔弗雷德•安恩特(Alfred Arndt)经常重复一个1921年预科中关于抽象和主题经验的故事。约翰•伊顿(Johannes Itten)让他的学生去“画战争”。一位“胳膊受过伤”和“手被子弹击穿过”的战争老兵,描绘了亲眼见到的铁丝网,枪炮和战士。而另一个学生,由于年轻并未服役,则“用拳头握着笔反反复复,中间打断好几次,弄出来的是尖头儿和曲线,”之后很沮丧地放弃了。伊顿在对作业的评估中,并不赞同老兵的想法,认为他的作业不过是一副“浪漫的图景”,绘画的元素“在和一个战士做游戏”,但是,他表扬了年轻学生潦草而就的作业中所展现的原创力和本来的情感。他说:“在此,你可以清楚看到,这是由一个在无情的世界里真正经历过的人所创作的作品。满目都是尖刀和激烈的反抗。”
伊顿摆在同学们面前的课题是指示对象的问题:一幅画作(或一个电影,戏剧,油画,或建筑)应该勾勒出世界上的主要事物还是在超越经验的日常局限时,指向产生经验的领域。早期的包豪斯人认为这个领域就是指精神。不过,我们可以用更有当代性的、唯物主义术语图表来重新将这一课题概念化。

图表既不是空间,也不是具体事物。它是将不同的水平或表达方式,内容链接在一起的一种关联,促使的是新形式的产生。在包豪斯时代,现代化本身似乎或多或少进入了产品之中,尽管不那么明显,就好像在努力挣扎着找寻合适的位置一样。如果设计师能够认识这一点,抓住这一蛛丝马迹的结构,将其清晰化,尖锐化,激活它,也许设计就能够通过新形式的展现促进它进入未来。梅耶坚持表示:“在每个适合存在下来的创意性设计中,我们重新组织了一种存在的有系统的形式。”他将建筑的过程这样描述:“在社会活动的过程中,社会经济,技术建构,心理物理元素进行有意识的图案化或形态化。”这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宣言,将设计定位为为主客体的整体规划。设计作为变形能力的图景,可以被发展下去;设计也是现代思想本身的图表。
包豪斯图表是一种几何和色彩构成图—-主色和辅助色,二维或三维几何图,对角线,序列架,图层,这些都应该成为物体的构成基础,无论媒介或材料是工业的,商业的,还是审美的。我们很熟悉包豪斯设计家具的图表,支持立方格和填充式平面;康定斯基协调的色彩和图形,他认为相当于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Aleksandr Scriabin)交响乐般诗歌的跨媒介相似体;施莱默(Schlemmer)几何形的剧装和布景;赫伯特•贝耶(Herbert Bayer)几何体的具有决定性的“普遍性”类型,被认为是梅耶所推崇的世界语的图像化;格鲁皮乌斯的包豪斯建筑,高空摄影加强了不同的透明度的平面效果。所有的这些例子都被认为是具有潜在性的共同的形式结构。但是像莫霍利和梅耶这样的设计师,也强调同样的图表组成所有真正现代的物体,甚至包括那些没怎么设计的物体。梅耶1926年的文章《新世界》的一段中,开头列出了莫霍利和其他人已经开始发展的一些视觉标识制作的报道般广告式的方法名单,这些方法很快进入到了心理视觉序列,认为集合图表产生了那样的效果:
印刷、摄影、电影摄影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完美以一种日益精确的水准再现真实世界。这个展现在眼前的途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姿多彩;飞机库和发电厂是时代精神的大教堂。通过现代元素中具体的形状,色彩和光:无线通讯天线,水坝,格构;交通表好似,铁路信号的圆圈,方形广告版;通过传输线路的线形:电话线,高架有轨电车线,高压线;通过无线电塔,混凝土杆,闪光灯,加油站,这一图景就这样产生了一种影响力:
现代性产生了它自己的语言:名词形状,色彩形容词,速度和密度动词,时代精神将这一切描绘。梅耶将工业风景的图画像象形文字一样读解,认为它与时俱进,是一种及时出现的标识结构,努力从已过时的当代中分离开来。就像将空间和时间、阶级和性别沟通在一起的标识结构一样,范式包豪斯产品,通过抽象化,要求的是一种具有认识性、意识性、实际性,以及视觉和美学的身份。这些作品以现代思想的实证和我们对事物的物理性追寻而出现。它们的丰富性在它们将客观材料和技术价值变成主观性视觉和心理效果的能力上得到认可,这些能力还包括一件作品的质量变成其它作品的形式,因此,将两种水准的主观性劳动和创作的客观真实重新统一。抽象形式,证明了机体接纳的可能性,为集体社会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实际上的训练期。包豪斯设计的视觉产品的具体经验,也许可以作为一种功能性的图表而被接受。
在我们的时代,抽象已经失去了它的图表性功能和将现代精神的几何统一起来的作用。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回归后,在很多的形式表达中,抽象不仅仅是一种基础的类型,而且也是一种哲学类型,是不合时宜的视觉装饰。设计,且不提艺术吧,冒着枯竭的危险,进入了严格工具化的企业中,在具体而有限的语境中一些机会主义在操纵着一切,设计变得既无法突破又丧失了神秘性。而且我们对这种统一化的趋势越来越怀疑,一些不可能的事物如交通标志,绘画,建筑和身体之间产生了关联。我们的物体不仅跨越了团体和阶级之间的联系,而且作为一种对个体化和私有财产纯粹唯名论肯定而存在:因这是我,所以这就是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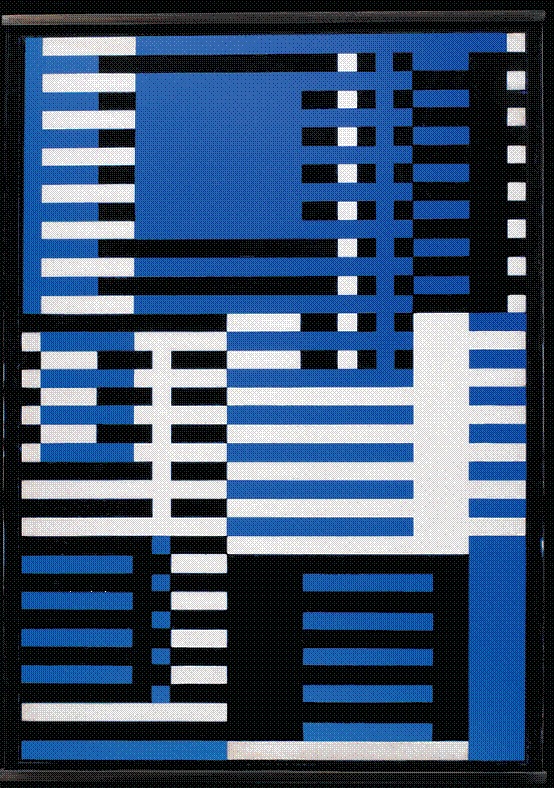
如果说如今的设计本体论是可能的话,那么,它将不是一种统一的技术活,也不是一种整体划一的形式结构。它应该能够产生艺术气氛,当然,艺术气氛是唯一很难定义的东西,它难以说清楚,不容易分别,然而却四处可见。新的图表,如今当然与数码设计技术和计算机程序不可分开,这些技术和程序将多重元素和不同的数据合成在一起,泛滥出来。很显然,当代设计创作,排斥任何戒律性的分割,大量的分界点,能将一切事物产生关联,这些都是包豪斯当时无法想象出的。新设计产生出的接受准则将被纳入相同的普通媒介中,就如录像游戏、社交网站和电视休闲节目一样。建筑和设计如今是毫无个性的媒介混合体的一部分,它的外在和功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文化上产生了转变和扩张,以综合的媒介经验从侧面散播开来。
当代艺术和设计的技术的自我(由它占据在世界上的确定性和持续性地位决定)变得不确定起来。如今,通过将客观和主观力量融合到新的表达和存在模式中,我们可以产生出完全崭新的自由。但同样,我们也会产生滞后。保罗•科里(Paul Klee)认为,一件艺术品的观众并不是先于艺术作品而存在,而是艺术品本身令它自己成为了艺术品,也就是说,艺术活动的力量就是将新的主体、新的自我、以及思考和理解的条件变成现实。将包豪斯作为一件过去的事件和一个具有活力的过程去思考,从中的体悟就是我们可以一直产生新的观念、不同的作品、新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包豪斯的本质是以一直变化的方式来实现自己。具体的改革可以从眼前的停滞中激发出集体意识,积极变化的欲望和希望。那就是曾经被宣称的为乌托邦设计。也许我们应该再次这样称呼它。
迈克•海斯(K.Michael Hays)为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建筑理论Eliot Noyes教授。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