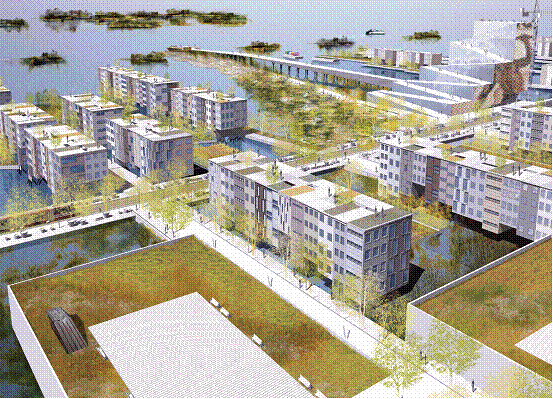
随着两极冰山的融化,温水的逐渐扩散,海滨城市(海岸线的腐蚀,甚至是越来越频繁的洪水爆发)如今正面临着如何抵挡海水侵袭这样的问题。早在2004年,纽约Stony Brook大学的调查者们,就建议修建三座水坝来保护纽约港。三个地点分别是布鲁克林和史坦顿(Staten)岛之间的纽约湾海峡,东河的上游,新泽西和史坦顿岛之间的海峡,这些防护坝将在纽约城遇到高水位时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样的先例(如荷兰的三角洲工程和伦敦泰晤士拦河大坝)在滨水城市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这样的工程在世界各地也发展起来,但是,卡特里娜飓风期间,新奥尔良防波堤的失败暴露了这种构造单一的工程潜在的危险。工程师盖•诺顿森(Guy Nordenson),景观设计师凯瑟琳•西维特(Catherine Seavitt),建筑师ARO事务所的亚当•亚林斯基(Adam Yarinsky),将这些大型的防护工程称之为“硬性”设施建设。与这样的举措不同的是,他们如今已经策划了一系列的应对方案,在纽约海岸进行“温和型”的防护设施建设,将海浪吸收进这座城市崭新的、可渗水的构造体系中。潮汐湿地的恢复,人工岛屿和礁岩的建造,防波堤和隔离码头的竖立,他们认为这些可以打造一个缓冲区,减少风浪的高度和力量,重新测量城市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居住和展览项目“涨潮”(Rising Currents)由策展人巴里•伯格达(Barry Bergdoll)组织,与诺顿森磋商,为纽约的MoMA和MoMA PS1所做,将诺顿森、 西维特、 亚林斯基调查的一系列设计提案草图展现出来。MoMA PS1重新变成一个做都市研究的临时性实验室,邀请了五个跨学科的团体,他们分别由建筑师、工程师、景观设计师、艺术家、生态学家组成,在纽约地区的设计办公室主任的带领下,在皇后区的空间居住了两个月。他们要求针对海岸线上升这一问题,构思出一套解决方案。最后所研究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在MoMA看到的这些。这些方案混淆了可行性和纯理论性之间通常的界限,既未遵循建筑的科学密码,也非出于科幻小说的本能欲望而进行大肆空想。而是游移在对科学事实近乎微观的兴趣和对建筑在形成社会图景的延伸性观点之间。项目的规模,基准模式的不断诉求,设计持续性的融入,这些都体现了对战后日本运动Metablolist所倡导的大型建筑构造的一种偏好,那场运动提倡的是超大规模的都市建构—-将城市功能比作细胞的产生过程,想象并建造(很少见)胶囊楼房和海滨城市,遵循着这样的信条:陆地是人类居住之地,海洋则是机器运作之地。就如Metablolist的方案那样,对纽约海港的一些间或疯狂的规划方案也采取了生物学的模式。参加这个项目的人们,并不是将生物过程作为汇集在都市中的建筑元素的一种比喻,而是直接将人体的有机运动过程作为设计的多样性的一种选择。
在对SCAPE的景观设计师凯特•奥夫(Kate Orff)的录像访谈中,她讲述了她的团队的“牡蛎-结构(Oyster-Tecture)”方案,诠释了一种“推动牡蛎本身的生物过程和生物性力量”的愿望。这个提议是希望能通过重新引介养蚝场来提高海水质量和减少风浪的冲击。虽然这个项目要求对本土的生态系统进行恢复,但对一个已经被破坏的自然机体的持续性掌控也依赖于相关的社会形态,崭新的技术和形式语汇。奥夫和她的团队从布鲁克林的城市农业运动中得到启示,想象出一个弧形的人造网构造,堆积在海岸边,水产从业者在那里进行局部养殖。同样,由建筑师马修•拜德(Matthew Baird)领导的团队,利用了自然体系和自然作用,将成堆的再循环的玻璃倒进新泽西的Bayonne水域,慢慢就形成了水晶线暗礁,从而缓冲了风浪的侵袭。废玻璃成为了水生物的栖居地,这种构想反直觉地将生态发展和城市消费联系在一起。他们将废弃的工业原地激活,对细胞的生物活动产生兴趣:在无用的油管道里养殖单细胞海藻,用于生物性原料的生产。ARO和dlandstudio团队将传统的基础设施既作为生态装置,又当做了景观特征:他们建议挖掘市区路基,形成一个可渗透的结构,“软硬有加”,让海水可进入城市的下区。多孔的筑路材料可以令排水进入一个巨大的地下海面,令有活力的植物生命遍布街道的表层。虽然设计避免明显的拜物化设施,但遍布的高速公路,通天大桥,复杂的管道,都是历史性大型设施提案的主要特点。纽约城市规划的基础,街道网,虽然几乎令人察觉不出,但还是与这个地区的自然体系融为了一体。
LTL和nArchitects的提议突出了城市与海,建筑与自然景观之间令人捉摸不定的关系,将城市变成了流动之洲。LTL,负责新泽西自由州立公园的再规划工程,在原地打造的是一个“水陆两用的景观”,恰好和这个项目中水平面的上升问题相契合。公共空间和水路随着海潮出现和消失,让位于于水上娱乐扩张的空间。nArchitects的提议是在布鲁克林和史坦顿岛之间开通水路运输,增加港口,将水域变成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城市地带。从屋顶延伸下来的住宅区一直扩展到水边,俯瞰着那些随海水起伏的绿色空间。自然的韵律带动下的公共空间,将城市中心从曼哈顿下区的摩天大楼到海湾的开放空间:用nArchitects的俏皮说法就是,那里是一条“活跃的地平线”。
以自然为基础的城市价值,尤其是城市水路的地位,至少从十六世纪开始就已经是政治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了,当时,在文艺复兴的为你的城市规划发展上,围绕着水力和建筑的争论起着很大的作用。经济萧条时期,威尼斯礁湖在生态上受到了影响,河道淤塞,私人土地持有者修建堤坝,另一方面,随着通往东方的大西洋航线的开通,水上贸易也开始衰退。当时,同时出现了修缮和保护礁湖的两种建议。第一种意见由水力学专家克里斯托弗洛•萨巴蒂诺(Cristoforo Sabbadino)提出,是一种“温和”的改良方法:疏浚运河可以容纳一部分海水,河流的改道可组织泥土淤塞。第二种方法是建筑泰斗艾维斯•科纳罗(Alvise Cornaro)提出的,既有象征性又很“强硬“:在威尼斯群岛周遭修建加固的防波堤,在Bacino di San Marco建造两座古典纪念碑,水流过圣马可广场的前方。前者是想将礁湖恢复到之前的那种自然状态,但并未防止城市主体的自动扩张。后者期待能大张旗鼓地重新规划这座城市,最重要的是,要将这座城的象征中心从圣马可陆地变成Bacino水域。
诺顿森起初提议,将卡特莱托(Canaletto)十八世纪的一幅景观画(画面上是Bacino水域的扩张)挂在展览的入口处。诺顿森对纽约海岸的展望,就如科纳罗提议中的Bacino一样,希望能将这里变成一个新扩张的大都会地区。而科纳罗重新规划威尼斯的中心的提议,是象征性地将区域扩大到Veneto的农田,“涨潮”计划里,重点强调的区域包括新泽西的局部,南布鲁克林和总督岛,曼哈顿下城的一小部分。但“涨潮”中的提议,没有一个对科纳罗的将修建防护堤坝和经典建筑作为强化城市形象手段的策略表示赞同。这说明静止的纪念性建筑不再是展现都市的最佳模式。这些计划都赞同通过分散的基础结构和流动的风景将城市中心进行置换。萨巴蒂诺和科纳罗在此似乎达到了一致,他们都认为生态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涨潮”提案中,设计乐观主义和“与自然共相处“的悖论贯穿其中。
但是同样的浪漫主义产生了一个关于自然的理想化概念,这一浪漫主义作为颠覆性的非理性赋予了大自然另一种遗产。1999年,建筑师莱波斯•伍兹(Lebbeus Woods)设想在哈德逊和东河(假定是通向大西洋的出口)筑坝,让纽约港的盆地急剧沉落。在一张画里,曼哈顿下区被高高的岩床支撑起来,成为了面向布鲁克林和海港的一座防渗的悬崖。这是将提议夸张化,为防止洪流而修建大坝。曼哈顿本身就变成了一面巨墙。这幅画是将“涨潮”项目中提出的策略反向。但二者都力图指向城市图景的规划中建筑服从于自然的观点。且不说伍兹图片中高耸的防护堤的细节部分(人工的工程构造)怎样,其本身却是一场天灾带来的后果—-从地理上讲,这是曼哈顿地震式的崛起。一座纪念性的“硬性”建筑项目在无法驯服的大自然的威慑中,变得微不足道了。虽然,“涨潮”希望能通过建筑上的乐观主义驱散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担忧,但伍兹画中黑暗的一面,一座建筑的某些东西被自然的灾难同化这些方面,都保留了下来。这些项目所预见的那些灾难-气候变化—当然都是人为造成的:上升的海岸线是技术干扰大自然所造成的恶果之一。“涨潮”提案证明,人造的环境已经和自然风景以及自然变化不可分割,而自然循环则是受到一系列人为元素的干涉。与自然共设计亦是设计对自然的征服。
“涨潮:纽约水坝项目”十月十一日前在MoMA展出。麦克•王(Michael Wang)现居纽约,研究艺术与建筑。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