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莫斯科,就连鸡尾酒会上也会发生意识形态之争。我最近参加的一个由奧伽•斯維伯瓦(Olga Sviblova)策划的晚会就是如此。她是莫斯科摄影双年展的策展人、新建的规模宏大的多媒体艺术博物馆馆长,我任教的那所艺术学校就隶属于这家博物馆。见到我时,她有点大惊小怪,凑到我跟前低声说:“我听说你们给学生灌输了一些危险的东西,有人说你教他们马克思主义!”
她所说的“你们”指的是我和我的同事David Riff。不错,我们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体系阅读的现代艺术史。而且我们的学校还是以罗德琴柯(Aleksandr Rodchenko)的名字命名的。为了让她感到没什么,我说,在西方的大学里马克思主义是主流理论,不用这么惊恐万分,但我越是这么说,她反而越是恐慌。她以为我在讽刺她,于是几乎开始惊叫起来,说她讨厌一切主流的、时髦的和有魅力的东西。
但斯維伯瓦错了,可怜的马克思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并不时尚,但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在俄罗斯,魅力这个词有着不可期待的命运。魅力袭来的时候,立刻被这里的人们竞相追逐,尽管现在几乎一切被认为有魅力的东西都带上了污点,这其中就有国外的展览,例如弗朗索瓦•皮诺特(François Pinault)在俄罗斯车库当代文化中心(Garag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e)举行的收藏展(2009)、高古轩画廊在红色十月巧克力工厂举办的展览(2008),以及今年初俄罗斯本土艺术家在车库当代文化中心举办的AES+F影像作品展。实际上,对于魅力的耿耿于怀说明了形式的僵化老套,也说明他们无法说出艺术家所要传递的信息及其作品的含义(我发现我的学生们不敢将他们的照片放大到8×12英尺的格式,因为他们怕别人说这些照片太炫了)。
这种明显的审美特征和政治的压抑是当前莫斯科艺术最显著的特征。今年夏天,Riff、Cosmin Costinas和我正在筹备在叶卡特琳堡举行的首届乌拉尔工业双年展。这个城市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强烈影响,我们新闻稿中的一个字被国家当代艺术中心的组织机构删去了。因此我们必须把那个敏感的“资本主义”换成更加委婉的“新秩序”,这下就没有人反对了,因为“新秩序”听上去有柯林斯或者多利安的意思(古希腊柱式——译者注)。
也许正是如此,“真正的艺术”和“形式”似乎成为了当代俄国津津乐道的话题。批评家们对“专业化”、“高质量”和“视觉统一性”等概念更是激情澎湃。一些艺术家断然否定他们的作品有任何政治含义,并且强调说他们的艺术语言体现的仅仅是个人的情感,或者换一种说法即“生与死的问题”。

在俄国的这种“新秩序”之下的当代艺术(希望)在新资本主义“常规”和去政治化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这样的艺术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一种光鲜亮丽的面貌,并且给新的精英阶层一种共同的身份。当代艺术本来是远离大众的,而现在却在国家的意志下强加给了大众,就像当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当然不像小说那样普及得彻底)。国家所举办的各种各样的双年展也逐渐开始被这里的中产阶级所接受。去年,国家当代艺术中心得到政府的赞助,在莫斯科市中心新建的17层豪华博物馆里举办了展览(他们自豪地宣布达明安•赫斯特和查普曼兄弟的作品有可能成为该博物馆的首批藏品)。石油换取的大把资金让俄罗斯的艺术更加国际化,但也失去了先前穷困潦倒时所具有的活力。最近有传言说车库当代文化中心要请国外策展人。另外,汉斯•尤利斯•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是第一个来新的Strelka媒体、建筑与设计协会举办讲座的名人。在今年秋天的康定斯基奖提名展上,人们可以看到罗伯特•斯托(Robert Storr)的身影,他是新的评委,在人群中虽然不太显眼,而且感觉还有点迷茫,不太确定自己站的位置对不对,不过他还是来了。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好几代艺术家都在争取自己的合法地位,而这种与权力机构、国际社会的和平融合正是这些艺术家一度梦寐以求的。现在,他们的梦想实现了,不过也未必如此。
在当前的新形式主义麾下的艺术家和策展人并没有体现出一派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气象。而俄罗斯政府对他们的态度则是被动的顺从。微笑默认其实挺悲哀的,“谁来改变规则?”才是真正的潜台词。Olga Chernysheva最近以著名的俄国绘画(帕维尔•菲多托夫创作于1851-52年的《再来一首!》)创作的35毫米电影《心跳停止》(Intermissions of the Heart, 2009)就反映了这种气氛:一个人躺在床上,在自己漆黑的房间里,开着电视,逗弄他的狗。这只狗不停地在棍子上跳来跳去。他就像一个典型的莫斯科艺术家,昏昏欲睡,有点自恋,暗中为自己的生活庆幸自满。作为一个不停地寻找艺术家的策展人,我意识到,当今俄罗斯艺术中完全没有体制批判的东西:这个国家的艺术世界并没有自我反思的诉求(或者说也许是缺乏这种诉求的能力)。

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的非官方艺术圈致力于捍卫当代艺术,将其正名为一种具有创造性和自律性的实践,有别于传统的苏联小资趣味。这种英雄气概扭转了艺术与体制性活动,并且为艺术界注入了一种团结一致的气息。早期现代主义以来形成的对抗性前卫精神使俄国最初的当代艺术焕发出勃勃生机。
然而,正如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随着当代艺术成为了一种中产阶级趣味的标志,这种前卫精神也面临着消解。不过,就算如此,俄国艺术也并未放弃这种幻影式的理想而去热衷于其他的道德准则。一方面,莫斯科的艺术空间(例如Winzavod艺术中心和车库当代文化中心)正在逐渐成为带有强烈的设计与消费“创造性”的大众化消遣场所(泰特现代美术馆的简化版),但是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秩序却挪用了这种非官方的精英主义,将那种社会先锋的幻觉呈现给艺术观众。
举例来说,我认为艺术带来的这种优越性正是莫斯科策展人Andrei Erofeev的动力,他策划的《违禁艺术》展(2008)因惹怒了东正教徒而被处以大约5千美元的罚款,由此引起了轩然大波。而Erofeev强调,他的这个展览旨在让人们意识到政治、道德和宗教审查的存在,但是这个展览却没有大范围地公开(没有上网),因此大多数人都没听说过这个展览。看到这个展览的只有艺术界的观众、外国记者,最重要的是Erofeev蓄意挑衅的教会势力。更惹人注意的是,Erofeev选择了Andrey Sakharov博物馆与公共中心作为展览地点。这个机构担负着明确的民主教育使命(博物馆的前任馆长也因此受到牵连,甚至被处以更高金额的罚款),因此,这个展览让已经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机构更加岌岌可危了。
在Erofeev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他并没有得到同事的支持,更不用说那些艺术家了,他们甚至还在一座教堂内举行了新宗教艺术展以缓和气氛。但是Erofeev的支持者却发出了和他本人同样的声音:“试验”与“挑衅”是艺术家独特的权力。但不出所料,几乎没有人提出这种批判(包括对教会的批判)是每个公民的权力,而不仅仅局限于艺术家。
Erofeev坚信,当代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有着特殊的权力。与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Marat Guelman也是一个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在俄国艺术界,他比任何人都更能触及到权力意志。这位画廊家出身的博物馆馆长始终的信条是“虽然你还不知道,但是你需要当代艺术”,在梅德韦杰夫总统执政下,这种倾向尤为显著(俄国政府赞同的是“少数幸福之人的现代化”。
2008年,Guelman在先前宁静的城市彼尔姆建立了当代艺术博物馆。就像很多俄国艺术场所一样,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公共机构,也没有那些敬业的管理员,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空间,充满了其创建人的勃勃雄心。今年夏天,我自己也在那个空间策划了一个展览(一个乌克兰当代艺术展览,我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任何赞助),我相信,如果Guelman继续担任馆长,这家博物馆定会有不错的发展。但是他目前正在将毕尔巴鄂的转型推广到其他的俄国城市。他最新的计划打算在Skolkovo举办。这是一个莫斯科外面的精英荟萃的研究中心,也被称为俄罗斯的硅谷。这个中心不仅有特殊的政府拨款和自由签证的权限,而且还有自己的法律系统。据说Guelman中了这个非官方的“政府”“标”,将负责Skolkovo的所有文化政治,不论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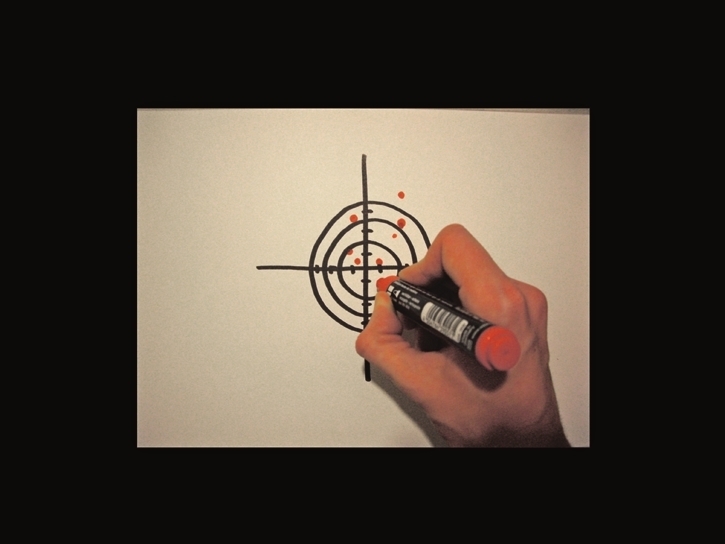
Erofeev和Guelman这两个俄国艺术界的重要人物都喜欢滑稽的青春期和例如蓝鼻子群体(Blue Noses Group)那样的性感(而非真正的政治性)诙谐,与同类组织相比,他们更充分地体现了当代俄国艺术家的悲哀:他们是普京政权的小丑,得到纵容,但也处于控制之下,虽然痛苦万分,但却衣食无忧。不过,青年艺术家却不相信表达政治批判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赤裸裸的身体部位。俄国当代艺术正在经历着一个剧烈的变动时期,就算这种剧变还称不上是宗派分裂。老一代艺术家(Guelman、Erofeev和刚才提到的蓝鼻子群体就属于此列)还在为那个远离无知的劳动阶层的共因冥思苦想的时候(就像蓝鼻子群体那样,劳动阶层的弱点被他们放大),而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则拒绝与这些老艺术家们分享这种“功成名就”的地位,他们开始将自己视为“艺术工人”,并且积极主动地寻求艺术世界之外的观众。
部分原因是由于现实情况造成的,当前的这些人是俄罗斯第一批为生计而奔波的艺术家和策展人(往往不是莫斯科本地人),他们年纪轻轻,不可能在九十年代就拥有了私人住宅,因此处在房租和首都的高物价的压力之下。另外,那种自由组织也是一种新的现象。在过去的两年里,莫斯科最有意思的展览是艺术家自己策划的,并没有策展人的参与。其中的一个就是2009年在Regina画廊举行的展览“被征服的城市”。这个展览是一些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艺术家策划的,其中包括Ilya Budraitskis、Aleksandra Galkina、Nikolai Ridny和David Ter-Oganyan。该展览是一幅社会与政治的写照,敏锐地把握住了当代城市空间及其规则与焦虑的气氛。他们这群艺术家已经具有了政治觉悟意识和抗议的动力与热情,例如Galkina的作品《难画》(Drawing Is Hard,2009,在其他地方展出)。在这件影像中,她用一只令人躁动不安的毯头笔疯狂地向那些国立大楼、汽车、靶子、圣诞树等东西的图画“射击”。青年一代的艺术家并没有以空洞的、具有新审美特征的形式主义自居,而是采用了“流行”的写实形象、叙事艺术、绘画,甚至是苏联风格的说教式的博物馆装置,例如刚刚由艺术家转为策展人的Arseny Zhilyaev就是如此。他去年在Proekt_Fabrika策划的两个展览(“机器和娜塔莎”与“劳工运动”)即涉及到当代的劳工阶层的状况。不过有意思的是,他的联合策展人Sergei Khachaturov(艺术史家、新自由主义报纸的评论家)则认为他们的展览更具有形式主义的意味,而非秉承了俄罗斯前卫精神的政治性。

因此,我们无法忽略“怎么办?”这个俄罗斯唯一具有明确政治倾向的艺术团体。“怎么办?”就像Ilya Kabakov那样扬名于俄罗斯境外,填补了俄罗斯艺术界(就算不是整个俄罗斯社会)的巨大空缺。即便在俄罗斯国内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个组织声张的具有社会激进性的艺术项目不仅大都在西方举办,而且恰恰就是为了西方,例如,他们最新的作品《塔:歌唱剧》(The Tower: A Songspiel,2010)尽管表现的是本土的事情——关于在圣彼得堡兴建摩天大楼的提议,以及随后对这个议案的抗议。当“怎么办?”提到批判性艺术的时候它强调的是批判性,而那些年轻的俄罗斯艺术家首先听到的则是艺术。因为他们已经不再着迷于这个组织的那种并不怎么激进的艺术政治了(这个组织更热衷于卷入非营利性艺术机构的全球化网络),而且往往将他们视为机会主义者,他们无法对自己的艺术实践提出充分的质疑。在俄罗斯人看来,他们在上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上展出的文字壁画表现得无非是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很难唤起人们的激情。如果艺术家们继续这样做东西,那用不了多久,反共的、故意遗忘的和对于苏联历史的歪曲将依旧成为国家政治,那些陈词滥调也将成为发泄的材料。
俄罗斯艺术家正在面临两种矛盾的职业生涯:走国内路线的必须保证作品在形式上令人满意,可以略带忧郁,但政治上不能太过分。或者他们也可以走另一条道路:最好贴近左派,表现政治题材,以一种说教的方式引用俄国前卫艺术的东西,而且还要长于社交。那除此之外再无路可走了吗?也许还有吧,但要另辟蹊径就需要比“怎么办?”还要远离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和那种经过体制批准的批判性艺术的避难所)。在俄罗斯,还有另一些艺术家,他们试图逃离当前的社会与艺术的沮丧气氛(你也可以称这种姿态为安然自得)。

但这就需要不按艺术的规矩出牌了,比如观念艺术的老将、理论家、集体行动小组的带头人Andrei Monastyrski,他现在说,他一直以来所做的(只有少数观众,或者根本没有观众的行为表演)不是艺术,而是“存在的实践”。最近,他将自己的行为上传到了YouTube上,他用了Semyon Podjachev(已故苏联作家,文笔晦涩)作为作品名称,在上传的视频中不仅有他自己的表演,还包括一些彼此不相关的古怪视频。可是这样的作品偏偏得到了本地的一个商人Gherman Titov的青睐(他与苏联的第二位宇航员同名)。他不仅赞助出版了所有与莫斯科观念艺术有关的文本记录,而且自己也变成了艺术家。
最近有消息称,明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的俄罗斯馆将举办Monastyrski与集体行动小组的展览(由Boris Groys策划)。至于Monastyrski能吸收多少当代艺术的成分,以及他的怪诞艺术在多大程度上能被世界所承受,让我们拭目以待。

叶卡捷琳娜•德戈(Ekaterina Degot),莫斯科艺术史家。
译/ 梁舒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