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特·史德耶尔对话劳拉·珀特阿斯
“技术已然让我们感到出其不意,而其所开拓的空间则空荡得刺眼。”齐格弗里德·科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曾这样写道。这位伟大的德国电影理论家并不只是在感叹机械化世界中生活的匮乏或是疏离,他同时也表达出一种欣喜,以及对于技术带来的可能性的期待,尤其是对电影这一可供玩味、发现不凡体验与视野的空间。劳拉·珀特阿斯(Laura Poitras)和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的电影与视频有着类似的令人兴奋之感;她们对所使用的全新技术、设备、以及巨大的信息场进行着探索。但她们所揭露的秘密和调查的事件又往往骇人听闻——无论是爱德华·斯诺登所揭露的美国政府对其公民进行的大规模秘密监控,还是以一种半开玩笑但又极其严肃的方式教我们如何躲避无人轰炸机。《艺术论坛》特邀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珀特阿斯,和正在纽约艺术家空间举办个展的史德耶尔,请她们就电影制作、认知观念、信息披露、数据加密、以及图像的希望和危险等话题交换各自的看法。

LP:上次我们俩碰到是两年前了——正好在我收到爱德华·斯诺登的邮件之前。当时你正在为威尼斯双年展创作有关监控和无人轰炸机的项目。
HS:我们当时还一起头脑风暴了一下。所以几周之后,斯诺登就联络你了?
LP:是的。现在回想起来,你的项目为斯诺登事件埋下了许多伏笔。
HS:我做了个视频,叫做《如何遁形:一个太他妈说教的教学片.MOV 文件》(A Fucking Didactic Educational .MOV File, 2013),所讨论的就是如何在被监控的时代里保持不可见的状态。它首映之后四天,斯诺登的新闻就出来了,非常惊人。我到处能看到斯诺登。而且我知道你在其中有牵涉和参与。
LP:许多人觉得有关消失的想法是纯粹的妄想。但是如果你的住处就是无人机的潜在目标,那么在视野中遁形或者躲避监控就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情况,而会成为真实迫切的问题。
HS:确实如此。事实上,你当时对遁形的想法是设计一款手机App,可以在无人机靠近时发出警告。
不过问题在于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弄出这么个东西。但确实你在这方面已经有很丰富的策略和技术了。这令我肃然起敬,因为你知道许多关于数据加密的知识,以及使用永远不联网的空气间隔计算机,诸如此类。
LP:在斯诺登出现之前,我已经不得不设法解决信息安全的问题了。那时候我长期跟拍雅各布·亚佩巴姆(Jacob Appelbaum),他正在中东各地训练激进分子、传授通信安全的技术。那些都是很敏感的原始素材——涉及的内容包括埃及抵抗运动,还有突尼斯的局势等等——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因为其中有许多人不想在镜头前暴露身份。
不过我之所以喜欢你的《如何遁形》,包括你整体上的创作的原因是,你将纪实和虚构元素混合的策略,还配上极其俏皮的叙事——被监控的威胁,还有这种近乎玩闹的规避它的方式。所以我很好奇:当你开始构思一件作品时,它是怎样推进的?你会不会意识到:“这个想法从这里开始”?
HS:在《如何遁形》中,起初是我得知了一个有关叛乱者如何躲开无人机而不被监测到的真事。无人机所能看到的是运动动作和人体热量。所以这些人就会披一张反光材质的塑料布,并且往自己身上浇水来降低体温。当然,矛盾的是,整片区域都充斥着明亮的单色塑料布,人眼清晰可见,但操控无人机的计算机却看不见。而且人们会在这些塑料布下面看书,直到无人机飞走。他们是特地带着书来的。对他们来说这是个绝好的可以学习并且放松的机会:无人机的阴影变成了某种大学。
那你呢?关于上一部电影,我记得当时我们聊过,它会是一部概述检举揭发人/告密者的片子,而且你已经有很多素材了。然后突然间事件发生,整个项目也完全改变。
LP:斯诺登会突然之间联络我正是我热爱自己工作的一个原因,它让我能与周围的世界发生对话,而且我真的从来都想不到会有爱德华·斯诺登的存在。我局限的想象力,比起我去现场拍摄时遇到的事件,要无聊得多。所以是的,这个事件很明显地改变了(原计划的)叙事。不过真实电影 (vérité filmmaking) 的制作,以及对当下进行时态所进行的纪录,就是会跟随事物的展开、受故事的线索牵引。这有时相当不确定,也很可怕,但是那样才会有戏剧性。当碰到斯诺登这样显然有着极强吸引力的事件时,要转移重心其实并不困难。
HS:然后你碰到了斯诺登,而且在香港的酒店房间里进行了拍摄。这之后你又是怎样工作的?
LP:在香港,我只是尽我所能地做记录,并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通过在那里的拍摄,我处于一种震惊的状态——震惊于这些机密文件,震惊见到了斯诺登,而且发现他竟然如此年轻以及他所面临的危险,震惊于我们很清楚自己的所为会惹怒这个世界上最有权有势的人,以及之后毫无疑问会引起的激烈反应。
格伦(格伦·格林华德,Glenn Greenwald)和我都曾目睹过在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以及媒体如何打造出将她病态化的叙述。我们担心类似的事情也会再次发生。但是斯诺登的显著区别在于,他决定好了要挺身而出。他已经做好决定不隐瞒自己的身份。当他第一次这样告诉我的时候,我吓坏了——我觉得这等同自杀。那之前,我一直以为他希望作为一个匿名的消息来源。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这样做非常聪明,也非常冒险——他清楚自己没法保持匿名,所以他决定率先公开自己的身份。当我提出想与他会面并做拍摄时,他表示反对,因为他不想让整件事情变成他的故事,也是因为如果有人试图阻挠相关报道,那我们都在一起的话就太危险了。但是我说服了他,理由是对人们来说要理解他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
离开香港回到柏林之后,我知道自己有义务对这些文件予以报道。斯诺登在给我的第一封邮件里是这么说的:无论我发生了什么情况,你要保证将这些资料返还给公众。因此我必须这么做。不过我并不是一个作家——我是说,尽管我一直为平面媒体供稿,但是我清楚自己真正做出贡献将会是以电视记者和电影制作人的身份。
HS:但我不认为完全是这样的,因为你增添了许多非常重要的贡献——超出了已经非常精湛的《第四公民》(CITIZENFOUR, 2014)本身。我认为你真正的成就之一是找到了如何处理这类信息的方法,你的报道方式,以及信息如何被存储、保护、传播、编辑、检查……等等。保留和传播信息,以及审时度势,这整个过程是一种艺术。而且我认为,相较于之前泄密事件的处理方法,比如维基解密来说,你的处理方式很新颖并且思考得极其周到。你是怎么想到这些的?你是怎么制定规则的?

LP:正如你所说的,当时有许多决定摆在我和格伦手里。我们是有所借鉴的。格伦和我都密切地关注过维基解密。格伦还写过相关文章。我也大量拍摄过朱利安(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而且我们看到他们一些相当卓越的成就,尤其是善用媒体合作伙伴来进行多个国际网点的信息发布。在过去,因为美国政府对本土新闻机构的施压,有些事会被抑制。但是如果好几家不同的国际新闻机构都有相同的信息,那抑制就会变得困难得多。
我们也一样跑了许多家新闻机构,但我对于资料非常小心谨慎。我不信任任何人。我不希望《卫报》那样的事故重蹈覆辙——他们发布了一个密码,使得未经编辑的国务院电报内容泄露。这实际上是身为记者的失误,而不是维基解密,是记者没能保护好密码。
因为国家安全局[NSA]的资料非常敏感,我觉得新闻机构对每件事的处理都必须基于具体事件的基础,只有与事件相关联的一系列文件才能被共享。而这样做有利有弊。缺点就是报道本身会更慢,有不少批评针对这一点,而我也确实同意这样的批评。我也希望自己可以以更快的速度进行报道。但是当斯诺登来联络的时候,我的身后可没有一整个编辑部。我必须亦步亦趋建立关系,尽管我保持着绝对的独立性——我与许多新闻机构有自由攥稿的协议,但都是以一个一个的故事来展开工作的,而且不保证独家,这样能让我有灵活的安排。当我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有关“棱镜”的故事之后[PRISM(棱镜)是NSA搜集网络交流数据机密项目的代码],我开始与德国的《明镜周刊》(Der Spiegel)以及《纽约时报》合作,而格伦在和《卫报》合作。但是格伦和我认为,斯诺登是将我们当作记者——独立记者——对待托付信任的。他并没有将自己托付给《明镜》,或是《卫报》,或是《纽约时报》。因此我们也不打算把所有的文档移交给媒体,因为我们曾经目睹过事件恶化,尤其是《卫报》公布密码的事情。
HS:这就意味着由你来做决定,OK,这一部分文档资料我打算和一个具体的新闻机构进行合作,然后我们一起操作那个具体的选题。那样就变成了某种美学决定。
LP:不,那只是发表的策略。它与美学无关。
HS:我不同意。它确实是一个关乎形式的决定,与如何组织信息有关,与信息的形式有关。在安全层面上而言当然很重要,但也事关保护你的自主权,作品的自主权。它也同样与审美的自主性相关。回到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有一系列谈话是关于美国无人侦察机在土耳其本土协助土耳其的战斗机,有意思的是两年后你和《明镜》一起发表了与那些袭击相应的NSA的文件,文件所显示的正是传达给土耳其空军的信号站,要求派出飞机来执行空袭。就好像你和斯诺登突然间提供了一些我原本以为会永远被隐藏起来的东西:一种视角,俯瞰的视角。
LP:是的,但你才是那个围绕着信息创作艺术作品的人,这非常不一样。
HS:好吧,你所运用的技术中很明确的一点就是你观察纪实性的视角,这在你去香港拍摄之前就已经广泛使用了——比如在也门,等等。我总是对主角与他小儿子在黎明祈祷的场景叹为观止。你是怎么进到那个房间去的?
此外还有你的编辑技术,是在信息加密技术上的扩展——选择的技术——以及让资料安全和传播信息的方法。不仅仅是让它们被公开、泄露或揭示,而是真正地为它们找到新的形式和回路。我觉得这是一种还没被如此进行定义过的艺术,但它确实关乎美学。它是一种形式。
这不仅在你的情况中是一个富有创意的挑战,而且总体上也是如此。比方你有一个数据库。这就可以追溯到维基解密的情况,数据库只是一座信息的宝藏库,必须创造出一种叙事来浏览、操纵数据。什么样的叙事方式能够适应科技的新属性,以及数据作为档案的宏大性?
新媒体理论学者列夫·曼诺维奇(Lev Manovich)写过数据库。他回顾了季嘉·维尔托(Dziga Vertov)的电影《持摄影机的人》(Man with a Movie Camera, 1929),并聚焦在他的剪辑工作——即如何在拍摄素材的数据库中遴选,而不是拍摄工作上。但是——我经常在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想到你——在二十一世纪,编辑该如何工作?尤其是假如剪辑的人也是拿着相机、声音设备和加密硬盘的人,就像你那样。她是一个设计出整套交流基础体系的作家。而且她是个女人,不是男的!维尔托的团队有好几个胶片卷轴。那些就是他们的档案。所以,现在不仅仅是叙述的问题,还有取舍运用,转译,要冒着严重的个人风险,还要躲避一大堆军事间谍。这是在新型的、不断拓展的电影制作领域中对透明性和不透明性的处理,而这必然要求能力、技巧上的拓展。
LP:讽刺的是,被放到美国政府的检视名单上并且每次出入境都要受到询问,但却带来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那就是我在规避国家政府盘查上变得更为聪明,而且也令我更坚韧。我已经打定主意不会被吓倒。所以,从某种程度而言,当斯诺登的第一封邮件发送到我邮箱的时候,我对边境人员所提供的基本训练由衷感激。
有关于更宽泛的档案的问题,以及如何寻找意义,则是我为即将在惠特尼美术馆所举行的个展而思考的问题之一。档案中有数量巨大的“新闻”以及政府滥用职权的证据,但它也开了一扇通往平行世界的窗口,那个平行世界在秘密之中运转,并挥纵着可观的全球权力。这里面有一整套文化、语言和世界观,绝非仅仅关乎事实。这是我目前的项目之一。
HS:NSA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如何管理自己的信息?
LP:对他们来,说从海量的数据中提炼出叙述是一种挑战——他们每天接纳的信息节点数以亿计——但他们对此并不擅长。他们会使用图标和一些视觉化的工具。例如,他们有一个程序叫作“藏宝图”(TREASUREMAP),为分析员提供可以反映出网络以及每一台与之相连的设备的几乎实时的地图。我为惠特尼所创作的作品之一也会取名为《藏宝图》,它是一种颠覆性的反测绘。我认为NSA对数据收集方法的真正核心是回溯查询——如何依照事实看到叙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想要“收集一切”,这自然也就违反了各种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与合理依据。这些违反包括了从监控名单到各种更为糟糕的滥用权力,例如运用元数据来锁定无人机的刺杀目标。
你在自己作品中的剪辑和归档方式是什么样的?
HS:我始终参与剪辑过程。我认为剪辑——不仅对于电影而言,也包括在诸多其他活动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后期制作不是回顾性地处理内容,而是在制造内容本身。剪切编辑就是在产生意义。
戈达尔说过,剪辑可以是“和”或者“或”。那是传统的电影或者视频的剪辑工作方式。而现在的剪辑要面对更新的媒体和物理现实,而这些正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媒介,成为一种更为扩展的活动,相应的就必须有能力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处理信息、创造意义。
现在被扩展的不是电影,而是拓展性剪辑、拓展性后期制作、以及在不同平台和形式之间的流通。我认为这是分析当代活动的至关重要的途径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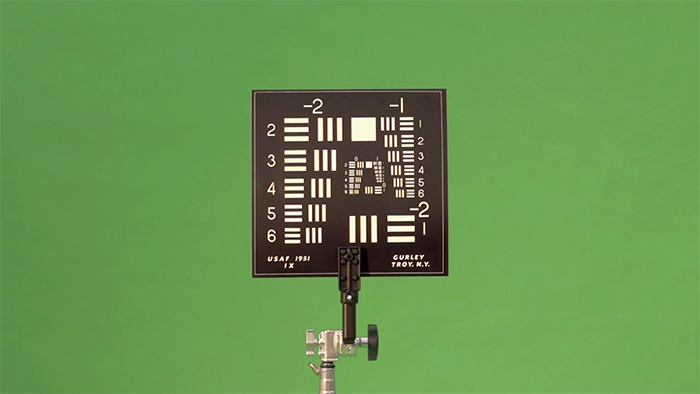
LP:你独立完成剪辑,还是与剪辑师合作?
HS:我自己做剪辑,不过之后还有色彩校正、合成、3D建模和渲染。我的团队来做后面的大部分工作。但我也会看效果:当我用After Effects做后期时,几乎没有任何实时回放。有太多的信息要处理,在你看到最终成果前大概需要两小时或是更久。所以剪辑就被渲染所取代了。渲染、渲染、双眼盯着渲染的操作条。那感觉就好像是我自己一直在被渲染。
如果剪辑时没法真的看到最终成效,你会怎么做?你只好揣测。就是一种揣测式的编辑。你会试图猜想它看起来大概什么样,如果把关键帧放在这里或那里。然后会有很多算法,来替你完成这些猜测。
LP:我在做这个有关NSA故事报道的时候,感到最为困惑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理我自己所同时兼顾的各项职能角色。你是怎样定位自己身份的?
HS:我从来没有受过要成为艺术家的训练,我也并不渴望被打上这样的标签。对我来说那样很奇怪。但是艺术界已经成为了一种感官产业——它传达出我们周围的各种紧张关系,从房地产业相关的一切到军事化、赞助行为、地缘政治,到普遍工作条件以及不平等现象,从实习生到高资产净值人士等等。
LP:我才读了你有关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重新设计规划的文章,里面对上述问题展开了精妙的讨论。你自己是如何在博物馆和市场这些体制中游弋的?你的作品也是按照版数出售的吗?
HS:是的,我会做几个版本。不过合同中会注明作品可以以线上线下任何形式来进行流通。它并不受到版本的局限。
LP:你有没有想过制作一部故事长片?
HS:没有,我知道在展示我作品的地方并不存在那种注意力。要做九十分钟长片的展映非常困难。人们只会放弃它。在电影院里就不同了。
LP:电影最大的好处是你会有一群“被俘”的观众——在那九十分钟里你可以拥有他们。还会有爆米花,你喂他们吃,给他们舒服的座椅。你不用去担心他们来回进出。
我觉得在艺术界里,(作品)时间过长常常被认为是种越矩,因为那会强迫观众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域,接受忍耐力的测试。然而在主流电影里,持久是绝对可以接受的。所以时长在这两个领域中接受度完全不同。当然了,沃霍尔是以优美的方式将之推向极限的一个极高明的例子。

HS:作为艺术,《第四公民》毫不费力地做了一些许多艺术家努力想要达成的事情——它渗入了大众媒体的流通。事实上,它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也最有效的政治艺术作品,完全没有遵循任何所谓政治艺术的狭窄教条。而且尽管你是独立的,但电影发行却走商业渠道——这有助于将电影传达到最初的斯诺登视频所传达到的那么数目巨大的观众群。
LP:我以商业的方式发行电影是因为我的作品确实属于叙事电影的范畴。而我的叙事方式是通过对个体面对冲突的叙述来理解更大的主题,这种类型恰好与更为流行的电影是契合的。所以虽然我没有屈从地改变我的实践方式来迎合大众,或者做出妥协,但它的确有被大众接受的潜力。我喜欢这一点。电影之所以这么美好是因为它是一个平民化的媒介。《第四公民》其实符合好莱坞电影长久以来的传统类型,那就是个体与国家的对抗。
HS:但同时我认为它在很多方面是前所未有的,因为这部电影感觉上就像是在记录自己的制作过程。报道事件本身是它所报道的内容。这电影与其说是一部作品,其实更像是对作品进行的记录。但这部电影似乎也可以算是一种虚构:你们所有人聚在一起,创造了这个事件、这个故事,以及许多用来讲述故事的工具;与此同时你们被巨变挟裹其中。这件作品最终是一个开阔而复杂过程,里面包含着尚未完全展开的政治、司法、信息、美学和基础建设等各个层面。
LP:我承认是有一些史无前例的方面——披露和报道的尺度、斯诺登对自己的曝光、反体制的记者获得了独家新闻、以及电影制作者成为了参与者。
驾驭这一切是很复杂的。比如,在我们即将要报道安格拉·默克尔之前我就知道,这会是条大新闻。而且,当然了,我会准备好带着摄像机去记录那一天。所以在两类事情之间就会产生一种奇怪的融合,一类是那些我可以预见会有影响力的、我会去记录的,另一类就是我无法预见的。
在你自己的作品中,你是否觉得可能制造出状况,或者是成为一种催化剂,逐渐对主题产生影响?
HS:不,我不这么觉得。
LP:但是你的叙述方式是在把玩时间与因果效用的。
HS:嗯,对我来说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处理现实生活的那种类型:怎样通过形式来处理它。传统的新闻报道有一整套标准的表达方式。其中一些很有必要,比如核查事实。不过我深信,现实生活比人们所能想象出的虚构故事要离奇得多,现在更是如此。因此报道的形式就不得不也变得更疯狂、更离奇。否则就会不够“纪实”,就会辜负所发生的事件。
LP:你认为什么样的形式能够与这种新的题材相匹配?
HS:对我来说,整个问题的核心是,我们暂且称之为图像生活与所谓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前者也曾被我们称之为再现。以前被称之为现实生活的这个东西已经被深刻地图像化。现在事关如何找到不同的流通形式,甚至是物理性地改变基础设施,因为现有的流通渠道都受政府和财团控制。
LP:我今天去了艺术家空间(Artists Space),你在那里布展的时候我看了一会儿,这种再现和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我看到“地下气象员”(Weather Underground)的时候很吃惊,因为它被演绎的方式非常搞笑、超现实。你知道那部有关这个组织的电影《地下》(Underground, 1976)吗?当地下气象站组织在四处躲避的时候,埃米尔·德·安东尼奥(Emile de Antonio)、玛丽·兰普生(Mary Lampson)和哈斯克尔·韦克斯勒(Haskell Wexler)拍摄了这部电影,真的是一部非常大胆的片子。
HS:我大概二十年前看过而且非常喜欢。当然了,在今天,“地下气象员”成了一个商业天气预报公司的网站。他们一度明确地表示名字的由来就是这个激进组织。
在我的视频中,设定为来自地下气象站的播报者——由一个小女孩儿和两位成人表演者扮演——站到舞台上播报天气,但所播报的天气奇怪地混杂着人造天气、政治天气、感情天气、各种灾难,渐入癫狂:气候变化、金融、地缘政治。到处都有风暴酝酿,不同的点点滴滴混杂成一次持续海啸。
LP:这是个特别棒的比喻。在我走进去看的时候就击中了我——我整个人置身于那种蓝色之中。而且我有着非常情绪化的反应,我感到自己好像被冲刷成某种东西。
HS:我其实是在试图营造一种感官体验,就好像整个空间都在水下。窗户上有蓝胶,让倾泻进来的光也都变成蓝色的。
LP:确实非常漂亮。还有那个弯曲的坐席——那是海浪吧?
HS:是的,影片中还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葛饰北斋的波浪——我记得是叫《神奈川巨浪》(The Great Wave off Kanagawa)。那是十九世纪典型的日本木刻。富士山在背景里,船只在浪潮中摇摇欲坠晃来晃去。这个场景反复出现在电影里。
这件作品以雅各布·伍德(Jacob Wood)为灵感,他是一个金融咨询师,后来转行成MMA(混合武术)评论人。他将不同类型的流动性联系起来:以风险为基础的金融流动资产随时可以摇身成为一场完美风暴,还有李小龙所描述的优雅的流动性:“要无形无状,就像水……水可以流动、或是渗透、或是滴注、或是冲刷。如水而行吧,我的朋友。”这个视频装置位于一个半管状/波状/健身房状态的结构,小孩可以在那里玩耍,或者只要愿意人们也可以在那里睡觉。我觉得他们应该脱掉鞋子、弓向垫子,不过这在一个西方语境里,好像要求得太多了。

LP:我想跟你讨论一下我正在给惠特尼的画册写一些基于斯诺登档案的东西——不是从新闻的角度来写,而是理论和艺术的角度。
HS:是的,我想调查一下在土耳其发生的事情。在你给《明镜周刊》写的文章中,你详细地写了NSA与土耳其秘密警察之间的内部合作,以及所有手机通讯基本上都受到监听的事实。
而我碰到过那些手机通话在法庭上作为笔录被宣读的人:记者、政治家都因为所写的文章或者是在电话上的通讯而面临数年的监禁。这被视作是恐怖主义。在涉及新闻和舆论自由的方面,土耳其一直是出了名的糟糕。但现在我们看到了一条监控链:NSA为另一个国家的指控提供数据。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一切是如何运作的,这要感谢斯诺登先生。
LP:通过档案,你会意识到一切都像是一盘棋。有些是我们佯装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现实,然后另一些是表面之下的实际举动,在政治舞台之下的现实政治。我们已经在维基解密中看到过了。能够往里看看,并且真的看到深层国家势力运作,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HS:土耳其的情况证明了他们的国家如何受到西方监控的基础设施所支持,一种卓越的深层国家势力,并通过企业合作来升级。我一直坚信这些永远不会被透露出来。我在欧洲长大,而许多我的朋友——都是东欧人——都已经能够看到他们的秘密服务档案材料了,因为在共产主义垮台之后这些都解密了。但我们这些之前在西德的人一直没这样的机会。
在斯诺登泄密事件里,产生了真正的“之前”与“之后”。
LP:你所建立的叙事,以及你对原始文献的反复使用,让我想到了亚历山大·克鲁格,想到了他的电影和写作——他对一种对立的或是替代性的公共领域的坚持,他将原始文献作为出发点进行叙事和批判。
HS:是的,确实有不少手法是从克鲁格以及他与奥斯卡·内格特(Oscar Negt)的合作而来的。
LP: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已经失去了那种艺术与电影之间密切的、批判性的互相交织的关系。通常,当我去看当代艺术,并且是运动图像的作品时,我会感到失望,因为它看起来很简陋。有时候我看到画廊里的视频作品会想,哇,这个制作实在廉价。
HS:那其实还好。制作廉价并不是问题。但问题是,他们怎么能那么无聊?
你作品中的图像质量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你追求什么样的制作水平?
LP:我的作品从最早的16毫米到后来的数码标清,再到高清。但我并不认同数码和胶片之间有什么巨大差异。我的作品更多地受到人和叙事的驱动,即使我所想要的图像是电影式的。
HS:但是你拍摄时用的是小型的手持摄像机,不是吗?而且由你自己完成大部分的工作。在伊拉克和也门,你也都是自己完成的。而这种方式会决定你与被拍摄的人之间会有特殊的关系——那些为了能够拍摄而建立起来的关系。我觉得如果团队更大,装备更多,灯光更复杂的话,情况就会大相径庭。
LP:是的,确实如此,在伊拉克和香港都是这样的。两次都是很危险的处境,所以单独工作更有利。我愿意承担风险,因为这是我的作品,但我不想让其他人也去承担同样的风险。

LP:我的下一个项目将在惠特尼,而且我目前还不太清楚那意味着什么。美术馆的语境和公众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政治内容在美术馆语境当中如何受限?与电影院有什么区别?
HS:我觉得就政治语境来说,你不必担心。你可以用余生去搞抽象绘画。你可以高枕无忧了。你有通行证。
LP:我不太确定是否真是这样,或者我是否能指望这些。
HS:另外一个十分相关的问题,则需要依据具体情况来逐案判断。那取决于你要在那里展示的内容,以及它们如何与具体的地点进行沟通。
LP:我对于要做以装置为基础的作品很激动,因为它没有长篇叙事电影的约束。在叙事长片中,你不得不为了叙事某一环节的需要而只能选择那三分钟的镜头。我很期待从那样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可以让观众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叙事体验中,可以交出一些选择权。我不会放弃叙述——仍然会有开头、中段和结尾,有揭示也有转折点——但是观众进入作品的方式会更有活力。
你是怎么设计在艺术家空间的那种展陈方式的,还有那些不同的元素?
HS:总共有五件视频作品。然后在书店后面有个项目空间,我放了三个自己的讲座。所有这些讲座都以某种方式探讨作为战场的美术馆。其中一个讲座中,我揣测一种设置了障碍的舞台,无薪酬的艺术实习生们要向豪华陪审团推销项目想法。所以我们用FEMA的沙袋堆出一个路障来。你可以用它来阻挡洪水,或是躲避敌人的炮火。但是在书店里,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用作观看电视屏幕时的座椅。还有一个讲座是把幻灯片和动画投影到像是军事沙盘一样的东西上,就是那种士兵们用来绘制地形和分析视线的。我得知沙盘(sandboxing)还是一个计算机安全里的术语,你用它来隔绝虚拟环境。所以这就更像是展览中的游乐场部分,因为那不是艺术,所以你可以去玩和做实验。
LP:我当时以为是反过来的。因为那是艺术,所以你可以去玩去做实验。
HS:不过你要知道,它不被认为是艺术会更好,因为那样你真的可以随心所欲。
LP:那你明天要做的讲座是什么?
HS:叫做“免税艺术”(Duty Free Art),它是关于自由港艺术仓库的,一种域外的区域,与为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做重新设计和其他在叙利亚的建筑项目相衔接。在维基解密上,有叙利亚统治者巴沙尔·阿萨德的行政机构与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工作室OMA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当我联络OMA要求确认这些信息的真实性时,他们的回复真是天才:“我们没法确认(这些电子邮件的)真实性。”试想一下,假如这是对于艺术作品不同版号的确认模板:“我无法确认这件艺术品的真实性。”我们所知道的那个艺术界一定会炸裂的。
人们往往认为这些讲座是行为表演,但其实完全不是。那不是戏剧。那甚至不是个讲座。它更像是个谈话。这来自于我作为老师的教育活动。
对我来说,没有预算的时候我就会去做个谈话,因为特别便宜。我也乐在其中。它就像是一种财政紧缩的形式。你总是可以进退有余。你将自力更生。那个“自力更生”(Left
To Your Own Devices)本来会是在艺术家空间这个展览的名称。向宠物店男孩致敬。可惜我给忘了!
LP:这是个好题目——你改天得用用这个标题。
HS:这题目也很适合描述你的工作:自力更生!
LP:你的讲座似乎与你不断发展和重建的作品方式是一致的——作品里有一种自发的和瞬时性的方面。你从一个项目到下一个时,怎么持续研究?
HS:比方说,在创作《十一月》(November, 2004)时,我经常重新审视那些材料。这个电影是关于我一个在库尔德斯坦被杀害的朋友的;差不多每两年我会进行一次更新,因为事情的发展非常戏剧化。
在你这个情况里,斯诺登会联系你并不是一个巧合。而我当时是突然之间面临这一切的。安德里亚·伍尔夫(Andrea Wolf)是我青少年时期的朋友,她大约1996年的时候加入了库尔德斯坦工人党PKK的女子军队。最后在一场与土耳其武装部队的战役之后,她被法外处决。我与这一切都毫无关系,而且我耗时很久才明白个中情况。但是这定义了我现在的作品和生活。
LP:关于这个事件,你有哪些没能解答的问题吗?或者没有抒发的感情?
HS:嗯,这个案件还没有被澄清,而且可能永远不会澄清了。但我认为政治上,情形已经不同了。就如你在《明镜周刊》的文章中所写的,PKK现在或多或少是以美国为首的反对Daesh[ISIS]联盟中的一部分。那些过去被当作恐怖分子处决的女性武装分子,现在则成为争取性别平等的榜样。她们以巨大的勇气去争斗,但仍旧面临死亡。情况一直在转变,但是最为惊人的是在库尔德社会中某些地方的真正变化,他们向着基本的民主和探索性的自治在转变。在一场极端暴力的内战中,这是一个艰巨的、令人钦佩、而不断濒临危险的项目。
LP:那么你想继续研究和更新这件作品吗?
HS:并不是我想,而是它至今还没让我走出来。情况还在继续,也还在变化,而我觉得自己知道得还不够。也许有一天会的。
“黑特·史德耶尔”在纽约艺术家空间展览,直到5月24日。“劳拉·珀特阿斯”会于2016年2月5日到5月15日,在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展览。
文/ 黑特·史德耶尔 | Hito Steyerl,劳拉·珀特阿斯 | Laura Poitras
译/ 虔凡 王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