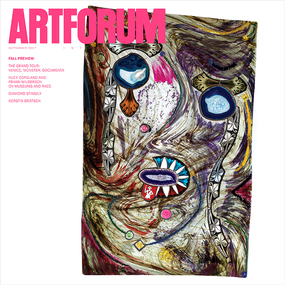风从何处来?风从树中来。
风从何而起?因树枝摆动。
树枝制造出了风吗?是的。
但树枝如何动起来?因为风。
——让·皮亚杰(Jean Piaget),《儿童的物理因果概念》(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Physical Causality, 1930)
大概在他去世前两年,哈伦·法罗基(Harun Farocki)展出了他的系列作品《平行I-IV》(Parallel I-IV,2012-14)的第一部分,这个由四个部分组成的环绕式电影成为了他最后一件重要作品。虽然法罗基的电影很多都是在研究科技和暴力图像的问题——从《眼睛/机器I-III》(Eye/Machine I-III,2000-2003)中反复出现的激光制导炸弹,到《严肃游戏》(Serious Games [I-IV],2009-10)里VR眼镜后身着军装、彻底迷失方向的士兵——但《平行》却显示出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克制,拒绝戏剧化事件,而是着意于探索我们越来越浸身其中的虚拟空间的结构和边界。
《平行 I》从对一个貌似细枝末节的问题的研究开始:在电脑游戏出现的前三十年里,对树的表现形式的变化。法罗基把这当作了一个艺术史的主题来处理,从而“引诱”我们开始真正地“观看”电脑游戏,而不是直接进入对其内容之暴力和残酷的批评。法罗基梳理出的历史中最早的树出现在《神秘屋》(Mystery House, 1980)中:一棵用锯齿状线条画出的巨型红杉。在这个游戏里,玩家需要通过打字输入指令在这个简单的环境里移动,而这棵孤零零的红杉其实无法“被游戏”,它仅仅是一个提示性的符号——冒险尚未开始:玩家仍然在房间“之外”。随着游戏的开发,对树的描绘也快速地进化了。从锯齿线到像素,它们先是获得了表面(surface),而后又拥有了体积(volume)。1990年代的时候,程序化纹理(procedural texture)——可以生成看起来拥有无尽细节的表象的碎形算法(fractal algorithms)——的开发制造出了诸如树叶之类的形态,而到了2010年代,照相写实主义的树已经开始可以在数字世界里的风的吹动下产生运动。随着这个系列的展开,法罗基把这棵树的变化当作了一个从命令列界面(command-line interface)到渲染世界的整体数字环境深化的转喻来处理。而当植物开始可以运动,我们发现我们已经不是身处一个文字历险里,也不是在《超级马里奥兄弟》(Super Mario Bros.)的绿宝石色背景里,而是在一个诸如《使命召唤》(Call of Duty)中照相写实主义的第一人称视角射击游戏中——那些空间是军事模拟和建筑渲染软件一同再现出的一个既熟悉又已摧毁的世界。玩家站在以写实主义风格刻画的美国城市,密斯式的摩天大厦被火焰包围,花岗岩的外立面布满弹孔。就好像在我们专心观察那些树的当口,末日到来了。
法罗基让我们看到,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电脑游戏快速上演了绘画历史教科书里讲过的所有变化,包括从象形文字到照相写实主义。这个加速的进化过程或许也可视作对摄影和电影历史的呼应,但不同于这两种媒介的是,电脑图形学无法从再现技巧进步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因为在电脑游戏里不存在被再现的外部世界。游戏提供了法罗基所说的——受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启发——“理想型”(ideal-type),指的是那些与实际的物件共享特征,但并不忠于或者呼应某个特定例子的模型。这点很说明问题,因为它揭示出,推动技术发展的并非对现实的忠实,而是对一种富有诱惑力的逼真(verisimilitude)的欲望。在这里起作用的是法罗基所说的“新构成主义”(new constructivism):在这个世界里,每一片树丛都是一点一点拼起来的,一个既无比细致又无比空洞的模拟物——你可以做到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现实主义在这里仅仅是一种感实性(truthiness)。
所以《平行》并非针对数字世界的考古学——技术进步的历史——而更像是一种数字人类学。此类研究的目标并非对进步的确认,而是对一个陌生世界内在逻辑的思考。法罗基和他的长期合作者马提亚·拉贾曼(Matthias Rajmann)为了这个项目收集了近千段影像素材。对如此巨大的素材库的分析——现在仍然保存在艺术家的硬盘上,尽管目前还没有对相关学者开放——显示出他们研究工作的彻底详尽。项目第一阶段(持续到2012年)收集的素材是来自政府和科学档案中记录云以及天气形态的影像,包括从最初那种粗糙的模拟图到更近期的电脑生成模型。这些转瞬即逝的现象的胶片以及数字图像的并置揭示出此类模拟物演进的背后驱动力。就像法罗基在2011年夏天写给拉贾曼的信中所说,“新项目令人兴奋,那些胶片先驱和数字余像。我想象着大海如何闪光,树叶如何在风中飞舞,沙子如何漂移。”
在2012年初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们研究的重心从电脑图形学的演进转移到电脑游戏的限制上。不用说,法罗基本人肯定不是个投入的玩家;所以他的田野工作需要一位“在地”向导。他雇用了拉贾曼十几岁的儿子连续几个小时地玩游戏(从档案来看,应该有几百次这种连续几个小时的活动),以此来获取完成作品所需的原始素材。而在《平行II-IV》里,法罗基给他的指令是不要想着玩赢,而是去探索典型的游戏世界建构中隐性的两种边界状态:一是可“被游戏”的世界的边界,二是跟电脑生成的角色之间互动的限制。在2012年的一封邮件里,拉贾曼描述了他跟儿子一起进行的一次“远征”,他的描述抓住了这个新世界的奇异:“我们非常缓慢地浮出水面,我们稍稍把头伸到水平线之上呼吸【…】我们研究了一个梯级喷泉,记录下了一些水滴的图像,那是从一个郊区房子门前的洒水车上溅出来的(屋内正在发生大屠杀)。在越南,我们在燃烧的房顶周围绕圈,热气把火星儿吹了起来,烟灰在空气中乱飞;等到靠近一看,发现是瓷砖在燃烧。”

把电影的理论性语言套用在这些游戏上是否还有任何意义?一些经典的电影隐喻在游戏中重新出现,而且貌似更丰富了。举例而言,法罗基观察到,循环(loop)时常在电脑游戏中出现,使玩家进入有关存在或者西西弗斯式的寓言里。归根结底,循环之于编码就如同它之于电影胶片一样原生和自然。但是,2014年在魏玛文化科技与媒体哲学国际研究学院(Internationales Kolleg für Kulturtechnikforschung und Medienphilosophie)的讲座上(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讲座),法罗基表达了在面对第一人称视角射击游戏的无尽流动时,现代主义电影的决定性概念——蒙太奇,通过单个镜头的碰撞而建构意义——明显的无力而引发的沮丧之情。
这些游戏在一个延续且线性的空间内展开,从第一代《超级马里奥兄弟》中的滚动带,到《反恐精英》(Counter-Strike)里的浸入式环境,时间被锁在一个永恒的当下。玩家沉迷其中的并非蒙太奇的梦境逻辑,以及非连续性的并置,而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梦境,它根植于那些在无缝空间中蒸发的事件带来的惊奇。理解游戏空间需要一种类似让·爱普斯坦(Jean Epstein)“影灵”(photogénie)的概念,指的是电影中无法言喻的那些东西——比方说,树叶的摇动,油迹表面的反光,或者是深水面上浪的运动——复杂的运动,其中每个单独的构成元素都无法清楚地区分出来,而且常常是处于意识边缘的。这种效应最有名的例子是卢米埃尔兄弟1895年的电影《婴儿的午餐》(The Baby’s Meal):据说观众对背景里树叶震颤的兴趣远大于镜头前景里被喂食的婴儿。
就像第一拨见到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的照片《自然画笔》(Pencil of Nature,1844-46)的那些人惊叹草堆的细节一样,早期的电影观众也惊叹于微风拂过草坪时的波动。在爱普斯坦1947年的电影《风暴》(The Storm Tamer)里,一个在海上风暴中失去未婚夫的女人遇到了一个老人,他用一个水晶球掌控着风。老人控制自然元素的能力只有当水晶球摔碎才会被终止。“影灵”的持续性和蒙太奇的剪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达到这种流动状态正是电脑图形学技术改进背后的目标——或者说,它的本能驱力(libidinal drive)。正如《风暴》中的水晶球,电脑图像的世界是自足的。它的诱惑力并不是受限于它将自身从虚空中拖出来那种努力,而是部分得益于此,风继续吹,正如在让·皮亚杰的寓言里,风动和树动的因果关系是无法区分开的。
作为对电脑生成图像历史的思考,《平行》可被视为法罗基对电影命运毕生探索的延伸,同时亦可视作与该项工作的大胆断裂——一件反思性的脱离之作。法罗基曾经表达过对辞典以及百科全书持久的热爱,尤其是“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这一堪称笨重的德国类型。概念史介于辞源辞典和哲学百科全书之间,它所记录的是哲学词条的历史,包括它们如何使用,被谁使用,为了什么目的而使用。法罗基认为这种哲学性比较的意义在于,它们可以让我们对语言的使用更加敏感,他也提出了一种类似的概念——他称之为“电影百科全书”(cinematographic thesaurus)——应该使之成为图像研究的工具。从美学力量来看,《平行》可被解读为对此项研究的贡献,即便胶片本身已经成为历史,它却构成了对电影辩证历史的延续。
亚当·贾斯珀是巴塞尔大学的研究员,也是《CABINET》杂志的特约编辑。
译/ 郭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