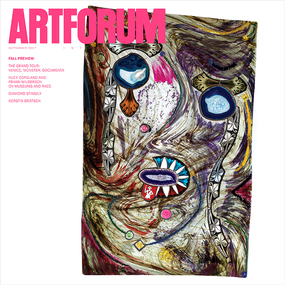等待进入安妮·伊姆霍夫(Anne Imhof)的德国馆的队伍需要排上两个小时。几只杜宾犬在一座十二英尺高的围栏后踱着步,我们不耐烦地等着,队伍里满是驯服的游客,他们不修边幅,疲倦不堪,汗流浃背,还背着一些印有其他艺术家和国家名字的帆布袋。而对于“懂行”的观众来说,德国馆的包才是最难拿到的,也是所有的包里面最好的,那是一只黑色的涤纶拉绳背包,上面印着艾利萨·道格拉斯(Eliza Douglas)没穿上衣的照片——她是艺术家、模特、伊姆霍夫的女友、这个潮流感十足且神秘兮兮的展览《浮士德》中的明星。
在里面,这座新古典主义的艺术殿堂被剥离得只剩下基础结构,这是一种只有金钱才能购得的极简:由不锈钢支架连接的厚玻璃墙和抬高悬空的玻璃地板塑造了整个空间,与波林·赛文斯基·杰克逊(Bohlin Cywinski Jackson)设计的苹果专卖店有几分相像。位于中间的房间里容纳着大部分动作,而两边的小房间——一间靠近入口,一间靠近出口——则提供了俯瞰表演舞台的视角,一些大幅丝网印图画是表演的装饰,上面重复印着又没穿上衣的道德拉斯,她张大了嘴。
媒体预览那天,伊姆霍夫站在空间的边缘审视自己的作品。她穿着黑色牛仔裤、黑色靴子、黑色耐克拉链外套以及一顶黑色棒球帽,上面印着白色字母的BALENCIAGA。神情冷漠而因此性感的表演者,一次六个或者七八个一起出场,他们在玻璃地板上的我们之间穿梭,有的栖息在视线高度的斜玻璃架板上,亦或站在距离人群二十英尺高的玻璃走道上。
作品持续了大概四五个小时,房间里有一条即兴表演的固定路径,还有许多标志性形象:道格拉斯站到建筑后侧的高玻璃板上,脱去她的上衣,仰望着人群的上方;表演者发出刺耳的尖叫,在我们之中以走T台的方式来回行进;道格拉斯对着麦克风唱一首凄凉的歌。
我们自在地在空间内移动,拍着并传播着为Instagram量身定做的图片,表演者漫不经心地看着又无视着我们的拍摄镜头。伊姆霍夫和她的团队通过他们iPhone上的WhatsApp交流,互相反馈,即时调整。我们观看着,无论是着迷还是沮丧,都被排除在他们的代码之外,而他们在地板上旋转、以头抢地、滑行,或者在玻璃地板的下方匍匐,向我们的脚伸出他们的拳头。他们震慑着,恐吓着,或者游手好闲,用弹弓射击青铜钟罩。他们在玻璃下面的大理石地面点燃火焰:获得金狮奖的那天,他们往奖杯上浇酒精,付诸一炬。

已经有不少笔墨花在这个展览中绝妙的建筑构造以及富有感染力的动作集合上,但是,这个表演包含了一个更加无形的特征:选择性——要知道,它来自一个曾经在著名的法兰克福周边夜店“罗伯特·约翰逊”当看门人的艺术家。表演者中有伊姆霍夫那美丽的道格拉斯、钢铁般冷峻的弗兰齐斯卡·艾格纳(Franziska Aigner)、傲慢而英俊的比利·布勒希尔(Billy Bultheel)以及谜一般的米奇·马哈尔(Mickey Mahar)。《浮士德》证明了创建一个场景所具有的力量,随后将其中的事物全权移交给一群穿着潮流服饰的伟大表演者。
衣如其人。在《浮士德》中,这些悲伤的/运动型的模特为我们带来的,是1995年左右史蒂文·梅塞(Steven Meisel)拍摄的CK One广告,我指的是理查德·阿维顿在1969年拍摄的“工厂”系列照片,甚至是2016年丹纳·格瓦萨里亚(Demna Gvasalia)设计的潮牌Vetements,同时我说的还是格瓦萨里亚在同一年设计的Balenciaga。波西米亚变成了车库摇滚,海洛因时髦(heroin chic)变成了养生哥特(health goth),或者只是山寨Margiela,而这一切态度变成了……一个漫不经心、为叛逆而叛逆的图像库,只有结果没有起因。
也许起因被过度重视了,也许时尚被轻视了。我认为道格拉斯在为伊姆霍夫当表演者时与她在为Vetements或者Balenciaga做模特时一样好看。伊姆霍夫则向着虚空纵身一跃,摆出一些熟悉而高质量的pose,她威尼斯画册中的配图是她的团伙在一间阴郁的工作室里营造气氛。《浮士德》是一件至高无上毋庸置疑的酷作品,但是也并不是无情的。它是一封蔓延生长的情书——来自神魂颠倒的伊姆霍夫致以道格拉斯的史诗般赞歌,我也倾向于觉得,它向伟大男人们的专制发出了一句终极的“操你”。《浮士德》是一个男人的故事,至少在歌德讲述的这则著名的故事中是这样:海因里希和靡菲斯特以他们自己的形象来重新创造这个世界,而女人们(格雷琴、海伦娜以及那可怜的瓦尔普吉斯之夜中的女巫)则仅仅是通往拯救之路上的道具。如今,地球又一次落在了一个与魔鬼做交易的傻瓜手里,但忘了什么救赎吧,我把赌注压在沙弗式的(译注:有女同性恋色彩的)虔诚上。
《浮士德》在威尼斯双年展德国馆持续展出至11月26日。
大卫·韦拉斯科(David Velasco)是艺术论坛英文网和MoMA出版的《萨拉·米克逊(Sarah Michelson)》的编辑。
译/ 张涵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