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球在转变。权力在转变。我们正在经历一种范式转移,说到底,这种范式转移可能和通常与“早期现代性”这个标题所绑定的一系列时代断裂具有同样程度的后果。如今当我们面对自己所经历的变化时已经找不到任何系统性的诊断了。在我们能够发明出有效的抵抗策略之前,我们需要勾勒出那些已经在运行的权力,并且铸造一套批判语言,来匹配我们的周遭。而这一状况,反过来,也使我们的批判重点发生了转变。
大部分对于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的研究都围绕着一些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核心特点的进程:经济的金融化、价值的抽象化、信息的数码化、计算互联网络的扩延、工业自动化以及劳工的机器人化。在这些研究中,权力依旧被主要理解为对生产形式进行拨用、管理以及自由化的社会规则。虽然对生产(production)本质的变化进行理论化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充分地阐述权力与“再生产/繁殖”(reproduction)相关联的一面。
在再生产/繁殖的领域——性、社会、文化——中,我们直面着当代权力最关键的层面。权力与生命之间的关系正在经历着最为剧烈的变异。在这里,我指的并不仅仅是70年代流行起来的福柯式的生命权力(biopower),而是权力对一切生命产生作用的一切渠道:从纯粹力量、暴力以及赐予死亡的能力(死亡政治学,necropolitics),到解码、保存、复制以及修改生命形式的潜力。“统治我们自己的艺术”,人际关系,体制机构,话语讨论,那些使活着的生物体被视作为“人类”、被视作为一个可繁殖的公民的技法,一具(有机的或机械的)身体有能力说“我”所需要经历的过程,这些,都在变异。
根据许多不同的知识社群的定义,生命最基本的意味,是一个可以维持和繁殖自身的系统。为此,该系统必须将能量(食物、阳光、化石燃料等)转化为热量,并将这些能量中的一部分分配给新陈代谢,如此才可存活并繁殖。任何一个政治政体都对捕捉和分配能量以及繁殖生命的集体性方式进行管控。就那个历史上被视作为人类的物种来说,繁殖的生物代码可能已经被符号学代码以及始终在加速流动和变异的语言、知识和实践——也就是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东西——所匹配,甚至超越。而文化的演变(技术、意识形态)也反馈在对生命的管控上,它影响着,甚至阻挡着权力执行其基本任务的方式——它的基本任务是控制和管理生殖。
自由派和共产主义的权力理论都将繁殖自然化了,并视之为无历史的(如果他们还会考虑繁殖这件事的话)。因此,对繁殖进行去自然化(denaturalize)便是紧急的、必须的。为了达到此般目的,下文就是对权力体系进行历史化的一些笔记,这些体系在其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体中操作生命,它们也构成了作为主角的我们——作为“活着的政治小说”。围绕以下三种权力技术类型的互动,我们可以更为便捷地思考历史。
第一种是古老的死亡父权制(necropatriarchal)权力体系,在其中,只有男性身体才是有主权的身体。妇女、儿童以及非人类生物体的身体都是次等的。在死亡政治术语中,男性主权是由其作为暴力的合法垄断者而定义的。父亲的和男性的权威是原始的、绝对的。父亲就是那个有权利赐予死亡,决定他妻子、孩子以及所有其他依附者命运的人。死亡父权制对主权的这种定义是最古老、也是最广泛的权力行使方式,展开来看,它相关于自然资源是榨取主义(extractivism)、相关于领土是占领、相关于社会领域是统治,而相关于性是强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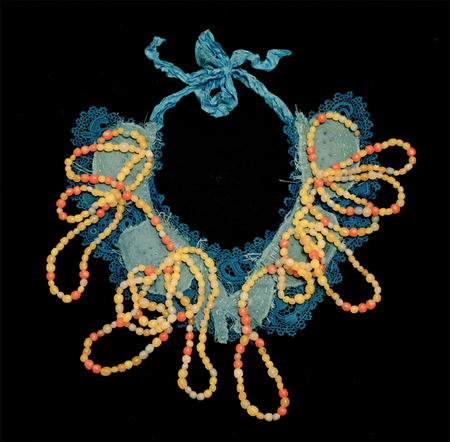
第二种是异性恋-殖民(heterosexual-colonial)权力体系,它伴随着现代性发展起来。十五世纪开始的资本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生产系统覆盖并超越了父权主权。异性恋-殖民权力体系的存在离不开种族这一新型政治分类,种族政治动用了新兴的经验主义,以及被用以合法化种植制度、奴隶制度以及反种族通婚法规的科学解释。对于性别差异、异性恋和同性恋的那些(显然是)解剖学的以及精神病理学的认识,在殖民帝国中统领着繁殖的实践。莫妮卡·威蒂格(Monique Wittig)、吉·沃康格姆(Guy Hocquenghem)、安吉拉·大卫斯(Angela Davis)、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杰克·霍伯斯坦(Jack Halberstam)、阿基里·姆本贝(Achille Mbembe)等人都已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见解,细数了异性恋常态化(heteronormativity)和种族这两者分别被构建为性别和人相学条件的诸种方式,作为对比的,是那些决定我们的身体在一个生产和再生产/繁殖体系中所处位置的权力技术。女人、孩子、有色人种、原住民、“残疾人”、离经叛道者,以及动物,都被视作为非人类,以及作为下等公民(infracitizens),他们没有渠道获得统治思维或者知识生产的技法,也对作为人类首先意味着什么这一点的支配性构想没有任何影响力。
十九和二十世纪那被标准化的异性恋制,与它关于身份和差异的逻辑一同,加固了性别-工业泰勒主义化以及生殖器福特主义(sexo-industrial Taylorization and genital Fordism)。这种对于性别的医药法学认识,使得生物繁殖越发地快速、廉价,以此来打造工业主义和新民族国家中的劳动力。其终极结果:将作为社会基本构成单位的核心家庭奉若神明——互相隔离,围绕繁殖来建构,并且易于迁移,利于促进种族和经济区隔。现代性不仅发明了一种新的、适应机器的劳动身体,而且还发明了一种新的灵魂,其有能力只对那种生殖利润丰厚的性产生渴望。
第三种权力技术是药物色情(pharmacopornographic)体系,它从六十年代开始崛起,尽管它的开端可以被追溯到1953年科学家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这一体系由对基因组的绘制和操控而定义,也由使用荷尔蒙和手术技术以改变身体的样貌和新陈代谢而定义,还由人们对社会性别、雌雄同体、跨性别的全新认识而定义。这些新的社会管理形态是对性别差异的认识危机的回应。已经很清楚的是,社会性别无法被缩减到两性,也无法被所谓的生殖器官的形式所定义,然而,医药和法律机制却仍坚持在技术上重构这种二元性,以维持社会等级制度。与此同时,控制着异性恋繁殖的技术在最近几十年逐渐外化。首先,(女性避孕)药片将异性恋与繁殖分离,这,将使原本合法化异性v.s.同性恋的解释变得老旧,在那种概要中,正常的生殖的性与病态的非生殖的性是对立的。第二,随着体外受精的出现,性重组开始在身体之外发生。很快,外在子宫的工业化也将使男性化和女性化之间的区别变得远古。有机育种者和人工育种者之间那不可避免的区分,将伴随着一种新领域的诞生:繁殖工人。第三,因特网,这个全球化的多媒体自慰义肢,将提供无限的色情和消费渠道,它也将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一种已经四面楚歌的认识,即身体作为生殖能量的容器、只为怀上孩子而存在。
药物色情生产和再生产/繁殖似乎需要一些“有创造力的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时刻。在二十世纪中叶,对于放射性元素的利用赋予了人类摧毁这星球上每一种生物体(可能细菌除外)的权力。核战争始终作为一种可能性悬置着,并且将药物色情技术与死亡父权冲动联系了起来。外部辅助生殖、基因组改造和货币化的新技术,以及灵魂设计的新型干预,这些药物色情举措中有一种潜在的死亡政治协同作用;所有的这些现象共同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来对其他人类以及非人类生物体进行控制、排斥以及歼灭。用基因和生物群系来武装自己的战士会带来意外后果,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或预测。我们需要对这个新状态负责:我们是第一个有能力摧毁这个星球上生命的物种。

简言之,地球上生命的存活全依赖那些生产和再生产/繁殖的合作与共生技术发明。
社会与文化再生产的语言符码的演变,是调查权力行使的关键元素。学习可以被视作为基因重组的一个文化类比,它也是个体与集体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异,或者适应快速变化的方式。我们如何从共有的历史中学习?是不是有可能用非死亡政治的术语来定义一种新的男性化形式。是否有可能将家庭和民族国家去父权化和去殖民化?有没有公平合理的方式来治理对生殖液体(精液、乳汁、血液)、器官(子宫)、细胞(胚珠、精子)以及基因材料的使用?可不可能将这些东西重新分配,甚至将它们集体化?我们必须将文化重组的原则应用到对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策略上,如此才能改造权力技术,才能(在政治上)变异。
我们生活在一个权力的技术与体系重叠交杂的巴洛克时代。我们并非面对着历史时期那清晰而平坦的地层,而是一种令人晕眩的复杂地形,其中充满着互相联通或短路的力量。有时,有着剧烈差异的技术之间可能建立起预料之外的联系;有时,两种或多种技术会为了控制和占领同一种能量路线、同一些生殖液体、细胞、器官或者身体而斗争。比如说,民族国家和生物医药产业为了控制女人的子宫而竞争,前者竭力使作为生殖免费劳动力的妇女继续成为国家资源,而后者则梦想着将子宫改造成臣服于自由市场经济的生物环境。特朗普时代是死亡父权制权力技术的高峰期,同时履行着种族和性别的殖民含义,并具有高度复杂的药物色情体系框架。然而,这个全新的数码与生物技术法西斯主义也可以是最后一个。
保罗·B·普雷西亚多(Paul B. Preciado)是一位哲学家、策展人,以及跨性别行动者。他是文献展14(卡塞尔/雅典)的公共项目策展人,目前为法国阿尔勒LUMA基金会的驻留作家。
文/ 保罗·B·普雷西亚多(Paul B. Preciado)
译/ 张涵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