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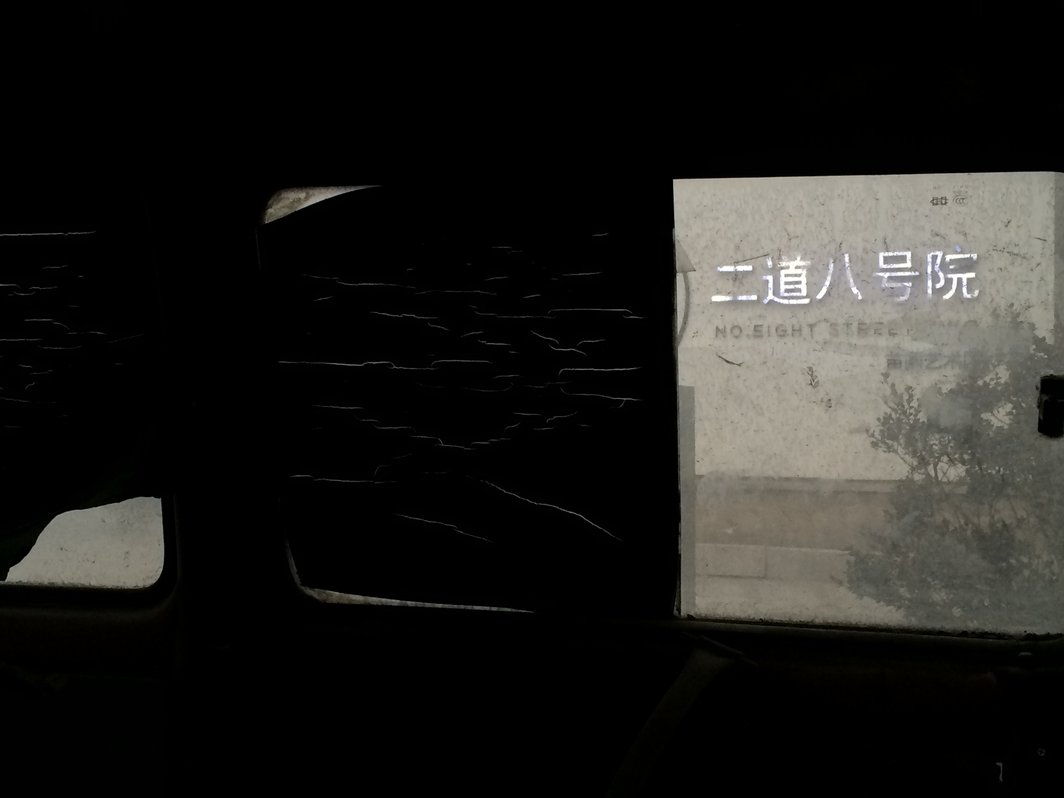
去年年底,飘荡许久的黑桥拆迁传闻终于落为了一个具体期限:2017年2月底。艺术论坛邀请了三位前黑桥居民共同完成这则“北京来信”:面对政策性的搬迁令,黄静远和曾宏分别从微观日常生态和共同立场探寻角度提及了“30分钟内不收费”所喻含的一种短暂的苟且;同时,贺勋通过照片和图释的方式捕捉了节日中萧条的二道八号院——可能是黑桥艺术区最后的样貌。曾宏在文中提醒我们,艺术家只是黑桥所有居民中的八十分之一,少于村民,远远少于同样临时落脚于此的外来务工者。在浩浩荡荡的人口“疏解”及流离失所中,能被听到的、被“呈现”的,只是冰山一角。
黄静远:
不算遥远的黑桥停车乱收费事件,从一个住在黑桥的普通人的角度来说,历经了这么几个步骤:先是用石头铁丝等等把其他几个通向黑桥的门堵住;再是在仅剩的几个入口派出拦车收费的大妈等一些厉害角色(当时的冲突是明显而常见的:语言的撕扯、肉身的碰撞、以车为盔甲的敌对、以艺术家设计贴纸和录像为方式的奔走相告、以派出所为据点的恐吓);然而,不知什么时候起,这些可以去冲突的“对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文明的机器关卡:一人一杆,车号自动识别,超过三十分钟开始收费,走的时候还祝你一路顺风。本质虽然没有变:杆的里面是依旧乱烧垃圾的黑桥,杆的外面是乱停车长达一公里多的“公路”;但是冲突的几率变了: 你不可能对一个平静地坐在岗亭里面的穿制服的年轻人做出多么粗野的冲撞,你更不可能对那个根据车号自动起落的栏杆进行多么深刻的报复。
石头铁丝和彪悍的大妈,岗亭和自动化的栏杆,这就是一个连环套餐。所以2016年末公布的黑桥拆迁事情不过是套餐里面最不让人惊讶的部分。只是,在拆迁里我们既无法识别也无权知道在种种幕后的角力中哪些是石头铁丝,哪些是文雅的岗亭。
不过,对于多数擅长视觉的艺术家来说,还是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可见”的。比如白夜照相馆就倾情奉献召集大家到二道八号的标志风景人工小湖和喷泉前,拍了有特定技术含量的大合影;艺术家坎保一直以来就有对焦黑桥艺术家的黑白摄影记录;不少艺术杂志和媒体也迅速的做了采访和收集;还听说ACTION MEDIA想找在黑桥的外国人来问问。近期最可见的事件可能是一场名为“黑桥一代”的展览。展览承办地Hi艺术中心的负责人伍劲在开幕式上就提出希望“把它做成一个有规模,有质量,历史性,现象级的文献展”。这多少让我想起红砖美术馆正在展出的温普林文献展:如果说温的文献“赢”在技术上我有你无+意识上的先人一步,走了从强大私有化到强大公众化的线路;那么“黑桥一代”则是在一个技术上人手一机+意识上时时刻刻自我历史化的情形下、对他人历史时间的有意诱惑。


另一种“可见”,是这个过程的即时的图像化和文字化,这便是微信群聊。从某时某刻拆迁消息确认开始,二道八号的住户群就开始毫无预设但自觉地进入了几个程序:先是关于新的艺术区的广告(从单户转租到大型厂房招租)、搬家公司推荐,再到大量的二手/囤积物品转让(最后发展到参与性颇强的竞拍),穿插其间的是各种程度的缅怀,导致求偶贴也不慎流入。这让我觉得一直以来的热词“艺术家自我组织”真是过于形而上了。而且这种“共同体”来得甚至有一点偷窥的意味:完全不相识的十来家人的灶台和洗衣机的档次和新旧程度(以及各种其他自带细节)一下子扑入眼帘。我不得不开始推测: 也许情怀的意思就是"交易所及,诗意必达”。
但是,哪怕是擅长“可见”如艺术家,也很难使得自己的未来“可见”。有一些预测已经在口口相传:黑桥之后再也没有离798等艺术集中活跃地点如此之近又具如此规模的艺术工作室群落了。住得分散是否对艺术能量有害这点难有定论,但是从现在这种情况看来,会住在一起的多少已经是有某种相似性的创作者。宋庄、李桥、燕郊,大家越搬越远。想慢慢试着在北京找自己在当代艺术里的可能和位置的“摸石头期”会越来越短。“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或者俗称“把北京搬出北京”)既然是顺理成章的前进方向,艺术在这里,其实只是小小顺带“伤害”到的。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冬日雾霾天里难民一样的找新家搬旧家,每个受到影响的艺术家都在寻找自己的方式来承受和应对。如同每一次灾难提醒我们的:总是弱小的最容易受到影响和伤害。
黑桥的拆迁是一个典型的北京跨年动作,既横扫一切,又又慢又痛。如果说黑桥乱收停车费和过路费只是一个糟糕空洞的电视连续剧的话,那么黑桥拆迁就是一个把电视机电视台电视卫星接收器全部一端而走的大清理。站在春晚开始前的绝好回顾时间点上,最近我们又被赐予了一个新的新闻,关于我们上网的未来的新闻。它证实了一点:前面提到的石头铁丝和彪悍的大妈+岗亭和自动化的栏杆的套餐,它已经是我们的网络生活现实,会更加坚定地成为我们的未来。


曾宏:
如果没有暖气,北方的冬天就是酷刑。而这个季节,也是政府驱赶底层人离开北京的最佳时机。黑桥的拆迁消息公布之后,李三在hi艺术公共平台的留言令人倍感温暖:“我是市场一杂货摊主,文明朴实的你们,是黑桥唯一的亮点”。在摊位上,他的妻子说:“你们都走了,我们留下来干什么?”我理解她说的你们,是指这个村里所有的人。仅仅两个月前,院里的电工小时,也说了和她同样的话。这似乎说明,艺术家和外来务工人员之间,并没有那么遥远。
2015年,在黑桥村口爆发停车收费事件时,数名现场录像的艺术家被带到派出所询问,在派出所外声援的人中,有一多半都是外来务工者。这件事将从未交集的两个群体临时聚集起来,而在今天,这也许是突发事件的价值所在。
今年4月,崔各庄乡的网站上公布了所辖的黑桥村的规划情况。按常规,规划之后如果没有立项达成,也就意味着动迁遥遥无期。然而,这次仅仅在规划宣布的半年多后,既将开始动迁,其行政的力度是前无仅有的。按照村民的说法,“有房本的留,没房本的走。过去是先拆,政府补偿租金直到安置完成,现在是先不拆,但对没房本的建筑断水断电,目的就是赶人。”
坊间传闻,北京市长的更换和对外来人口的驱赶息息相关,在公开的数据中,朝阳区的外来人口压力是最大的。仅黑桥村就居住了近8万人,其中村民只占2700人左右,其余7万多人都是外来务工者,也包括近千名艺术家和家属。


2015年,二楼出版机构和李一凡联合发起了“六环比五环多一环”的艺术项目,在皮村工友之家的座谈会上,发起者希望“艺术家像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样,深入到五环以外的外来人口聚集地,以了解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而今天,多数艺术家发现自己和所有居住在这个区域的务工者一样,有着相同的生存处境。
刚到黑桥的时候,听朋友谈论2008年以后的经济走势:“经济一旦崩溃,人民就上街了,我们这些艺术家工作室,首先会被那些住在村里的暴民洗劫一空。”不知道今天艺术家们还有没有这样中产阶级式的忧虑,二道八号和村里,只隔着一条臭水沟而已,而今天的政治和经济困局也已不是那时候可比。至少,把革命寄托在经济领域的崩溃和把民主寄托在中产的崛起一样,都是同一种思维方式。而中产梦和中国梦一样,已被“人无贬础,中或最赢”式的焦虑所淹没。
1995年冬天,在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前夕,政府对聚集在福苑门村的艺术家进行驱逐,不少艺术家被驱逐之前都有在沙河和六里渠被强制劳动和遣返原籍的经历。如果说90年代的艺术家,为了拒绝体制化生存、宁可选择游荡者一样生活方式而成为政府眼中的不稳定因素,那么今天的艺术家已被牢牢地捆绑在艺术体制的生产链条中,成为了另一类产业工人。
在多次公共领域事件发生之后,有感于艺术圈对此类问题的无视,有朋友在微信上发帖:“真希望艺术区来一次强拆。”但今天的艺术区,恐怕也不会再有“暖冬”那样的事件发生,没有开发商和资本进入的愿景,艺术家也不再具有单独被清理的身份,而是和所有那些外来务工者一样,属于“疏解非首都功能”政策中即将被清理的低端人口。
文/ 贺勋 黄静远 曾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