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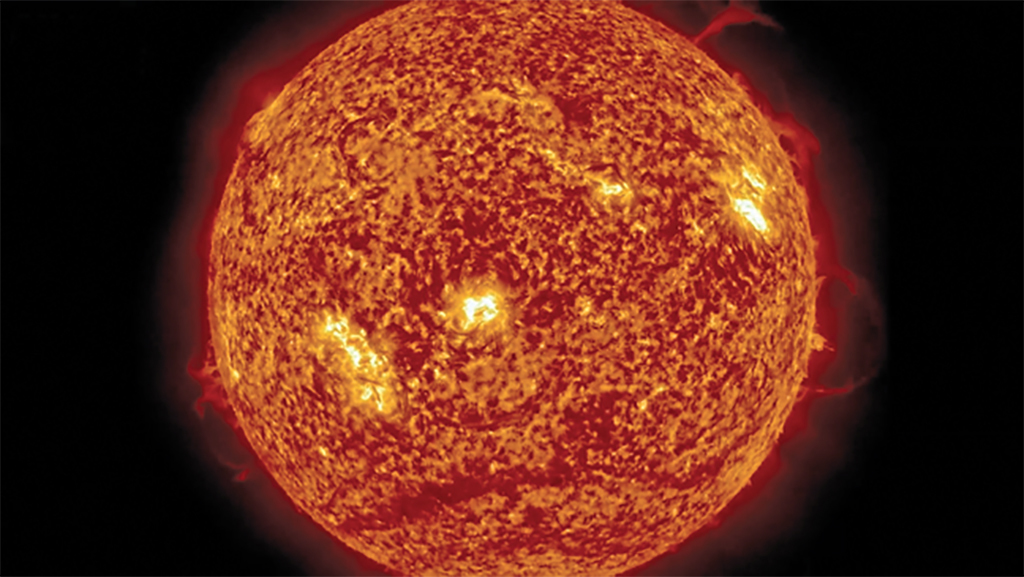
2018年3月26日-9月27日,在美国亚洲文化协会(ACC)的资助和支持下,我在纽约进行了为期半年的驻留。期间,完成了关于《十月》杂志的调研,先后采访了10余位编辑和作者,并收集了数百份档案资料;与此同时,比较系统地观察和了解了纽约的画廊、美术馆、非盈利机构的运作以及整个纽约艺术生态的结构。本文是根据半年来的一些点滴体会整理而成的,谈不上深刻的认识,只是一些浮光掠影的感受和体会。
2018年9月18日,由The Met Breuer举办的《一切皆有关联:艺术与阴谋》(Everything is Connected: Art and Conspriracy)低调开幕,原以为这样的话题会激起些许波澜,结果同样被淹没在纽约成百上千的展览中。展览搜集了上世纪60年代末至2016年特朗普上台之前的70余件有关艺术与阴谋的作品,涵盖了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美国或涉及美国的所有那些诡谲而尖锐的政治事件,包括肯尼迪遇刺、尼克松访华、水门事件、黑人运动、伊拉克战争、9·11恐怖袭击、国家监视系统、无人机战争伦理等等。从中可以看出,五十年来艺术家作为行动者是如何介入种种政治丑闻和不正当的权力机制的,以及他们是如何应对官僚系统的欺骗、公共媒体的阴谋等隐匿的政治逻辑的。展览的时间节点卡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前,但事实上,在纽约的半年里,我所看到和感受到的更多是艺术家、策展人们对于特朗普时代的焦虑、不满和抗议,这也使得种族、性别和阶级这些陈腐但永恒的政治议题又“卷土重来”,几乎占领了整个纽约艺术界。时至今日,美国知识界和艺术界中的精英们似乎依然无法理解特朗普何以会当选美国总统,何以全世界都在右转,何以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会大行其道。
三个月前,位于纽约切尔西画廊区的非盈利机构The Kitchen与种族想象研究所(The Racial Imaginary Institute)合作呈现了一场集放映、表演于一体的活动,内容是两年前美国大选期间,发生在美国城镇街头的种种抗议行动。其实不光The Kitchen,像e-flux、Creative Time这些机构也曾数次举办类似主题的讲座和表演。自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民众的情绪非但没有消停,反而更加肆虐,四处蔓延,到处可见调侃、讽刺特朗普的街头涂鸦和艺术作品,还记得特朗普和金正恩会晤没过多久,哥伦比亚大学MFA的年度夏季展上便已出现相关题材的作品(Taejoong Kim, Silent Scenes, 2018)。也是在这前后,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重磅推出了艺术家Andrea Fraser的新著《2016年的美术馆、金钱和政治》(2016 in Museums, Money, and Politics)。这部厚达900多页的调研报告以特别的方式记录了2016年也就是大选期间,全美100多家美术馆、非盈利机构与竞选政治、文化慈善事业及竞选资金之间的复杂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其中各自所占的比重,显然,除个别外,大多美术馆和机构的董事会依然由民主党主导,在纽约更是如此。期间在关于《十月》(October)杂志的调研访谈中,当最后问及特朗普时代的美国艺术与政治时,Rosalind Krauss,Yve-Alain Bois,Benjamin Buchloh这些美国学者中没有一个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和拥戴者,对于当下纽约很多艺术机构乃至整个艺术系统的政治化及其带来的反智倾向,更是表现出不满和不屑。这并不是因为民主党是纽约大多艺术机构的最大金主,而是无法容忍和理解特朗普的一系列政治举动及其上台以来所导致的美国乃至整个世界政局的变化。
惠特尼美术馆去年开幕的以政治抗议为主题的馆藏展还在持续的发酵,广受好评的Adrian Piper在MoMA的大型个展也事关种族议题,而一向激进的布鲁克林美术馆连续几个大展都是围绕种族、性别和身份展开的,“我们想要一场革命:激进的黑人妇女,1965-85”(We Wanted a Revolution: Black Radical Women, 1965–85)之后(这个展览后来巡展至Boston的ICA,同时开幕的还有Arthur Jafa个展“爱是信息,信息是死亡”),紧接着推出了拉丁美洲激进女性艺术家展(Radical Women: Latin American Art, 1960-1985),最新的馆藏展“国家的灵魂:黑人权力时代的艺术”(Soul of a Nation: Art in the Age of Black Power)同样是以黑人为主题,甚至连位于曼哈顿中城的纽约市立图书馆也在举办纪念民权运动的文献展:“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60年代的记忆”(You Say You Want a Revolution: Remembering the 60s)……不过,真正具有煽动力和政治性的还不是这几个大型展览,而是Arthur Jafa在Gavin Brown’s Enterprise(GBE)的个展“山上的空气,未知的愉悦”(Air above Mountains, Unknown Pleasures),Leilah Weinraub去年的影片《搜查》(Shakedown),以及加纳血统的英国艺术家John Akomfrah在新美术馆的大型个展“帝国的符号”(Signs of Empire)。巧合的是,他们几位——包括去年在新美术馆举办个展的艺术家/电影人Kahlil Joseph——之间都或多或少有着一定的关联,甚至还有不同程度的合作。合作的前提自然是有着共同的志趣,透过他们的作品,其实我们也不难觉察到这些,或许这是黑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质地和力量,而它们真正吸引我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久违的气息和动能,就像波德里亚说的:“黑色这一暗肤色种族的色素,就像一种自然妆容,受人工妆容映衬,成为美的组成要素——不是性感的美,而是动物性的、崇高的”,并“具有一种隐秘的和仪式的力量”。美国种族题材的电影我们并不陌生,如曾经与Arthur Jafa合作过的导演Spike Lee的《为所欲为》(1989)、《马尔科姆·X》(1992)、《种族情深》(1994)等系列作品,近年备受好评的Steven McQueen的《为奴十二年》(2013),以及由Ava DuVernay执导、以1965年马丁·路德·金领导的从塞尔玛向蒙哥马利进军的事件为底本的《塞尔玛》(2014),更早的还有Arnold Perl执导的纪录片《马尔科姆·X》(1972),等等。历史的排演固然提供了政治和情感的动能,但其内在的复杂性又不可避免地被“政治正确”所抽离或简化。Arthur Jafa其实是近几年才从好莱坞的电影摄影师转行到当代艺术界,也许剧情片已经满足不了他的情绪和欲望,他需要更直接和更有力的方式传递他的愤怒、不满和爱。诚如他所说的:“我向往复杂性、细腻和美,这些都是我珍视的东西,也是我作为一个黑人天生被剥夺了的东西。……历史上,当黑人进入西方社会的时候,没有被当作人看待,而被当成物。所以我们与物品的生命有一种非常疯狂、复杂的联系。在我看来,我们介于主体和客体之间。”(Nell Frizzell,《卫报》采访,2017.10)因此,他惯用的“伎俩”是,在黑人政治与大众文化之间找到寻找一种持续的起伏和连环的撞击,如果说激进的黑人运动唤醒了沉睡的大众,那么大众的参与则给予了黑人政治一定的能量和推力。

五十年前,一场革命几乎席卷了全世界,然而在美国,抗争和暴力其实已经持续了多年,至1968年,由于越战和黑人解放运动相互裹挟,风暴再度激化。此时距离美国黑人运动的英雄和领袖马尔科姆·X(Malcolm X)遇刺身亡已经三年,但抵抗、冲突与暗杀此起彼伏,从未消停。“与被美国官方和主流接纳、修改的非暴力运动领导人马丁·路德·金不同,马尔科姆从一开始就展现了抵抗者决绝的态度,他对白人政权毫无幻想。”……他曾说过:“如果暴力在美国是错误的,那它在海外也应是错误的。如果保卫黑人男女老少的暴力是错误的,那么美国强征我们到海外去暴力地保卫它也是错误的。反之,如果美国有理由强征我们并教会我们学会暴力地保卫她,那么你我就有理由不惜一切手段在这个国家里保卫自己的人民。”……“于是,他抹去了自己的姓氏——指出那不过是殖民者对祖先的奴役和强暴的记号,而将其悬置为未知数‘X’;同时,这开放的姓氏也昭示着‘我即你们,你们即我’的动员力量”。(刘烨,《六十年代的迟到者:黑人运动,美国的出走与带回》,2018.6.)另一位曾经署名“X”(恶克思)的中国艺术家廖国核常常将“政治正义”作为自己调侃和反讽的对象。2018年5月初,廖和我一同看了Arthur Jafa在GBE的新展,亦为其政治诗学的力量所震撼和吸引。这是廖第一次来美国,四个月后,他再次来到纽约,并在博而励画廊上东区空间举办了个展“烧女巫”。尽管画廊身处“隐秘”的中产阶级寓所,纽约艺术界对于这样一个小展览的关注度也极其有限,但看得出廖国核通过“精致”的量身定做,力图与美国当下政治、文化对话的欲望。廖国核说:“在权力系统运行过程中间碰到卡壳、某些矛盾解决不了或者需要达到某些目的制造恐慌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具体的人被抛出来,这样的个体就是‘女巫’。在西方宗教权力很发达的时候,经常会有指认‘女巫’然后残酷地把人活活烧死的事。这里面除了权力,还有愚蠢、狂热的情绪。在这个权力运行机制里,我们每个个体都有被系统抛出来,被当成‘女巫’焚烧的焦灼。”(顾虔凡,Artforum中文网采访)我不知道“女巫”这个灵感是否来自Jafa新展中的自画像摄影《玛丽亚·琼斯》(Mary Jones),但不难找到二者之间或明或暗、脆弱的联系。《玛丽亚·琼斯》最初是受历史学家Jonathan Ned Katz和 Tavia Nyongo的一次学术演讲《想象人妖》(Visualizing The Man-Monster)而创作的,其原型人物是19世纪30年代流落纽约街头的一个名叫Mary Jones的跨性别黑人性工作者和小偷,后来因偷盗白人的钱包而被捕。巧合的是,几乎与廖国核个展同时进行的GBE的放映项目“Shakedown”中,那些地下脱衣舞表演的同性恋女孩也最终被白人警察铐走,同样回应了“女巫”这个隐喻。廖虽然没有种族的意识,但展览所映射的权力结构——它也许是普遍的也许是中国特有的——和Arthur Jafa、Leilah Weinraub影像中的种族政治是一致的。
两年前,那部只有7分28秒的短片《爱是信息,信息是死亡》(Love is the Message,the Message is Death)推出后,一度风靡欧美艺术界,直到今天还在四处传播。影片通过黑人歌手Kanye West带有福音音乐色彩的歌《Ultralight Beam》将历史上黑人运动的经典事件、影像档案巧妙地串为一体。当然,真正具有煽动力的是体现在这些事件中的荣耀、暴力和渴望。在后来的一次聊天中,David Joselit提醒我,音乐是Arthur Jafa作品最重要的一个特质,也是我们进入其作品的一个重要的感知通道。两年后,Jafa推出了新作《Akingdoncomethas》,这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影像以黑人基督教信仰为核心展开,一如既往,其中穿插着美国黑人历史上的暴力事件和政治行动。和Jafa其他作品一样,这里没有清晰的叙事或文本线索,也没有纵深度可言,艺术家像是“编织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大网”,“从一个更加广义的、笼统的历史视角描述‘他’和‘他们’”,仿若“一股包罗万象的黑色巨浪”,直击我们内心深处的卑微、晦暗和麻木。(Chris Fite-Wassilak,Arthur Jafa: What We Don’t See, 2017)此时,所谓的“政治正确”反而变得次要,甚至已然被种族政治的原生力彻底摧毁。何况在很大程度上,“政治正确”原本就是一部分白人知识分子的一种政治诉求,对于更多黑人而言,他们并不希望或很警惕被诸如此类的政治话语限制。Jafa就说过:“黑人身份固然不可避免,可一旦说我是黑人,我就要受到约束,一方面,我断言我是黑人,因为我本来就是;但另一方面,我不希望其他人对黑人的行为作出狭隘的判断。”(Nell Frizzell)因此他抒情的表达并不仅仅是为权利辩护,或是为了获取某种平等,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诉诸一种远远高于世俗生活的启示和自由的灵魂。

此次新展开幕的第二天,GBE举行了Arthur Jafa的画册发布仪式,场地不大,但座无虚席,满眼望去,基本都是黑人,想必部分是来自画廊周边即其所在地Harlem的普通民众。另一位几乎同期在新美术馆举办个展的黑人艺术家John Akomfrah恰好也是Jafa的朋友,并为其画册贡献了专文。而且,两位艺术家在影像手法上也不乏相似之处,按Joselit的话说,Jafa现在的影像更接近Akomfrah早期的作品,比如《汉斯沃斯之歌》(Handsworth Songs,1986)。不过,在我看来,二者最大的区别是Akomfrah的影像中具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沉思和冷峻,而Jafa的影像更像是一种黑人政治波普。Akomfrah是一个政治行动者,与之合作的Black Audio Film Collective(成立于1982年的一个黑人艺术团体)和他都以犀利的政治调查和实验精神著称,此次展览的标题“帝国的符号”便取自Black Audio Film Collective的第一部同名影片,创作于1983年,其中黑人运动的历史档案和影像资料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叙事资源和想象空间。《马尔科姆·X的七首歌》(Seven Songs for Malcolm X,1993)是一部关于这位美国黑人运动领袖的实验传记,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片,和Akomfrah其他作品一样,其剪辑本身也带有一定的虚构色彩。也正是通过模糊虚构与纪实的边界,那些死去的档案满血复活,焕发出别样的生机和力量。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生前是Akomfrah的好友和战友,在其去世之前,Akomfrah创作了《未完成的对话》(The Unfinished Conversation,2012)。这部影像装置不仅是为了纪念霍尔,同时通过寻绎霍尔生活、思想和行动历程中的点滴及其背景,重建了一部革命的史诗。作品聚焦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就是霍尔政治和理论生活的黄金时代,与之相关的发生在1956年的苏联入侵匈牙利、第二次中东战争、英法以色列入侵埃及以及女权主义的兴起等事件。也许我们不应该将他的影像视为一件艺术作品,它更接近一部文化研究,或按霍尔的话说,它是一种对立于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及其霸权的“抗争的符码”。有别于Arthur Jafa的是,Akomfrah不再局限于20世纪的黑人运动,而是基于更加宽广的视野翻检历史、审视当下,比如在三频影像装置《眩晕之海》(Vertigo Sea,2015)中,他以海洋及其所象征的扩张性文明为基调,将生态环境的变化、奴隶制历史、移民文化、殖民文学等诸多不同但又息息相关的素材和议题有机地组织起来,编织成一部宏大的历史叙事和政治散文。且同时,就像在《未完成的对话》中Miles Davis的爵士乐被作为霍尔生命—政治历程的隐性线索一样,他总是将情绪压到一定的限度,更多是透过思辨和哲理的语言铺陈叙述。
写到这里,不能不提GBE及其所在的Harlem地区。记得两年前的秋天,我第一次来到纽约。飞机一落地,有朋友便提醒我纽约治安不好,特别是在黑人聚集地Harlem尤其要当心,后来一个美国朋友告知我纽约可能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并推荐了位于Harlem区的两个艺术空间,一个是工作室美术馆(The Studio Museum in Harlem),另一个就是GBE。前者是一家主要关注黑人艺术的非盈利艺术机构,目前正在装修扩建中,新空间将于2021年正式开放,一个小的临时空间目前设在位于127街的GBE隔壁。要说真正让我惊艳的还是GBE,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家老牌画廊,它的实力也许不如David Zwirner,Hauser & Wirth和Gagosian这样的超级画廊雄厚,但展览品质丝毫不逊于这些画廊,可贵的是它始终保持着前卫和实验的姿态和精神。也有人说,GBE之所以迁至相对偏僻的Harlem区,就是为了区别于更多平庸的空间。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但即便是“权宜之计”,也不能否认进驻Harlem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事件,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政治性,因为Harlem就是革命和抵抗的象征。在纽约的半年期间,我曾来这里看过四次展览,每一次展览都仿佛在制造一个政治的爆点。尽管今天的Harlem早已没有了冲突和暴力,看上去比唐人街还要井然有序,至少GBE所在的127街及其周边已然成了富人的居住区,但不可否认,Harlem历史上的抗争、冲突和暴力潜在地感染并滋养着GBE以及这里的艺术。
上世纪60年代,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当代艺术的转向其实是同构的,比如概念艺术的去物质化,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抵抗艺术的日趋商业化和市场化,特别是针对艺术市场对于越战的回馈。换句话说,去物质化本身就是反战运动的一部分。(Lucy R. Lippard,《六年:1966至1972年艺术的去物质化》)而作为文化研究的三大经典主题,种族、性别、阶级很多时候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共生、纠缠在一起。也是在此期间,经典的形式主义批评已经无法适应越来越多样的艺术媒介和语言,《十月》就是在这一特殊的背景下诞生的。Annette Michelson和Rosalind Krauss原本是Artforum的编辑和作者,两位都是法国理论在美国最早的引介者,当时适逢形式主义没落和政治性的弱化,他们所力主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恰好取而代之成了一个新的有效的理论入口。有一种说法是,当年Artforum主编拒绝发表Michelson推荐的福柯的《这不是一支烟斗》,她一气之下,和Krauss等人从中独立出来,创办了《十月》,并将福柯此文作为创刊号的主打文章。这当然只是起因之一,可以肯定的是,无论Michelson,还是Krauss,都一致认为当时的Artforum已经腐败了。在Michelson看来,一旦杂志商业化,就形同妓院,而她断然不可服务于一家妓院。这是她基本的立场。(Amy Newman,Challenging Art:Artforum,1962-1974,2000)这也是《十月》从不刊登任何商业广告(包括美术馆、画廊的展讯和海报)的原因,想必全世界没有几家艺术类杂志能做到如此纯粹。《十月》的基本理念是“艺术”、“理论”、“批评”和“政治”,但其核心还是“政治”(和“革命”)。这也是他们取名“October”的真正动因。我们无法概括四十年来《十月》刊发的所有文章,但至少通过两部十年文集,可以洞悉一二。1987年、1997年《十月》编辑部曾编过两本合集,是对两个十年的总结,不同时段,涉及不同的话题,比如“历史唯物主义”、“体制批判”、“精神分析”、“修辞学”及“身体”;“艺术/艺术史”、“后殖民话语”、“身体政治/精神分析”、“景观/体制批判”。自不待言,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美国艺术也正是聚焦于这些话语,其中,自然融汇了种族、阶级、性别等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在Hal Foster看来,正是种族、阶级和性别这些话题,开启了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评论的新视野。不过,《十月》虽说是政治性的,但他们从不愿意将其作为政治工具或政治武器,所以理论的带入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为了避免这一点。也因此,过于理论化一度成了《十月》备受诟病的原因之一。(David Carrier)但反过来,这也说明了Krauss、Bois等老一代学者为何不满今日艺术越来越被政治化而思辨性、智识性越来越弱的现状和趋势。
说到《十月》的政治性与激进性,无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十月》诞生所代表的转向无疑是革命性的,然而问题在于,每个时代的政治主题和激进性所指是不同的。比如在今天,我们所身处的是一个全新的政治时代,它完全不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和五六年前比,都判然有别。可《十月》自创刊以来,始终保持它固有的风格和节奏,甚至连编委都没有太大的改动,所以一度被批评为是一个封闭的小圈子。但对此,他们自己不以为然,就像Hal Foster所说的,他更愿意将《十月》看作一个乌托邦小部落,更重要在于,这里没有任何限制和约束,只有不断的煽动。如今,Krauss和Buchloh都已经78岁了,Bois也已经66岁了,但他们依然很活跃,也从未停止思考和写作。遗憾的是,这次调研访谈错过了Michelson,可以说,这位传奇女性和Krauss一道缔造了艺术批评的一个时代。9月21日,正在盖蒂基金会翻阅她的档案时得知她于四天前就去世了,终年97岁。她的离世是否意味着一个批评时代的结束尚不可断言,但对于《十月》而言,无异于失去了一个主心骨。这让我突然想到一个细节,十几天前在Krauss家里,看到她桌子上放着两本书,其中一本正是Michelson最近出版的一部文集《未来前夕:电影评论选》(On the Eve of the Future:Selected Writings on Film),而那时Michelson已近生命垂危之时,我猜想,也许Krauss是想再次触摸这些熟悉的文字,追忆她俩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斗友谊。

上世纪90年代初Douglas Crimp离开《十月》虽然谈不上是标志性事件,但似乎暗示着一些变化。杂志创刊没多久,在编辑第四期时应两位主编的邀请,Crimp加盟了编委会,并担任副编辑一职。差不多十五年的时间,整个杂志的编辑、运营主要由他和Krauss、Michelson三位负责。但激进的Crimp似乎并不满足于此,与此同时,他也在从事独立研究,并积极参与政治抗议和社会运动。1988年,October Books出版了他编著的文集《艾滋病:文化分析/文化行动主义》(AIDS: Cultural Analysis / Cultural Activism),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所有的争论聚焦在,艾滋病已经不再是医学的危机,也不再是社会和政治危机,而是一场深刻的意义危机。两年后,Crimp趁热打铁推出了新著《艾滋病演示文案》(AIDS Demo Graphics)。也是在这前后,他离开了《十月》。其实在此之前,《十月》就曾做过AIDS的专题(第43期,1987),然而Crimp持续的激进行动还是令两位主编略感不适,或者说这已经多少有所背离《十月》的理念和初衷,更何况照此下去,《十月》不是没有可能沦为AIDS运动的工具和武器。今天看,艾滋病的传染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早已成为全球性的灾难,它不仅事关公共卫生和医疗制度,同时还涉及性别、同性恋、社会歧视、精神分析、心理学、社会伦理、生命哲学等问题。可以理解,作为同性恋者的Crimp何以对之如此敏感和激进。不过说起《十月》,Crimp还是为之动容,对于两位主编既“感恩”又“怨恨”,毕竟《十月》陪他度过了最好的年华。值得一提的还有Craig Owens,他是Art in American的编辑,也是《十月》的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同性恋者。1990年,刚满40岁的他因为艾滋病去世。生前他曾经撰写过数篇关于性别、同性恋的文章,在罗切斯特大学教书期间,还为学生专门开过Visualizing AIDS的课程。(Craig Owens, Beyond Recognition: Representation, Power, and Culture)他显然没有Crimp那么激进,但二者的写作、实践和行动无疑都带着自己强烈的生命体验。就在Owens去世的第二年,艺术家David Wojnarowicz也因艾滋病去世了,年仅37岁。今年夏天,惠特尼美术馆举办了Wojnarowicz的大型回顾展“历史让我夜不能寐”(History Keeps Me Awake at Night)。与此同时,位于切尔西的P.P.O.W画廊也推出了他的个展。两个展览虽然并没有引起我太大的兴趣,但在现场我依然感受到了这位激进的酷儿艺术家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挣扎和不屈服。他曾经无拘无束自由地穿梭在纽约的大街小巷,通过绘画、摄影、录像、音乐等各种媒介,参与并见证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纽约最疯狂、最激进的艺术实验和社会运动。然而有一天,艾滋病危机突然闯入了他的生活,并先后夺走了他的爱人、摄影师Peter Hujar和他的生命。Hujar病逝后,Wojnarowicz的创作都是围绕AIDS展开的,并留下了大量带有强烈的生命温度和政治热情的作品。但在展览现场,真正触动我的不是他的绘画,也不是他的影像和音乐,而是他的摄影,特别是那组Hujar弥留之际的黑白照片。这样的语言的确有点煽情,但很多时候,煽情与残酷只在一线之隔,更何况,他从未放弃向一切偏见和歧视的抵抗和斗争。另外不得不提的是,也是这个夏天,PS1推出了伊朗裔美国戏剧导演Reza Abdoh的大型回顾展,这位出生于1963年的天才导演32岁就去世了,而且也是因为艾滋病。虽然我们已经无法体验他戏剧的现场,但透过这些视频档案,依然能感受他疯魔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他雄心勃勃的实验中,融合了童话、BDSM、脱口秀、视频艺术以及早期前卫戏剧等,毫无疑问,这些激进的实践足以反映当时纽约、洛杉矶地下俱乐部的生态和已然失控的艾滋病危机。今天,艾滋病毒依然在肆虐和蔓延,关于它的讨论和社会运动虽已成为日常政治的一部分,但这些展览的举行则将这一危机直接推到了我们的面前,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对它所关涉的性别、伦理及公共政治等问题。

诚然,《十月》越来越无法适应今天艺术和政治的剧烈变动。最初他们是要跟僵化的学院体制区分开来(Hal Foster),现如今,学院和图书馆却成了《十月》最主要的归宿。今年的夏季刊,《十月》发表了一篇Ted Nannicelli撰写的关于去年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的“世界剧场:1989年以来的艺术与中国”的文章《动物、伦理与艺术世界》(Animals, Ethics, and Art World),此文并不是关于展览本身的探讨,而是针对开幕前夕因为美国动物保护协会的抗议,迫使主办方不得不撤下涉及动物的三件参展作品这一事件的分析和评论。美术馆被迫撤下作品无疑是对艺术家言论自由的冒犯,长久以来,反伦理、去道德化也一直是艺术政治的一部分。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参与式艺术的兴起则重新提出了艺术与伦理的关系。何况,还有来势汹汹的左右两翼民粹主义在一边煽风点火。激进的古巴艺术家Tania Bruguera曾指出:Aesthetics(美学)这个词其实是由Art(艺术)和Ethics(伦理)二者组成的。但一直很欣赏Bruguera的Claire Bishop则提醒我们,通过诉诸伦理判断参与式项目的价值是困难的,这里的重心不在艺术和美学,而是艺术作品融入社会的过程中的情感强度,因此,其批评主要针对的是工作程序和意向性的伦理判断,可以说这是一种以生产为导向的艺术政治评论。(Claire Bishop,《人造地狱:参与式艺术与观看者政治学》,林宏涛译,台湾典藏家庭出版,2015)这意味着,Bishop真正推崇Bruguera的不是她对于美学和艺术的认知,而是她在实践中的情感强度以及所爆发的政治力。对一向激进的Bishop而言,平庸才是最致命的。Ted一文基本延续了Bishop的相关论点,重申了随着批评理论、政治和美学的转变,对于当代艺术运用动物的抱怨和批评不但不能被忽视,而且应该认真思考它所关涉的伦理和道德问题。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有人甚至吃惊于《十月》居然发表这样一篇文章,想必也是因为四十多年来《十月》极少发表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文章,还有人觉得讨论动物保护事件本身就很愚蠢。可问题在于,似乎唯有通过这样的讨论,才能真正参与和介入到今天的艺术现场,才能真正将中国与美国、与世界连接起来。对于杂志而言,唯此才能体现它激进的一面。所以,在问及《十月》是否越来越保守的时候,现任执行编辑Adam Lehner予以了坚决的否认,并以最新一期(第165期)为例,说:“我们花了大约200页来讨论如何处理冒犯性纪念碑的问题,还有50页来讨论‘非殖民化博物馆’,这难道还不政治吗?”
《十月》的编辑作者们自然瞧不上Jerry Saltz这样的网红批评,但也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当然,Saltz也不屑于这些知识精英。互联网改变了媒体生态,也造就了像Saltz这样的艺术评论,但真正的危机不仅是传统的纸媒还能不能生存下去,艺术写作也同样面临着挑战。在纽约,除了《十月》以外,还有Artforum,e-flux,Art in American,Frieze等这些媒体,包括定期免费发放的刊物Brooklyn Rail,它们关注点不同,写作风格也是各异,若论在艺术界的影响力,《十月》可能不如后面这些媒体。不过,《十月》的目的并非如此,他们原本无意即时参与现场,扮演一个激进行动者的角色,而是为了深入地展开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这些问题也许是历史的,也可能是朝向未来的。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是,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十月》的诞生与新的理论介入艺术批评和写作是一体的话,那么,今天艺术的变化要求知识方式也必须做出响应的调整,问题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这些理论还能适应今天的艺术吗?不消说,今天没有一个理论可以一统天下,没有哪一个媒体是绝对权威,也正因如此,催生了丰富多样的写作方式和讨论空间。在纽约,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讲座、研讨、放映和表演等活动。这里有上千家画廊,上百家美术馆和非盈利机构,它们分散在切尔西、中国城、Soho,上东区(包括中城区)以及布鲁克林、皇后区等地,每个区域、每个空间有着不同的调性和风格。在切尔西和上东区,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大师的“僵尸展”,真正生动、鲜活的则分散在中国城、Soho和布鲁克林的那些小画廊和非盈利机构。
当然,在纽约的半年里,我也好奇那么多画廊、展览和艺术家,到底有多少人在消费,那些中国城、布鲁克林的小画廊到底如何生存?可他们持续不断的开幕,足以表明还是有人在买单,而且很多时候,他们的展览规模虽然不大,但水准丝毫并不亚于切尔西的那些超级画廊。画廊的生存自然依赖于市场和商业,可那么多非盈利机构又是靠什么运营的呢?我曾经留意过The Kitchen的赞助,其中包括数家基金会、大量的画廊和个人(除了收藏家,还包括艺术家、评论家和策展人),且不论具体的赞助金额,至少从资金来源的结构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健康而强大的运营系统。比如Marian Goodman,自新世纪以来,一直是《十月》主要的赞助者。我想,也许只有在纽约这一资本大熔炉,才会滋养如此多的艺术家、美术馆、机构和画廊,它们像细菌一样,一方面寄生其间,另一方面又在啃噬着前者。
有人说,纽约不属于美国,纽约就是世界。纽约是唯一的,它是艺术的帝国,相信全世界没有一座城市能与之匹敌。然而,它也是一座毫无人性的城市,像一台24小时高速运转的超级机器,每个人都栖身于其中的各个角落。早在三十四年前,波德里亚就说过:“在对垂直性的技术癫狂中,在加速的平庸化中,在各个面孔幸福或不幸的生机中,在人类对于纯粹流通的献祭的傲慢中,整个城市(纽约)都在酝酿着自身终结的妄想。并将这一妄想审美地写入其疯狂中,写入其暴力的表现主义中”,它“旋转得如此迅猛,离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唯有宗教、种族、黑手党、隐秘或邪恶的社团和某些共谋者能继续生存下去”,唯有艺术、乞丐和那些癫狂者们才会真正享受这里的轰鸣、肮脏、拥堵和压迫。警笛声不时地划过曼哈顿的上空,像浪漫的乐章,却又弥漫着毒性和暴力。偶尔在街头会碰到秩序井然的游行队伍,但纽约终究是一个没有政治的城市,马尔科姆·K的幽灵似乎只能回荡在美术馆、画廊,和每一个共情革命者的内心深处。
文/ 鲁明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