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此文根据“全球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对谈整理而成。“全球语境下的当代艺术”作为《艺术论坛》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联合呈现的系列对话活动第二场,8月11日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报告厅举行。
自阿甘本关于“当代性”的讨论被翻译成中文以来,中国艺术界长期对“当代性”概念及定义抱有争论。在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许多当代艺术家的文化背景、身份变得多元。本次对话大卫·乔斯利特和帕梅拉·M·李教授基于此从多方面诠释20、21世纪的艺术史,讨论从杜尚“现成品艺术”的理念到20世纪中期影像艺术和新媒体激进主义,再到现今当代艺术在全球化和数字化双重压力下的发展与可能。
大卫·乔斯利特(David Joselit,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特聘教授)
1980年代起在波士顿当代美术馆担任策展人,参与并策划了多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展览。获哈佛大学艺术史博士学位,1995至2003年执教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艺术史系博士生项目;2003至2013年执教于耶鲁大学,并在2006至2009年期间担任艺术史系主任。他的新书《艺术之后》(After Art)于2012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帕梅拉·M·李(Pamela M. Lee,斯坦福大学珍妮特·海顿·琼斯与威廉姆·海顿·琼斯讲席教授)
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并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在纽约城市大学研究中心研究学习并参与惠特尼美术馆独立研究项目。研究领域主要为现当代艺术理论及评论。其文章发表在《艺术论坛》、《Grey Room》等多本重要艺术杂志。
帕梅拉·M·李:在我发言的最开始,我要特别感谢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也要特别感谢《艺术论坛》。我想先简短地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认识很长时间了,我想和大家谈谈我们认识的过程,我们在当代艺术中所做的工作,还想和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当代性”这个概念的历史。今天将是一个对话,在对话过程中我们会提出一些问题,甚至我们会有一些疑问邀请大家一起探讨,和大家谈谈当代艺术世界当中“当代性”所发挥的作用,这也就是今天所谈的背景,现在请我的同事大卫·乔斯利特进行发言。
大卫·乔斯利特:我特别感谢今天主办方,我非常高兴来到北京,非常高兴来参加今天下午的活动。像她说的那样,我们就此话题展开的对话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 我们之所以提到时间段的问题是因为,“当代”作为一个形容当下的形容词事实上已经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从1983开始作为当代艺术的策展人,我见证了当代艺术的几个不同版本,所以今天发言最开始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当代性在现代艺术史中的演变过程。
首先我想和大家谈的是几个阶段,或者说当代艺术的几个发展的历程,当然有些地方有历史跳跃性。我们很容易忘记的一点是奠定现代艺术一篇关键的文章,法国的著名的诗人、艺术评论家夏尔·波德莱尔的《现代生活的画家》(Le peintre de la vie moderne),他认为现代性是一种风格,而且是当下的变体,但其中有永恒性的元素。我想我们对于当代性进行探讨和其目前的表现形式中,很容易忘记当代性其实是现代性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进入今天讨论的话题之前,我们在最开始想问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想讨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讨论当代性的时候,现代性往往被我们暂时放在一边?”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重要,因为现代性代表着一个价值体系,是当代性急于压制的价值。第二个节点与我之前所提及的我在波士顿当代美术馆(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Boston)的工作有关,它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机构,于1930年成立,起初作为现代艺术机构,是纽约的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后来它的名字改为当代艺术机构。你可能很难相信,机构名称的更改在1940年代是颇具争议的。这似乎否认了当时现代艺术具有的先进性格,同时美术馆接受并展示了一系列商业化的艺术生产。实际上我们关于当代这个概念的讨论过程中很容易忘记一点:从一个历史演变的语境中来看,现代性和当代性有密切关联,在有些情况下两者还存在着一定对比的关系。
帕梅拉·M·李:我想对于大卫前面引用的夏尔·波德莱尔关于“时尚”的修辞一些补充。在艺术领域工作的人其实习惯性地认为时尚、“新”的事物是永远循环、不断变化的,并将其视为我们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刚刚大卫说到的一点我特别赞同,就是他提到自己职业生涯第一站,他曾经是一位策展人。其实我自己的经历也有很多类似之处,我曾经在一个画廊工作,叫Metro Pictures。当时纽约有一个地方叫SOHO,我们认为SOHO是当代艺术世界的策源地。所以这个地方是具有时尚性的场所,也因为这一点我们不仅开始了关于现代性和当代性相关关系的讨论,而且直接引出了后现代的讨论,即现代性、后现代性在当代语境中,这样一个新文化主宰的时代之下发生了怎样的演变。
可能大多数人对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理论文章非常熟悉。在这里我特别想跟大家强调的一点也是我认为依然非常有意义的一点:如果我们要把当代性从历史角度进行观察与界定,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 那篇著名的的关于后现代状况的文章非常相关。在这篇很长的文章反复提到一段话——我们在理解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之后我们将试图概念化当代性中的时间概念——他所提到的是“后现代性代表的是历史影响力的退化”。
就是说现在这种迫切感、纪实性、历史的时间性好像在后现代当中已经全都消失了。大家作为艺术家、评论家、策展人,或者,对于我们来说,艺术史学家,我们在1980年代讨论当代性时,人们对于这种历史性影响的退化是思考当代艺术时的重要因素。 这一点也把我们带入了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如何界定当代的时间段等一系列话题中。
大卫·乔斯利特:让我们回到詹明信的文章, 这是作为理解后现代性的基石著作之一, 帕梅拉也说过,早期当代的表现可以被称为后现代。我们对此观点的认同十分重要,因为,詹明信发明了一个词汇,“模仿作品”(Pastiche),它经常被负面地应用。这个词通常指一种伪历史,或者虚假的历史,有些东西看起来是古老的,但却可能是昨天新做的东西。在美国能看到一些看似中式的装饰, 但其实与中国完全无关。詹明信对于模仿作品的理论是使具有历史性的东西在当下得以重新演绎,并且服务于当下。像帕梅拉所说,詹明信觉得这是具有政治性的问题,因为对于他来说,历史是一系列具有政治及批判性的分析。同时这还意味着,历史是被当下激活的,并服务于当下的关注。 当代一直试图把历史带回到当下,通过不同方式,为了不同用途,这像是后现代一直在做的事情。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么为什么会排斥“现代”这个词?最终,“后现代”需要“现代”来证明自身的意义,就像我之前举的例子,大概在1970年之前,波士顿当代艺术机构的改名被认为是对现代声明的放弃。什么被放弃了?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现代艺术,理所当然的与现代化关联在一起,这种工业化的进程,城市化的进程,还有新的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等等,这些都是关于欧洲在19世纪发展的基本陈述。如果我们放弃了这种现代艺术,或者是艺术与现代化的关系,我们就放弃了那段历史。 同时这也是为什么当代显得十分具有诱惑性,我们丢失了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心位置,或者说,作为客观看待历史的终极角度。那么如果艺术不与现代化进程关联, 在当代的语境下,如果我们把所有时间等同来看,它们同时存在,那么就给了我们另外一种可能性来了解全球化。可能这种理解方式将不基于美国和欧洲之前发展而存在。
帕梅拉·M·李: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积极的方面,可以认为是一种当代性的普遍的概念,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必须要摆在桌面上,尤其是在我们共同研究和工作、尤其是作为艺术史和当代艺术批评家的工作当中,在我们把现代、后现代当作历史性既成事实(fait-de-complet)的概念放弃之前,我们要清楚,我们声明放弃了什么,抽离了什么?很多人应该都很熟悉这种当代艺术的时代化或者阶段化划分。在我个人看来,这是需要更加仔细审视的一个概念。即在整个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当中,比如说1989年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新自由主义革命展开,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的著作《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1989年同一时期的这一系列事件对于艺术市场还有艺术教育能够产生怎样的影响,实现了怎样的目的?这听起来可能是宽泛的理论和概括,但是就我任教20年期间认识的很多学生而言,这意味着在80年代、70年代、60年代,还有20世纪初所发生的事情不能作为当代性所保持的新奇与即时性。从一个教育的角度,人们会担心当我们放弃20世纪的概念,它将成为一种历史性的遗忘。这也似乎是很多后现代的哲学家、理论家在80年代所做预测的最后成真,他们当时并没有深刻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反思。
大卫·乔斯利特:我认同帕梅拉所说的当代作为一种类别(contemporary as a category),当代从泛指最近制造的东西,时下的产物,或者作为时下存在的形容词到一种风格,这其实是很离奇的。 这里我想给大家谈另外两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其中一个是我刚刚提到, 除了现代艺术往往与现代化有关,现代艺术同时还注重创新与原创性。所以如果你想做一个现代艺术品,你必须创作一个新的形式,或者是一种新的媒介。当代艺术的开放性,在其诸多问题的可能性中,它允许不将艺术作品的原创性作为其最重要的核心部分,也就是说这个作品不需要像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在巴黎, 或1965年在纽约创作的作品那样,是具有清晰明确形式的作品,而是在这件作品中表达在地情况与发明一种新的可在全球流通的语言变得同等重要。因为我觉得当代性只是人们试图适应新的艺术世界,尤其是在89年之后的时代的努力。所以从正面的角度来讲,当代艺术不再需要创新,从反面来看, 我们看到过去的现代性历史一直被人们线性地理解为一个事情接着另外一个事情发生,而当代能够让我们在时间性方面有循环性的、回馈式的、 错时的理解方式,可以看到整个世界中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进步与发展速度,并且给予不同世界一个排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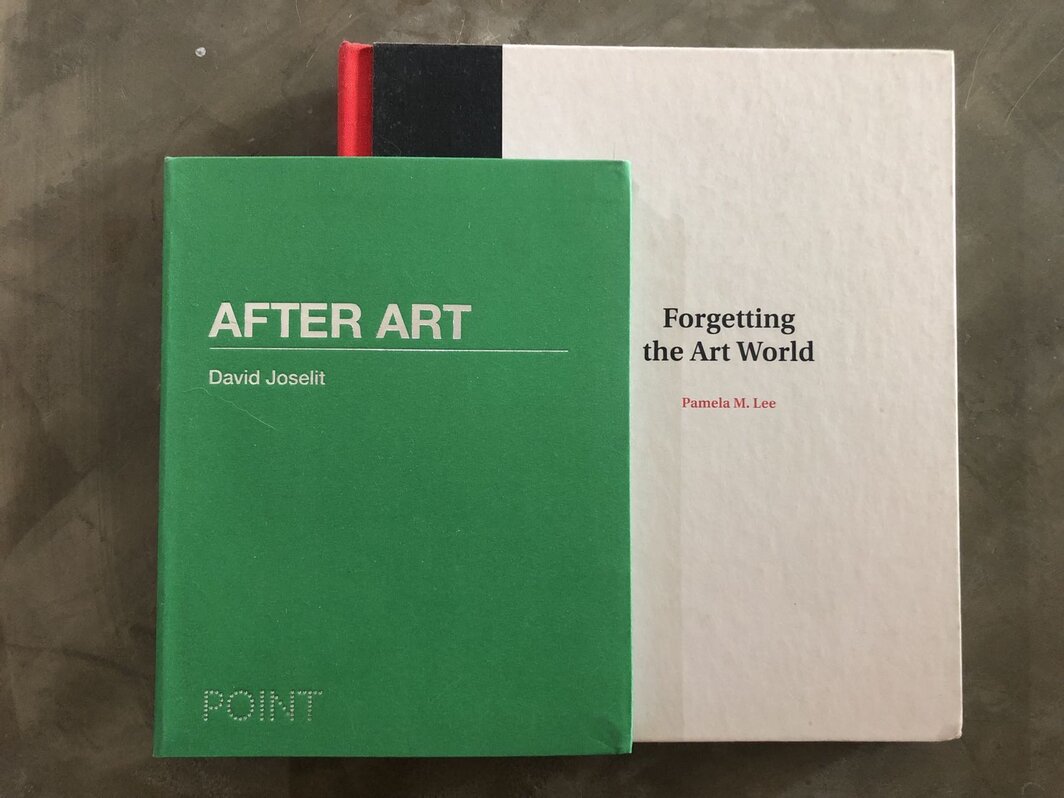
帕梅拉·M·李:我觉得这个不仅针对全球化的问题,这种当代性也反映了我们怎样对艺术作品进行分析的方法,还有艺术市场的发展和转变,所以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谈一下我们幻灯片当中放出的两张图片。
你刚才提到“当代”和“全球化”,如果这两个不是近义词的话,我们至少可以说这两个词是相互延续的,说到一个词就必须谈到另外一个,尤其是在过去几十年当中说到艺术,这两个词是连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和大卫在过去15到20年中一直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所有关于网络、回馈、反馈、回路式的艺术,以及艺术市场还有观众之间的关系,一直主导着全球化的话题,我的《忘记艺术世界》(Forgetting the Art World)是一种尝试,试图解决与分析这种问题。这本书也出于我对于当代艺术与全球化间某种叙述性的沮丧心情,或者说,用一个更恰当的词,全球主义(globalism)。全球主义代表了当代的阶段性风格,可能我们大家对于这些关于全球主义的图像,飞机、护照、机场、边境、迁移等等非常熟悉。
通过撰写这本书,我希望将艺术品本身视为全球化进程的产物和一种媒介。从实际操作的层面讲,我们将现代看似完整具有延续性的主题,线性前进,这包括艺术作品的创作,传播的形式,流通的途径。而我也曾经书写并研究过的1990年代艺术家的发展,探讨他们如何成为当今著名的全球当代艺术家。基于案例分析的方式,我希望能够对这个问题进行一定的回答,当然这里也有很多其他问题需要回答。
大卫·乔斯利特:我的这本书是《艺术之后》,谈这本书之前我想谈一下帕梅拉的《忘记艺术世界》, 我们需要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历史问题。刚刚她区分了全球主义,我理解为全球形态,其作为一种风格的流动性,以及对于世界上不同地方、或是对异国风情的观点;全球化则指历史条件下的全球经济。比如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地区的劳动分工,可能一个地区的工人赚的钱不太多,而他们的工作被由在别处的企业总部所操纵,而生产本身也是通过数字操控完成的,以及其他现象。
帕梅拉所指出的其实就是历史的功能, 给我们展示出的是文化现实的结构,而不是仅仅呈现它的面貌。我们讨论现代主义的重要意义在于其深深植根于历史,连同它附带的自身的问题。而且刚才我们还提到一点,这也是一种针对社会经济的环境分析。她刚才和大家谈到了各种具有全球生产能力的艺术家,他们在工作室中就使一系列全球化特有的力量得到了具体化实现,对此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帕梅拉·M·李:我想这颠覆了对于全球化的某种解读,它作为即将发生的生产模式, 艺术作品其实不仅是代表或者作为某种生产模式的缩影,而是很直接的内化了某些过程并且给予其推动。比如说,在一些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的特定类别中,大家可能听到一些有争议的词汇,比如后福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等等,一种混合语。那就一件艺术作品而言,它具体意味着什么,或者,艺术家如何运用此类的方式,不仅仅作为表征或反思,而是作为全球化的人工制品,艺术作品实现的急迫性,而非这些流程的风格注脚(stylistic remainder)。
大卫·乔斯利特:说到这一点,798艺术园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实这里就代表了艺术如何变成非常有效的投资方式,使得一个地区的经济得以发展并给予此地或这个国家一种身份认同。我这本书思考的问题是艺术如何作为一种权力与各种机构、制度的关系,比如说博物馆和全球市场的联系。英国的一位思想家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写了一本书 《后民主》(Post-democracy,2000),其中也谈论了全球化问题。他说全球性的企业除了品牌形象以外什么都可以外包。那么不管总部是在北京、纽约还是在其他地方,他们需要生产的只是自己的形象,自己的品牌,生产自己的企业和生产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新型企业来说,比如谷歌,品牌形象很重要,但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几乎是同样重要的。所以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知道艺术家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代表,在美国被我们经常称为创意阶层,比如设计师,等等, 他们是主要以商业形式或是艺术形式创造图像的人。这其实就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形象化范例。你当然可以说太过分了,这些人是进行艺术化创作的,怎么能走商业道路呢?但这也反映出艺术家在现实生活中有一定影响力,这种权力可以被以有趣和意想不到的方式利用,所以是这本书中我思考的一个话题。
还有一个话题我觉得也非常重要,而且这个话题不仅与信息数字化息息相关——数字化作为一种技术,也是一种隐喻,其关于内容如何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艺术媒介作为思考艺术的基本因素这一观念被取代了,我们看到的是一系列的“信息”, 从这些信息中艺术使我们看到内容(content)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
帕梅拉·M·李:从很多方面来讲,我特别赞同你刚刚说的这些。而且你刚才说到的一点是品牌形象,在这样一个全球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情况下,什么都可以外包,作为策展人、批评家,关于这一点我们一直在进行思考。具体来说,这种艺术作品的交换体制,使得当下发生的现象远远超出了我们学习和研究的范围。平面设计还有建筑系统都成了我们必修课,而且也要了解企业结构与沟通方式——所有全球化企业的范例都要有所了解。由于这些情况的出现,我们对于当代艺术的思考也要发生改变,也要涉及商标、LOGO或广告等现实生活中的因素。
大卫·乔斯利特:是的,我们致力于不断拓展当代艺术思考的主题范围。还是让我回到艺术史,从美国的视角来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艺术史家注重不同形式的视觉艺术作品,但这些作品没有作者署名(authored),也就是将艺术风格作为某种文化诊断。 在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中,一件艺术品本身成为了研究的单元。我们需要对这件作品进行解读,并与其他因素相关联。在我们两个的研究中希望建立一种研究方法,试图将作为网络运作的图像体系视为研究的对象,一件艺术品如何将其传播的体系包揽于一身, 如何将图像世界视为一种流通的世界,同时在这个背景下每一个图像都需要解读。
帕梅拉·M·李:对于艺术史,还有历史的阶段性,我们一会儿回过头来还会再谈。让我们谈谈形式,一种对当代艺术特殊的解读是由皮特·奥斯本(Peter Osborne)提出的。
大卫·乔斯利特: 我不想就他的看法进行太深入的评论,我只是想说,他提出了非常强有力的论断,即我们应当视当代艺术为“后观念艺术”。换言之,当代艺术是在观念艺术之后出现的,也就是在1960年代末,70年代初,主要是在欧美地区为主。在北京这么讲,让我看起来像是在发表一个地方性的欧美中心主义观点。同时,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观念艺术做的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在70年代观念艺术的情况,比较有意思的是艺术作品和信息之间出现的互动关系,两者被认为处于平等状态,艺术作品本身就是数据和信息的某种形式,而不是一种独特的图像形式。比如说观念艺术会使用文本、图像,其关注并非图像的美学化,而更加注重审视文字内容的语境和流通方式,这呼应了奥斯本说的一点,我们可以将艺术视为信息的理论化,就再次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一点:艺术不仅只是一种表征,不是任何事物的次生品,而是说艺术是全球化生产方式的结晶,艺术家成为了全球化生产者的范例,而且艺术作品给予我们一种信息的理论。所以在这些艺术作品当中,我们可以跟进这种流通方式,而且使用这种图像,通过建立档案等方式来建构艺术和信息的框架。通过艺术作品可以展示这种沟通的形式与图像的多维度意义。实际上这是一种理论的方式,令我们清楚这种数据在世界各地的流通方式。
帕梅拉·M·李:在这里我想做一个简短的补充。如果我们理解现代艺术理论做出的重要贡献,也就是艺术作品的自律性,对于客体的分析,在这里,这种分析归纳出了一种艺术作品在其中流通的系统。艺术作品的信息性,其实是一种媒介化的可读性,具备某种透明性,如果说一件艺术作品中包含了语言,那么它对于观众产生的影响,就会与它流通的系统产生相关性。

帕梅拉·M·李:我们来谈论一下时间性吧!为了不让下面的对话显得太抽象,我带来了一些图片与影像。就像我在最开始提到的,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观察各种艺术创作,尤其是近30年以来的艺术作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对于在各自工作中得出的结论达成了某种共识。
首先,我们认为当代是一种对于时间以及时间性的思辨。如果我们聚焦于“当代”这个词,那么我们必须要认同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现在所有在座的人都是与时间相关的,被完全整合入“当下”(present)之中。这与我们整个对话密切关联。刘秀怡之前建议我们可以提及阿甘本(Georgio Agenbem)的文本《什么是当代》(What is the Contemporary?)。就他的理论而言,在一个共同空间存在的人,共享当代性的人指的是那些处于时间之外,去同步或非同步的人。他们与时间之间存在某种距离,使得他们可以更好地看待与分析我们所处的这个看似透明,看似自然化的当下。
我们找了一些艺术品做例子,借此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探讨上述问题。鉴于现在UCCA正在展出的展览,我想从肯特里奇这件几年前曾参加过卡塞尔文献展的作品说起。
大卫·乔斯利特:对于这件作品我不会说太多细节,但想先简单探讨一下时间性的问题。假如我们在思考当代时,把它作为艺术全球化来思考的话,以刚刚提到的阿甘本的“时间之外”去看待我们自己文化之外的文化——也就是全球化语境下迫使我们选择的角度——那么我们一直都是处于时间之外的,我们不可能存在于一个整体的、历史的或统一的世界进程中。另外关于现在的时间有趣的一点在于,为什么当代是一个诱人的概念?这里面有一个时间的质感问题,与人类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即时的收发邮件,可以发微信且马上得到回复。我们在进行金融或贸易时,都是以毫秒单位来完成的,并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价值。还有新式的旅行方式,交通方式,还有更高效的获取信息的方式,这都是以前从来没有想到的。所以当代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概念,包括很多与时间相关的体验。这样能够让我们从非常小的不同差异中提取出一些抽象的时间概念和价值。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肯特里奇作品中的时间。这件作品是与美国学者彼得·格里森(Peter Galison)合作的产物,格里森是一位物理学家,主攻科学历史,做过大量关于爱因斯坦的研究。他关注的课题包括时间如何统一,以及时间的问题怎样推动高等物理的研究。我们可以在这件作品中看到时钟的时间,感觉有一个时钟在转。这是给我们展示在工业化时代,因为里面有一些机器,所以时间在此是与生产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像我们之前所讲的自然发生;还有里面的录像,快速闪过的图像,这是对于时间的截断,与这种时钟的时间属性是不同的,所以它展示了不同时间的形式。这件作品叠加了我们对于时间的不同理解:数字化的,机械化的,以及时钟的时间。
帕梅拉·M·李:时间的再现形式或表象形式可能是这件作品最主要的创造动机。它让我们看到,像时钟这样一种如此平常,如此规范性的机械装置怎样能为看不见的时间赋予形状。艺术家在装置中也有意把时钟的样式做得比较古旧。但这件作品最为打动我的一点在于,它让人看到了工业化进程如何建立在一种技术化的时间基础之上。 这让我想起某位哲学家说过的话:资本的形式而上学其实就是一种时间的技术。这也将工业时间或是福特式时间性并象征化了。
大卫·乔斯利特: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件作品展现了时间的统一其实只有在工业生产和火车运行时间表的建立过程中才能得到实现,因为我们很难统一和协调不同地方的时间。我们可以说时间是一种把不同地区的国际需求联系在一起后得出的结果。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会怎样?很难想象。在很多的地区,以农业为本的地区和国家很难把这种时间统一在一起, 因为他们不一定有这方面的需求。还有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工业化的劳动分工。比如说每天的工作时间都是常规化的,而不是取决于季节或者日照规律。这件作品让我们回到最初,把时间作为一项发明来看待。我们当前的电子化、数字化使得时间更加完善,比如我在纽约,却可以收到某人从其他地方发来的邮件。我们现在可以把不同地区的不同时间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不仅仅是像过去停留在一个时间地区。
帕梅拉·M·李: 谈到这一点,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件同样非常著名的作品:艺术家克里斯蒂安·马克雷(Christian Marclay)的《时钟》(The Clock,2010)。这件作品时长24小时,展示的也是24小时的时间。当它在纽约、伦敦、旧金山展出时,很多画廊和美术馆都举办了通宵观影活动,感觉有点儿像艺术界的睡衣派对,让大家一起观看马克雷了不起的剪辑成就。从我的角度来说,正是如此大量的剪辑工作令这件作品呈现出史诗状态。艺术家把很多电影中带有钟表的片段重组,将对这件作品的观看泛化与社会化,想想那些完整看了24小时的观众,肯定感觉像参与了一场派对一样。
大卫·乔斯利特:就像你说的,这是一件24小时的作品,屏幕上始终都有一个时钟在,上面显示的是实时的时间,也就是观众所处的展厅里的现实时间。这就把我们引回到当代里的时间性问题。当代的时间一方面其实是连贯的、连续的,就像你手机上显示的时间那样;但另外一方面也是非连续性的,一种虚构世界之间的蒙太奇。这件作品从一个镜头到下一个镜头,里面并不存在真实的叙事,因为它追踪的是时钟表盘,而不是情节或人物。所以,人们可以看到时间在片子里变得非叙事化,一方面被打破,一方面又保持连续。这件作品提出的就是一个时间的形式问题,时间在加速的同时也被打碎。你要不要谈谈这个作品的制作过程?
帕梅拉·M·李:关于制作我也没有太多要补充的,只有一点:这种对时间的蒙太奇剪辑方式与观众的实际时间体验之间的连续性很有意思。正因如此,这件作品才变得非常受欢迎。这件需要24小时看完的作品在无意之间——当然艺术家本人肯定考虑过这一点——反映了全球化当代艺术界的一种存在范式。不仅如此,它还提示出,今天的艺术体制及其时间性本身如何越来越跟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变得水乳交融。
除了《时钟》的放映以外,我们还能想到很多类似的展览,比如瑞士艺术家托马斯·赫赛豪恩(Thomas Hirshhorn)的作品《24小时福柯》(24 hours Foucault,2004)在巴黎东京宫展出时也是在通宵放映。观众可以在任何时间进入美术馆,随便从哪段看起都行。
大卫·乔斯利特:你刚刚提到的让我们想到关于当代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它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也跟数码化、跟24小时体验有关 。最近在美国国内艺术圈大家经常提起的一种说法是:人们欣赏艺术作品越来越多地是通过网络,而非实体展览。这一点不光适用于那些因为太远我们无法实际前去的展览,同样适用于那些跟我们在同一座城市的展览。很多人现在都首先选择通过画廊网站或其他网络平台观看作品。这一点极大地改变了艺术的创作及消费方式。目前有些艺术家被归类成“后网络”一代。“后网络”这个概念本身还有很多有待商榷的地方,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在讨论环节继续谈。不过上述现象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当代性的问题:作品到底是指其数码化的形式,还是实物化的形式,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形式,应该怎样展示?
帕梅拉·M·李:接下来的图片距离《时钟》的问题很远了。我们下面打算讨论的是历史性以及历史的不同版本问题。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图像来自于艾萨克·朱利安(Isaac Julien)今年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作品。我们很多同事似乎并不如你我这样能够认同这件作品,它事实上引起了很大争议。这是一次行为表演,展示的是《资本论》的朗读现场。艺术界很多人非常吃惊,甚至愤世嫉俗地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平庸的作品:“为什么有人在这个时代选择用马克思作为素材?”,并且用类似戏剧的形式制作。不用看,大家也能想象这件作品引发的批评意见,即,朱利安在创作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景观,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剧场,以最坏或者最平庸的方式迎合了当今艺术界的政治角力。其实我当时非常吃惊自己对这件作品的欣赏,因为我的确感觉到这件作品为急于冲向当代的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史学意义上的停顿。冲向当代是什么感觉,相信每个去看过大型展览的专业人士都有体验:你不得不看得很快,不得不走马观花,往往没有时间和空间去了解作品产生的大背景。尤其如果你是一名对美学与政治感兴趣的策展人,就不得不去想,把马克思的幽灵召回到这样一个最有名/最重要/最臭名昭著的当代艺术平台到底意味着什么。
大卫·乔斯利特:对帕梅拉关于这件作品内容及定位的意见,我表示完全赞同,但是我想接着谈谈它的形式。非常奇怪的一点是,朱利安使用时间的方法与马克雷其实有共通之处,虽然两件作品截然不同。展场里两个大屏幕基本上是实时讨论的记录,有点像演讲提纲,所以包含了某种教学性质在里面。而正如帕梅拉所说,朗读《资本论》这个行为是在展场中心区域进行。其中的形式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从头到尾通读一本书和24小时跟踪时间的流逝,两者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性。时间在此具备一种整体性,但面对这个整体,你只能时进时出。因此,这其中既包含了非持续、不定期的当代性,同时也让人体会到它背后还有某个你无法把握、无法抓住的整体。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出的是一种历史理论。虽然他做了很多实证研究,但他的理论具有一种高度抽象的形态,当然跟辩证法有关。所以,朱利安的这件作品虽然从内容来看,好像反映了在今天的艺术界里,政治如何沦为景观,但从形式上讲,它其实提出了一个关于时间持续的问题:长的持续和短的持续。另外,朗读行为的表演性质也很重要,我曾经用“资本的编舞法”来描述过这一点。因此,作品的重点不仅仅在于它的内容,而在于如何表演,如何表现,如何由个人或是机构表达给另一个。
帕梅拉·M·李:这正好引出了下面这件跟《阅读资本论》(DAS KAPITAL Oratorio,2015)完全相反的作品: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的《艺术家在场》(The Artist Is Present,2010)。这件作品以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表现了作为戏剧舞台的美术馆,作为娱乐或旅游的艺术这一概念,互动性在里面都成了娱乐。阿布拉维奇身着红裙坐在美术馆展厅中间,周围是空旷的场地,有一点像个拳击场,你可以选择坐到艺术家对面,跟她“遭遇”。艺术家的在场不仅指她个人的在场,也是一种艺术明星的代表。关于这件作品还有阿布拉莫维奇这个人物的性格表现,我比较关注的是所谓“艺术家在场”周围涉及到的美学维度。阿布拉莫维奇是明星,为了看这个明星艺术家的表演,你得排长队,跟你去演唱会或夜店的时候一样。你凝视的这位艺术家变成了某种化身,代表她身后作为娱乐场所的美术馆。
这就把我们引回到关于当代性的理解。在场感构成了当代性很重要的一个侧面。也就是说,艺术家本人坐你的对面,就像现在大卫和我之间的距离。这种在场感如何引发了我们对于当代艺术和当代性的思考?你距离这位编排了整个景观的女艺术家这么近,她给予你的这种现场实感(immediacy)其实也是人们期待当代艺术能够生产或给予的东西。另外,坐到艺术家对面的很多观众都会自拍,他们放到网上的海量照片和录像让“艺术家在场”这一形象的传播范围远远超出了MoMA本身。所以,“艺术家在场”这件作品的表演性中所包含的“现场感”,其产生了影响其实远远超出了现场本身。
大卫·乔斯利特:如果我们讨论的当代性指的是一种具体于当下的时间体验,那么阿布拉莫维奇的这件作品里其实汇聚了三种不同的时间度量尺度。第一种是完全没有经过中介的时间。就像《时钟》和《阅读资本论》一样,艺术家整个展览期间从头到尾都在那儿,她的在场提示的是一种现实的时间。而楼上展厅里,有很多表演者重现了她过去和搭档乌利一起做过的作品,同时展示的还有当时的记录照片。这就涉及到一种重现的时间,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模仿”的概念:把过去带入当下,使之成为当代的一部分。第三种涉及帕梅拉提到的自拍问题。除了观众拍摄的海量照片以外,整个表演馆方其实有现场录像。实际上,这场展览在网上传播得非常广,也引起了很大反响,不少人留言说被阿布拉莫维奇感动到落泪。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提出一种关于当代性的形式理论, 它一定涉及到几种不同时间度量尺度的共同存在:真实的时间、经过中介的时间,也许还包括重现的时间或者《时钟》所提示的虚构时间。

文/ 大卫·乔斯利特 (David Joselit),帕梅拉·M·李(Pamela M. 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