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BOOKS

被废除功能、成为历史文物及公共艺术的坦克,分分钟从它的基座上开下来,加入新的战争;正在展出着某一历史议题的博物馆,分分钟有难民涌入,成为避难所;金融危机或政体坍塌导致某一货币贬值时,当红艺术家的抽象画分分钟成为替代黄金,确保其拥有者维持着世界1%富豪的地位。这是希托·史特耶尔(Hito Steyerl)在其新书《免税艺术:行星内战时代的艺术》(Duty Free Art: Art in the Age of Planetary Civil War)中描绘的几个瞬间。这个行星上所有事物向其他任何事物宣告了战争,在由数码技术和算法治理倾情协力的真实和虚拟的战场上,最不可能做到的,就是分清同盟、敌人、战友,就像想象力丰富的中华未来主义也预言不到春晚小品里对中非关系的展望,其中由非洲人扮演的猴子,不知道与此刻蹦跶在恒温箱中的克隆猴有什么关系,然而或许是同一种高端理想,在五环外驱逐着它们的灵长同胞人类。
作者在全书多处论述了一股被她称为“代理政治”(proxy politics)的当代趋势,这也构成了作为艺术家的她长期致力于挖掘和演绎的“再现理论”(theories of representation)的最新章节。再现/代表政治(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在近几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以往,某个人群或事物得到越多的再现/代表,其图像在公共视野中越可见,就拥有越大的政治权力;而如今吊诡的是,“当图像以海量飘浮于空中时,精英们却在浓缩、集中权力。”可见性不再具有任何现实重量,暗箱操作前所未有地普遍。这让人想到各种直播和短视频平台的泛滥,边缘人群、法律擦边球、赤裸的社会问题,都通过娴熟的再现和自我再现套路,内耗在整体不被看见(或者说被看不见)的网络平台。
代理受委托代替某人某物出席、决策、做出行动。替身演员是一种代理,人在游戏和虚拟现实中的化身(avatar)是一种代理(但是当然,VR已经过时,今天我们都谈区块链),“翻墙”软件的运作是一种代理机制,而代理最广泛分布的案例,就是网络“水军”——一个个看起来和其他账号没什么两样的ID,你不知道它的背后是一个同时操作着十个屏幕、每日完成发帖数指标的带薪评论员,还是一个机器替身。当史特耶尔说“后再现/代表的政治是一场机器人军队互相厮杀的战争”时,她可能没有意识到“水军”这个中文词多么准确地概括了她的意思。“代理政治”或许该被翻为“水军政治”。
的确,社交网络上的战争愈发惨烈,从“炸号”这个最近频发现象的名称就能看出。网络监察员放弃了任何礼节和耐心,“一言不合”就删帖、禁言甚至炸号,没有预告也没有事后通知;除此之外,为了应对网友的语言智慧,他们的工作也从机械的敏感词检索演变成阅读分析,这就不仅仅需要软件和机器人,还需要无数支审查水军每天对社交网络用户发出的一切做出噪音(noise)和信号(signal)之间的辨别。“敏感”在这里也被赋予了一层新的意义:对信号足够敏感。
史特耶尔在书中多次提问:如何区分噪音与信号?她指出,更重要的是,对噪音和信号的区分往往制造了不可逆转的生存等级。由于我们永远无法完美精确地隔开噪音与信号,无论现实还是虚拟的战火中都有无辜者牺牲。当那些误伤牺牲了的,以及因为言论而被炸号的人去淘宝买了一个新的社交网络账号时,他们与负责制造噪音的水军、负责揪出信号的水军一样,成为这个局域网中不被(实名)认证的“次等生物”,厮杀在战争的前线。

如果我们追溯水军的生命政治,我们会发现他们往往是生活在发展中地区或第三世界国家的严重低薪、工作过度的廉价劳动力,这些新时代劳工并非内格里和哈特笔下构成诸众的那些未受社会规训、纯净而原始的“肉体”(flesh),而更像是一种“午餐肉”(spam)。史特耶尔如曾经漂亮地阐释了“坏图像”/垃圾图像(poor image)一样阐释了垃圾邮件(spam),“spam”的原意为“罐头肉/午餐肉”,一种深度工业化、商品化,被剁成糜又与无数化学添加剂混合在一起的人工肉,是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中被剥削的身体的真实写照,这些午餐肉/垃圾邮件不受欢迎,没有文化,具有欺骗性,但我们常常忘了ta们构成了我们邮箱、火锅和麻辣烫以及现实中大部分的空间。
“水军政治”在艺术界意味着什么?作者建议,是时候更新“体制批判这个二十世纪术语”了。她认为当代艺术建立在一种“在场经济”(economy of presense)之上,“放映后的问答环节比影片更重要,现场讲座比原文本更重要,认识艺术家本人比知道ta的作品更重要”,在这种生态中,在“疯狂的自我雇佣或者说自我失业”或者说自我剥削中,艺术家要想“罢工”是不可能的,你的暂时不在场只会使你的在场更加稀缺,抬高你的价值。这时,有效的抗议手段是雇佣水军/代理来代替你在场,代你参加放映问答、替你社交,这样,那些并非虔诚地想要理解你的艺术只不过是想见到你本人的观众,也能更自在地分配他们的注意力,来执行多重任务——大家都是数码劳工时代被过度使用的午餐肉。
另外,当代艺术本身是一种水军,它的出征制造了一种全球大同的假象——差异再剧烈、矛盾再尖锐的地区,它们的当代艺术的样貌总是相似的。艺术积极地参与着行星内战,“用黑话来掩饰洗钱勾当,还有后民主时代的庞氏骗局。”史特耶尔在多篇文章中把当代艺术行业的方方面面都黑了一遍,从展览媒体稿(“艺术界的垃圾邮件……与生殖器增大广告有得一拼”)到自贸区艺术仓库(“如果说双年展、艺博会、士绅化房地产的3D渲染、明星建筑师设计博物馆是这些地方的企业化表面,那么秘密美术馆就是它背后的暗网,通往[艺术品]销声匿迹的丝绸之路”),这些犀利的玩笑,从Art Review杂志“权力100”榜2017年排名第一的艺术家口中说出再恰当不过了。
作为“替代货币”的当代艺术,要谨慎继续成为各种“外围法西斯主义”(derivative fascisms)的帮凶。法西斯主义拒绝面对再现的复杂性,为了动员人群,它需要的是大量的套路化的图像。文首提到的“再现/代表政治”的图像通胀现象,与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是兼容的。在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力通过图像自我代表的时候,越来越少人的政治权利得到了代理。人民代表成为了人民水军——人民缺席了,替身上场;就像所有电影替身一样,他们是受过训练的,尤其是投票时。既然不知道何时可能被“炸号”的我们都是、或者正在成为水军,那么,作者认为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利用替身(或者被替身利用)去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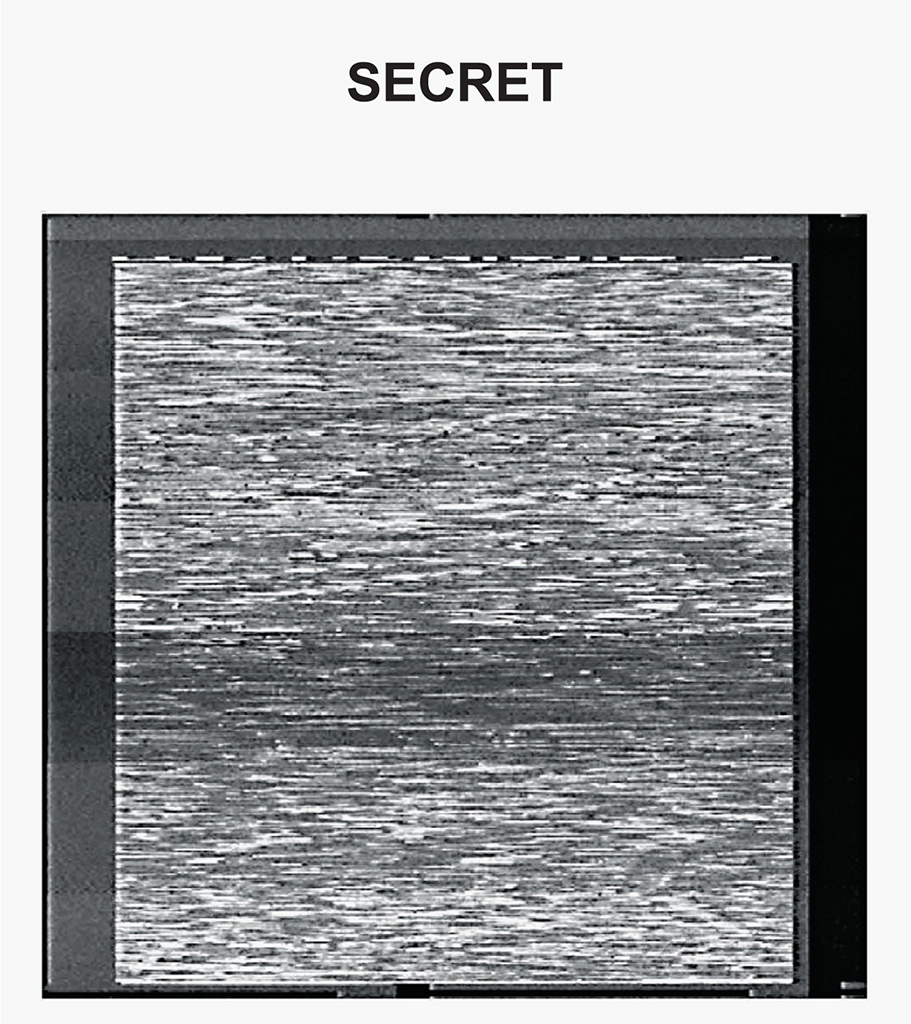
文/ 张涵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