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BOOKS

和谈话录中常被提及的知识分子一样,项飙也偏爱白话,相信“有水平的人应该用很小的词讲很深刻的道理”。贯穿于《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2020)全书的“距离感”一词即是最好的例子:作为能够引发人们的空间和位置想象的白话,“距离感”这个词堪称精确地反映了项飙对待研究的基本态度。
身为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著有《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2000,2018)、《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2010)等名作,发表了数十篇社会人类学领域内的论文和涉及各种公共议题的杂文,是一位勤奋的学者和知识分子。项飙成长于温州,求学于北大和牛津,但直到今天,他的身份认同仍然是温州人——与北大与牛津相比,温州处在政治和学术的边缘位置,这使他能够以乡绅为方法,更好地审视地方与中央、边缘与中心、小世界和大体制的关系。但是作为资深的田野工作者,他同时强调“距离感不是指对问题的关心程度、对事实的熟悉程度,这些不能有距离感,越近越好,要把自己融进去。但在分析的时候,要有登上山丘看平原的心态,才会比较客观、灵活、全面。”
“乡绅”是这本谈话录中最关键但也是争议最多的词。何谓乡绅?项飙解释道,“乡绅首先不喜欢现代知识分子”。紧接着他说,“我从小觉得自己成为职业上的知识分子是挺自然的,但我不太喜欢启蒙式的知识分子”。之于走过1980年代的中国知识人(项飙出生于1972年),这显然是个比较另类的声音。但或许我们要从中分辨一下项飙的“不喜欢”指的是什么。学者荣剑在题为《从启蒙知识分子到公共知识分子》(2019)的文章中如此定义启蒙知识分子:“1980年代是思想的年代,知识人的主要工作是思想启蒙,知识人可以称之为‘启蒙知识分子’,‘启蒙’是‘思想解放’的近义词。在‘启蒙’的旗帜下,知识界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不分左右,无问东西。”这个定义基本涵盖了知识分子可能持有的全部立场,如果项飙反对启蒙的知识本身,似乎就会把自己摆在一个反对思想解放的位置。但事实上,项飙反感的主要是启蒙作为一种风格在1980年代带来的集体性“迷幻”,而不是启蒙的内容。在他自己的用词中,启蒙的风格是特定的“声音”、“腔调”或者是“口气”。
其次,具有乡绅气质的研究者和调查员不太一样。前者的研究内在于田野(社会、群体、乡村等)之中,其所使用的语言基本上是在地的,“是行动者他们自己描述生活的语言”。其实对于项飙这样的人类学家,重点从来就不是研究的内在性与否,或是在地性与否,这毕竟只是个立场的问题,而是如何具体地把握自己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各种尺度,位置的、语言的、结构的等。谈话录这一形式能够很好地承载谈话者对立场的声明,却很难像专著或者论文那样跟踪和描绘那些处在持续变动中的尺度,这导致项飙的许多观点既清晰又模糊。清晰在于,作为立场,内在化、在地化是特别明确的方向;而作为路径,实现内在化、在地化,同时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感的具体路径却相对模糊。类似的例子还有“图景”这一概念或者说主张。在读到项飙的论文《作为图景的理论》(Theory as Vision),看到他在文中对梁漱溟、毛泽东两个人的农民理论的比较分析之前,谈话录中提到的“理论其实不是给出判断,而是给世界一个精确的图景,同时在背后透出未来可能的图景”听起来就像是漂亮的格言,尽管有一定的话语魅力,但在细节上过于模糊,因此只能被看作是一种立场,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推导后得出的较为确凿的结论。为了避免这种误解的发生,我们应该将《把自己作为方法》看作是理解项飙思想方法的索引,要依据谈话里所提出问题的框架,在他真正展开自身及其思想方法的实际著述中寻找更为确切的答案,否则书籍标题中的“自己”就会被局限在谈话录的界域中,造成理解上的错位。
第三,乡绅会做伦理判断,要在观察社会时判断某个现象的好坏。“但是乡绅和道德家也不一样,……他的伦理判断要和老百姓的实践理性对得上。”项飙坦承自己对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有一种亲近感,是“比较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式的民粹主义”。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在《什么是民粹主义?》(What Is Populism?, 2016)中写道,“民粹主义者……,他们的主张是道德化的,象征意义上的(而非基于事实经验的),所以不可能被证伪”。(《什么是民粹主义?》,第51页)但这显然并不是项飙所主张的民粹主义。
在《作为图景的理论》中,项飙认为梁漱溟和毛泽东对中国乡村社会都有深刻的理解,但两个人对中国20世纪初期的现状分析却存在根本差异。梁预测由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最终会走向失败,因为革命会以新的系统挑战农民数千年来赖以生计的社会秩序,但毛却相信农民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在项飙看来,梁漱溟的理解在历史上是正确的(historically correct),因为从历史上看,来自外部、尤其是国家层面的资源榨取和社会压迫的确要比阶级矛盾问题严重得多,贫农将地主或者是富农视为敌人并非特别常见的情况。与之相比,毛泽东对农民的理解则在民族志的意义上是精确的(ethnographically accurate):毛所强调的是贫农实际上想要什么,以及他们能做什么,而不是作为连贯系统的所谓传统是怎样的,而他的这种视角抓住了那个时刻最为重要的动力学(dynamics)。(以上概括参见:“Theory as Vision”,Anthropological Theory, pp.215-216)实际上,所谓“伦理判断要和老百姓的实践理性对得上”就是因为项飙在实际研究中期许了这种民族志意义上的精确性。如此看来,尽管项飙自认是民粹主义,但他的立场却要基于事实的经验,因而和一般意义上需要被特别警惕的民粹主义有一定的距离。当然即便如此,项飙仍然要面对米勒对民粹主义者们的诘问——“老百姓”/ 人民究竟是什么人?在学生时代完成了“浙江村”社会调查的项飙肯定知道,“老百姓的实践理性”的内涵很难被简单地概括出来,它所包含的复杂性会抗拒被概括。那么应该如何拿捏这个词的抽象程度,继而使得它最好地服务于研究就成为项飙始终要解决的难题,而这个难题的解决方法显然已经不是一本谈话录能回应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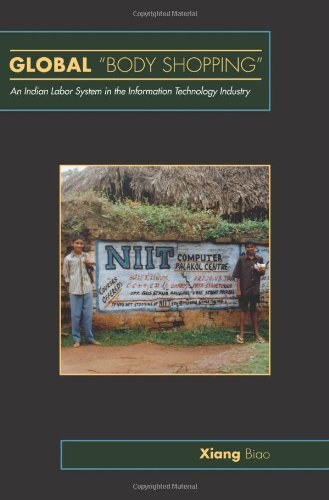
项飚在谈话录中的观点时常会给人一种自相矛盾的感觉。例如,他认为“距离感其实就是历史感。……应该(把事情)放在大的环境下给它一个合适的权重”,同时又觉得“如果太讲历史,可能会把一些矛盾给解释没了,所以有的时候强化一些片段,其实能够更加激发我们的思考”然而这里的“自相矛盾”却十分合理,因为它们是一些“要拥抱的事实”。“重要的是处理其中的矛盾,(思考)有没有理论或者方法让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会同时这么做”。作为半个同行,我深刻理解为什么项飙会展现出这种“自相矛盾”,因为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来说,很多问题领域并无绝对的标准。以距离感和历史感的关系为例,即使是在同一个研究中,所谓的距离也可能会摆荡于绝对的历史化和绝对的非历史化之间。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研究者充分调动自我的主体性,并实时调试自己的研究与历史的距离,反而有可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偏狭,而这也正是项飙所说的“距离感产生了精确性”的意义所在。
*除特别标记以外,本文中所有的引用均来自《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
文/ 胡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