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BOO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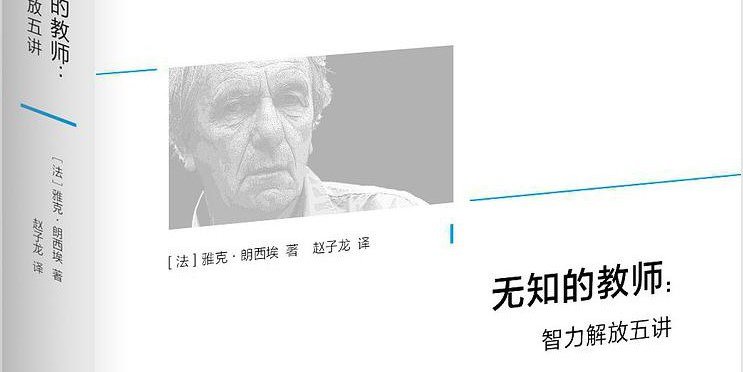
在法国思想家雅克·朗西埃看来,政治的任务如果是致力于人的解放,那么它的使命就更在于重新界定知识本身,在于给予被压迫者以自己发言的位置并聆听他们的声音,让过去那些不被当作话语的“噪音”真正被人听见和辨认。出于这种激进政治的考虑,朗西埃早年爬梳了巴黎公社时期劳工写的诸多随笔、诗歌和日记,以近乎“拼贴”的方式将它们呈现出来——这就是他著名的《劳工之夜》(Proletarian Nights)。
朗西埃在他一系列关于劳工文化的研究中指出,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希望恪守阶级身份的整合性和固定性,劳工们对于阶级界线和文化差异的漠视和跨越反而构成了颠覆性的因素。被压迫者不需要知识分子来宣布他们被压迫的事实——他们对此一清二楚;但也正是因此,向往中产阶级生活、向往布尔乔亚知识分子写作的劳动者,对于统治者就成了一种危险的社会存在,他们对既有生活的不满时时刻刻可能化作颠覆整个生产体系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朗西埃的“激进政治”所要批评的对象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知识再生产机制本身,不如说是曾经的一代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包括布迪厄和他的老师阿尔都塞。朗西埃认为,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对于体制的批判相当程度上不自觉地成了体制的帮凶,因为他们的整体论述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工人们处于受压迫的境地而不反抗是因为他们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蛊惑,而他们会受到蛊惑,根本原因是他们受压迫。在这样的论述结构中,劳动者永远也无法找到出路。而朗西埃的这本争议极大的《无知的教师》,也应放在他与左翼知识分子对话的语境中来看。这本书并不像它初看上去那样易读:诚然,如果把这本书当成一本教育指导手册,那么它的“实践意义”似乎非常明显:它似乎是一本鼓吹自学的教育手册。但确实如此吗?
这本书的“缘起”是一次颇有意味的教育实践:19世纪初,一位名为约瑟夫·雅科托(Joseph Jacotot)的教师到比利时鲁汶大学负责教授法语,由于不通学生的母语,他所做的全部教学努力就是让全班同学读一本双语对照的小说《忒勒马克》(Telemaque)。但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学生最终居然通过完全自学而习得了法语。朗西埃将这一教学实践与传统教师那种讲授语法、句型等等的“解释式”教学法相对照,认为雅科托这种完全以相信学生的智性能力平等为起点,不在智性上施加压力而只在意志上加以监督的教学法,可以称为具有解放意义的“普遍教育”。与此相反,传统的解释式教学法实际上做的是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强行划出一道智性能力的鸿沟,而能够填补这个鸿沟的只有教师的言语,也即只有教师能够判断学生是否掌握了教学要点、掌握了多少。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教育让教师强行介入学生和文本(教材)之间的直接关系,让教师在学生学习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扮演一种主导话语的角色。朗西埃指出:
教师的秘密是知道如何辨认教学材料与受指导的学生之间的距离,这距离同样也是学习和理解之间的距离。解释者本人建立这种距离,然后再负责拆除它——通过他话语的完整性来布置安排这种距离,然后再重新收编这种距离。
因此,在朗西埃看来,传统教师其实有意无意地混淆了“智性”与“意志”,并因此通过这种混淆而将自己的智性凌驾于学生之上。哪怕将来学生被认为“学会了”所有教学点,学生还是会默认自己与将来的教师之间存在着智性差异,并会主动将这种差异带入整个社会生活。就像福柯对于现代监狱制度的论述所示,学生在整个“解释式”教学法和教学体系的规训下最终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主体,也即自觉地将智性不平等和由此而来的一系列等级关系内在化:学生非但没有通过教育而在智性上获得发展,反而最终成为整个体系的不自觉的合谋者。就此而言,可以看到朗西埃在书中挑战的正是传统教学法的前提(而非方法论本身):“向某人解释某事,这首先就是向他表明他靠自己的能力无法理解该事。‘解释’的确是一种教学行为,但它首先是一个教学法的神话,是一则寓言:世界分成掌握知识的心智和无知的心智,分成成熟的心智和不成熟的心智,有能力的心智和无能的心智,聪明的和愚蠢的。”与之相对,朗西埃推崇的“普遍教育”实践所揭示的则是“所有句子,以及由此而言所有写下这些句子的心智,在天性上都是相同的。”智性平等是“普遍教育”揭示的至为重要、也最具解放性的一点。但让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这种实践——它构成了朗西埃整本书的“原初场景”。朗西埃在谈到学生如何通过《忒勒马克》学习法语时写道:
为了谈论《忒勒马克》,他们能够运用的只有《忒勒马克》这本书上的字句。要理解费内隆写下的这些句子并表达自己对于它们的理解,这些句子本身足矣。学习和理解是同一项“翻译”行为的两种不同表达。没有什么超出文本范围之外,除了一点,那就是表达(即翻译)的意愿。
在这段话里,朗西埃将学习和理解“翻译”为翻译行为的不同表达方式。这是一个多少让人感到惊讶的选择。他之所以使用这个词,是因为“翻译”在上述“普遍教育”的“原初场景”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如前所述,这一教学实践的目标是让不懂法语的学生学会法语,而他们唯一的教材就是一本双语对照的《忒勒马克》。从教学的文本材料到教学目的,“翻译”都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位置。由此可以看出,这一“原初场景”并未区分文本的“字面含义”的理解和对文本的阐释:学生或许通过这本教材学会了法语,并且知道这本小说的基本故事情节,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能够很好地对这个文本做出阐释;学会阅读古希腊文是一回事,能够阐释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另一回事。在这里,朗西埃似乎没有考虑任何对于文本阐释的品质差异;简言之,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对于“深度阐释模式”的摒弃,因为理解文本的字面意思和更加“深刻”的理解在“翻译”即“表达”自身对于文本的理解这一意义上并没有高下差别。
无论如何,朗西埃论述的真正重点是“表达的意愿”。这进一步和平等有关,因为“平等的方法首先是意志的方法。只要一个人愿意,他就能凭借自己本身的愿望或情境的约束来自学,不需要教师做解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朗西埃这本书包含的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智性平等是一个事实还是一个前提性假设?
朗西埃明确指出应该将它视为一个假设,并以此为基础来探讨既有的教育等级制度所遮蔽的方面:“我们的问题不是证明所有智性都是平等的,而是考察根据上述假设可以做些什么。为此,对我们而言,这项意见只要是‘可能的’就足够了——也就是,与之相反的真理亦无法得到证明。”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确乎能从文本中找到一些段落,在其中朗西埃试图证明:智性平等是可以确证的。根据他对“解放”的定义之一,解放是“每个人都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智性动物的天性;这是倒过来解读笛卡尔的论题。”换言之,不是人的思考规定了人的存在,而是人“存在”这一基本事实就决定了他是一个能够思考的存在者:“人并不因为说话而思考——这恰恰会将思考从属于既有的物质秩序。人思考是因为他存在。”如果人的存在这一基本事实就规定了人是思考的存在者,那么智性平等也必然如同人的存在本身一样确凿。在这种“自然状态”下,没有人能够号称自己在智性上优于他人,因为思考的条件(“存在”)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这是不是意味着智性平等因此是一个事实?有人或许会说,朗西埃在这里说的是每个人都有智性能力,但“智性平等”仍然是一个假设;人的存在固然规定了人是思考的存在者,但朗西埃并没有否认思考能力可能存在不平等。上述反驳在朗西埃的整个论述中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朗西埃看来“不平等”仅仅是出于对平等的恐惧的结果。为澄清这一点,让我们回到朗西埃对于“意愿”或“意志”的理解。

上文已经提到,传统教师的错误之一在于混淆了意志和智性。教师或许有权让学生的意志臣服于自己的意志,但却不能让学生的智性臣服于自己。朗西埃非常明确地指出:“人是由智性支撑的意志。”但接下去他马上对此做了限定:“说意志的要求是不平等,这可能足以解释在专注方面的差异,而专注方面的差异则可能足以解释智性表现上的不平等。”此处我们需要确切理解朗西埃一些概念语词的意义,包括“意志”、“专注”和“智性”——这些概念均在书中得到了特定的界定,望文生义地理解恐怕会造成相当程度的误读。
首先,“意志”或“意愿”指人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而进行自我反思或自我尊重;更进一步,“意志”是“理性的门槛,是自我作为理性存在者的意识和尊严”,正是人的“意志”培育了智性活动:“理性存在者首先是一个知道自身力量、并且不在这一点上自我欺骗的存在者。”可以说,由于“存在”的基本事实规定了人作为思考的动物,所有人在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一个理性而有能力思考的存在者这一事实。
其次,“专注”指的行为是“让智性的行进遵循意志的绝对约束”。因此,专注就是一个对于自身的思考能力有着自我意识的人凭借意志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规范。那么专注上的差异(或不平等)来自哪里呢?朗西埃对此给出的答案是所谓“不平等的激情”:
不平等不是任何事情的结果;它是一种原初激情。或更准确地说,不平等的成因只有一个,就是平等。不平等的激情出于对平等的晕眩,在平等所需的无限使命面前感到懈怠,在面对理性存在者理应做的本分时感到恐惧。
事实上,正是“不平等的非理性”,也就是不平等的社会本身,使得社会中的个体“放弃自身,放弃其本质中那无以度量的非物质性”——个体的不专注和分心来自于他进入社会之时。在这个意义上,不平等与其说是天生注定的“原罪”,不如说是抛向个体的一个选择,因为——
人们必须选择赋予真实的个体以理性还是赋予他们的虚构整体以理性。人们必须在“从平等者之间建立一个不平等社会”和“从不平等者之间建立一个平等社会”之间做出选择。任何倾向于平等的人都不应该犹豫:个体是真实的存在者而社会是一个虚构。平等只对真实的存在者有价值,而不是对一个虚构。人们只需认识到如何在一个不平等社会做到彼此平等,这就是解放的意义。
但困难恰恰在于上述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是平等者的不平等社会,要么是不平等者的“平等”社会),因为朗西埃同时告诉我们,“智性”——作为“平等”的对象或内容——暗示着一种互惠性:智性的力量“让人通过他人的确证而被理解。只有一个平等的人理解另一个平等的人”。于是我们得到了“平等”和“智性”之间、“理性”和“意志”之间的等值性。从此可以推出什么?答案或许令人惊讶:“社会”本身的可能性建基于此。朗西埃写道:“上述同义不仅是人的智性能力的基础,而且一般而言是社会得以可能的基础。智性平等是人的共同纽带,是社会得以存在的充要条件。”这里的矛盾显而易见:一方面个体作为思考的存在者一旦进入社会就会被“不平等的激情”所异化——由此也解释了“专注”方面的差异,并解释了智性的差异——另一方面,朗西埃又主张智性平等是社会的纽带。为了确证(平等的)他人,为了理解他人所表达的内容,就必须预设智性平等。朗西埃将这一智性平等归为“人”的特征而非“公民”的特征——他说:“只有人之间才有平等,也就是说,将彼此仅仅视为理性存在者的个体之间才有平等。与此相反,公民作为政治虚构中的居民,是陷入不平等泥淖的人。”然而,难道不是政制本身规定了公民的特定生活方式,而后者又规定了人们相互理解的可能性条件?或许可以强调说,朗西埃批评社会不平等时往往用的字眼是“社会秩序”而非一般而言的“社会”。但归根结底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除了无政府状态之外还能是什么呢?更合适的解释方式是把朗西埃笔下的“社会秩序”翻译为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性体制甚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将他的“社会”翻译为平等者的自由结合。即便如此(或正因如此),一个难题仍然得不到回答:纯粹意义上的“社会性”以智性平等为基础哪怕是可能的(或至少不是不可思议的),它仍然未能摆脱“特定生活方式”的难题。正如共和主义者对于罗尔斯设计的“无知之幕”提出的质疑那样,“善好”、“理解”,甚至“表达”,这些概念在投入政治共同体运作中时都不能够剥离具体政制赋予它们的意义和形式。抽象地讨论“智性平等”的前提,正如抽象地讨论“无知之幕”下人的理性算计那样,是一个颇成问题的思想实验。
不过,朗西埃毕竟不是罗尔斯那种致力于设想公平正义的政治组织的思想家,“普遍教育”也不是“无知之幕”那样的认识装置,因为前者根本上就是反一切体制的:“被解放者无疑尊重社会秩序。无论如何,他们知道这总比无序好。他们的认可也到此为止了,但没有体制会满足于此。”这也就是为什么“普遍教育”不是一种实用的教学方式;毋宁说,它更是一种解放的宣告——不仅要将人们从传统教育的“解释式”教学法以及它所建构的一整套等级秩序中解放出来,而且要将人们从社会中解放出来——如今被解放者“知道他对社会秩序所能期待的是什么,并且不会拿它太当回事”。撇开朗西埃论述中蕴含的政治代价不谈,就人从社会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而言,这一过程中包含另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即传统教师的教学法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解释式”教学法是社会权力的代表或典型体现,抑或是福柯意义上的知识型(episteme)?事实上,朗西埃多次提及,社会秩序预设了传统教育的解释模式;但要论证这一模式就是社会的权力模式或统治模式,仅仅在类比的意义上进行讨论远远不够。认为启蒙哲学所提倡的教育观念制造了人们(在教育中)的智性不平等是一回事,而认为这一观念构成了不同社会机制得以组织成型的范式,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朗西埃提出的近乎二元对立的设想——要么是由智性不平等构成的社会秩序,要么是从智性平等出发的“社会性”——并没有为类似“知识型”的考古学式考察留下空间;或者说,朗西埃给出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排除了历史性考量。
如果我们可以将朗西埃这本书视为对“普遍教育”的宣告,一次言语行为意义上的实践,那么它的对象就是知识分子。似乎是知识分子而不是“人民群众”——正如朗西埃在书中提到的农民父亲教儿子学习阅读的故事所示,后者已经在(不自觉地)践行以智性平等为出发点的“普遍教育”——深陷下述幻觉而不能自拔: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智性上的差距。如朗西埃所说,“为了解放他人,人必须自我解放。”可归根结底,为什么知识分子会有这种幻觉?
一个可能的回答是:正是知识分子认为智性上的差异是重要的,比如一位哲学系教授会认为自己对《理想国》的解释与一位未经过训练的社会读者对该书的理解的差异不仅是“意见”不同,更具有品质上的差异。朗西埃反复强调,“普遍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天才”,而是消除人们的自卑:“问题不是培养学者,而是让那些相信自己在智性上低人一等的人抬起头来,离开使他们停滞不前的泥潭——不是无知的泥潭,而是自卑的泥潭。”朗西埃谈到,“‘天才’真正的谦逊之处”(“天才”在此指的是那些将智性平等作为出发点的艺术家)在于运用自身的能力向人们表明他们和他自己一样拥有平等智性以理解他的艺术作品。这些话听起来很鼓舞人心,但“智性平等”带来的解放并不意味着观众能够和艺术家一样创造出同样的艺术品。似乎一种“等级”悄悄地重新从后门溜了进来:艺术家不仅知道人们的智性平等,而且能够创造他人所无法创造出的艺术品。无论这意味着什么,至少可以说,在“天才”和观众之间确乎存在某些重要的差异,某些关乎品质的差异。对此,一个朗西埃式的回答可以是:“解放”的人民并不否认艺术标准本身,他们强调的只是人们都具有平等的智性,以此为起点根据各人不同兴趣在各个领域进行钻研,没有谁比谁更高贵,仅此而已。按照朗西埃的说法,“我也是个画家!”的意思是:“我也一样拥有灵魂,我也有感情要与我的同伴们交流。普遍教育的方法与其道德教诲相同。”但我们所处的消费社会,难道不恰恰奉行了这一前提?政治、哲学、宗教等等都变成了可供消费的符号,更不用说人人都可以就当代艺术高谈阔论一番了。坚持艺术的高贵性和艺术家的智性优越,在当下社会难道不恰恰已被视为另类的言论甚或当作笑谈?至于对《理想国》的解释,除了学院里不同解释路数彼此对峙之外,在社会读者中多少人会较真呢?对文本的理解差异无关深度,对各个领域的钻研只是由于人各有志,所有差别都可以化约为草莓口味冰淇淋和巧克力口味冰淇淋的差别——这难道不正是当下社会的文化政治现实?可另一方面,我们其实自觉不自觉地仍然尊重品质的差异,譬如当我们写出一篇关于《理想国》的论文,我们会更在乎教授怎么评价它,而不是门口摆摊卖水果的小贩的看法。我们在惶恐地将论文递交给教授的时候,有没有预设“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智性鸿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真的愿意放弃这个前提吗?或者说,我们倘若不愿意放弃,这是出于“不平等的激情”或对于平等的恐惧吗?
本文引用文字均为作者从1991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译本中的摘录翻译。
文/ 王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