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BOOKS

千叶雅也,《当代思想入门》(『現代思想入門』),讲谈社,2022,目前尚无中译本。
在当今日本学界以德勒兹研究而闻名的千叶雅也(Chiba Masaya),继出版了一系列“轻度哲学随笔”类型的著作以及一部散文集和一部长篇小说之后,今年又在“讲谈社当代新书”系列出版了一本文类上或许属于“传统学院派”著作的小书,即《当代思想入门》。这部面向一般读者介绍二十世纪法国理论的入门类书籍,出版两个月便已二次印刷,并在各类书籍热销榜上名列前茅,甚至出现在了地铁车厢的广告中。当然,这次多少令人有些意外的畅销并不意味着如今日本的普通读者对于所谓“当代思想”或“法国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毕竟“买畅销书”和“读书”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而将一本书从一开始就包装为“畅销书”,则更多关系到出版社和书店的营销策略。
但无论如何,千叶雅也无疑是抱着向大多数没有接触过法国理论的读者进行“科普”的目的而写作这本书的——他甚至将自己的这本“入门”著作称作“为了[其他]入门而准备的入门”,“为了[其他]入门书而准备的入门书”。这一自我定位也就解释了整本书在写作方式上采取的策略,即并不着眼于完整而系统地介绍书中出现的思想家,而是以明快和朴实的语言将几位思想家的核心论述和方法重新整理和提炼,以便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最基础的思想准备,让他们由此契机而开始阅读其他介绍性的书籍、乃至阅读原著。擅长“轻度哲学随笔”写作的千叶雅也,甚至在全书最后的附录部分以“手把手”的方式向读者示范了面对晦涩、修辞繁复的理论著作,应该采取何种阅读策略。确实,在针对几段德勒兹和德里达的原文的讲解和改写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作者对于讨论对象的周到理解。
然而,说到一般性地介绍二十世纪法国理论,坊间已有的著作可谓数量繁多。除了中国读者非常熟悉、在日本也得到译介的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以及卡勒的《文学理论》,就日本的语境而言,从1980年代浅田彰等“新学院派”知识分子对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详细介绍,到2000年代初内田树等评论家面向一般读者撰写的法国思想入门,可以被称作“当代思想入门”的著作也已不胜枚举。更一般地说,尽管千叶将这本书命名为“当代思想入门”,但书中主要介绍的思想家——千叶重点探讨了三位“后结构主义者”,即德里达、德勒兹、福柯,并从其思想资源和问题意识的角度,又分别引出了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拉康等人,最后作为对“后结构主义”的继承性批判介绍了马勒布和梅亚苏——在单纯的年代意义上,大部分或许已经很难被算作“当代”。读者可能会萌生一个非常简单的质疑:在2022年以“为了入门书而准备的入门书”的方式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思想,还能算“当代”吗?对于这一点,千叶自己在“后记”中如此写道:
当代思想已经是“二十世纪的遗产”,正在变得像传统技艺一般,有必要继承其阅读方法。现在意识到的这些事情,过去想都没想过。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当代思想确实是“当代”的,而自己想要成为“当代思想”的开拓前沿的研究者,在当时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中略)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本书与其说是作为专家而写的著作,不如说或许是一个从十几岁开始就憧憬法国当代思想、出发点是想要酷炫地用上“块茎”“解构”等说法的“当代思想粉丝”的总决算。它是青春的总括,是憧憬的尾声。
换句话说,作者从学生时代的憧憬出发而形成和积累的对于法国思想的“某种阅读方式”,构成了这本书的基调和背景。一方面是早已被学院化、正统化乃至“传统技艺”化的“当代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思想的“当代性”逐渐变得可疑),另一方面则是作者所坚持的这些“当代思想”的普遍性和“当下性”——于是,我们似乎不得不吊诡地说:在当代,我们仍然有必要阅读“当代思想”。千叶承认,这是一个“矛盾”。在我看来,这个并不复杂的“矛盾”在整本书中也或多或少形成一种推动力(甚至一种写作上的焦虑),使得作者始终想要从德里达、德勒兹等人的论述中提炼出某些“直至当下”的、与一般读者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人生教诲”。(这本书腰封上的宣传语便是:“人生得以改变的哲学”。)
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这本书的一大特征是:聚焦不同思想家之间共通的思考方式,将针对不同对象的论述化约和抽象为一种方法论上的操作。例如,在总论“当代思想”的性质的部分,千叶写道:
事物是通过所谓“暂时固定的”同一性与偏差和变化等的混合而展开的,而这种暂时固定的同一性和差异之间的律动往复,便是当代思想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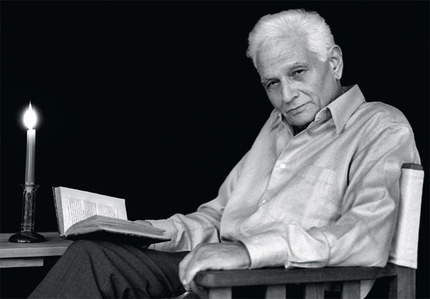
通过这些抽象度极高的范畴,不同理论家的讨论对象——如德里达的“书写”、德勒兹的“差异”、福柯的“权力”等等——得以被统摄到一种共通的思考方式乃至论述方式下。在千叶看来,就“当代思想”特有的思考方式而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德里达,后者批判性探讨的“二元对立”和对诸多对立结构的“解构”,形成了“当代思想”的基本语法。千叶对“解构”的操作步骤进行了如下概括:
①首先,在二元对立中,质疑默认将一方作为弱势的价值观,从弱势方出发思考别样的逻辑。但不是单单将二元对立予以倒转。②描绘出对立项相互依存、没有哪一方占据主导、胜负予以保留的状态。③这时候,也可以运用第三个概念——它既非强势也非弱势,承担着二元对立的“不可决定性”的职能。
对于熟悉法国理论的读者而言,千叶的这番概括恐怕早已不新鲜。我们甚至不得不说,当年遭到批判性考察的种种二元对立结构,支撑它们运作和传播的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诸方面的可能性条件,也早已发生了众多不可忽略的变化。面对这些变化,如果我们仍然单纯从字面上理解乃至接受德里达的许多具有“当下”意义的分析和批评,结果很可能是表演了一场技巧上高难度的“大战风车”。不过,千叶在凝练地勾勒了“解构”的操作步骤或方法之后,既没有进一步引申到“解构”作为方法在其他领域(如文学或建筑学)的诸多运用,也没有试图探讨德里达思想的历史背景(也许作者可以说,这些都不属于入门书的范畴),而是得出了一个“人生哲学”式的结论:
在我看来,应该认为他们(指德里达和列维纳斯——引者注)的思想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即“人原本就是这样的:就算没人跟他们说什么,他们也会行动”。人只要活着,就不得不在广义上具有暴力性质,纯粹非暴力的生活是不可能的,这是毋须多言的前提。正因如此——我认为这是容易招致误解的一点——在这个毋须多言的前提上,如何将“他者”的伦理编织进去,便成了问题所在。
如果说上面这一结论对普通读者的日常生活还不能起到具体的指导性作用,那么让我们看一下千叶在讨论了德勒兹和福柯后的下面两个“结论”:
重要的是如何维持一种非常困难的安排,即从这种价值观之争中抽离=游离开来,但也彼此关心,同时这种关心又不成为对他者的管制。
不要太拘泥于内面,而是从物质上与自己发生关联的同时,将这种关联作为对大规模生命政治的抵抗。(中略)这是新的世俗生活,也是一种[独特的]世俗性的自由,即享受日常生活非常及物的、但又不过度的个人秩序安排,并以此为本位,即便有时逾出社会规范,也能以“这就是自己的人生”的态度泰然处之。
在千叶看来,上述两个“结论”分别是从德勒兹的“差异哲学”和福柯晚期的“伦理思想”引出的教诲。重复一遍: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千叶是否正确解读了德里达、福柯等人的思想,而是他感到有必要以非常直接和显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些“当代思想家”的的确确和读者们的当下生活发生着关联。然而,吊诡的是,一旦我们需要发明乃至“脑补”出德里达和福柯的“当代性”,以至于有必要将他们的理论还原为一系列“人生建议”,我们似乎已经距离这些思想家在自身著作中聚焦的具体问题很远了。
在整本书的结论部分,千叶为读者准备了一份“当代思想操作手册”式的提纲(顺便一说,就像诸多“轻度哲学著作”中常见的那样,本书中充满了各种“小结”和“归纳”,仿佛生怕读者在读了两页后就跟丢了论述的要旨),并在其中为“如何创造当代思想”指明了方向。具体而言,千叶提出了“他者性原则”、“超越论性的原则”、“极端化原则”、“反常识原则”这四条原则。这里仅举“他者性原则”为例:
他者性原则:基本而言,当代思想中新的任务登场的时候,首先就是发现:在当时的时间点上,作为前提的以前时代的思想、先行的宏大理论或体系中,某些东西的他者性遭到了排除或遗漏。
的确,无论是德里达的“书写”、福柯的“疯狂”还是德勒兹的“差异”,都是上述“他者性原则”所强调的提前遭到排除或压抑的一方。而且,千叶以梅亚苏等晚近思想家为例表明,在德里达等人之后创造出新的“当代思想”,似乎确实可以依照上述方式展开。不过,如果将“当代思想”化约为这些步骤和策略,那么不得不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今在SNS上泛滥的各种“仇恨话语”,不仅可以成为“当代思想”的批判性分析对象,而且本身也恰恰符合“当代思想”的基本策略和语法,不是吗?操弄着各种“你也一样”式的修辞、擅长比烂大法(whataboutism)的人们未必读过德里达或福柯,但千叶由后者的思想中提炼的诸多操作原则,事实上早已潜移默化地成为当代社会话语乱象的一部分,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基本氛围。如柄谷行人和浅田彰在1983年的一次讨论中指出的那样,法国理论家们在对一系列二元对立和形而上学传统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对他们的批判对象抱持着极大的严肃态度甚或敬意;而这样的严肃态度,早已让位给了反讽和虚无主义。
但这并不是说——如许多保守主义者或自称的保守主义者所反复论述的那样——二十世纪法国理论(或引介这些理论的日本“新学院派”)是导致当今话语乱象的罪魁祸首;毋宁说,我们恰恰需要重新审视的是千叶这本书症候性地向我们展现的、“当代思想”的当代困境:一方面,产生法国理论的历史背景早已发生改变,以至于诸多当初被认真对待和分析的议题如今似乎已经是可被替换的特殊“内容”;另一方面,似乎比“内容”更重要的“方法”或“思考方式”,却与充斥于互联网内外的种种“仇恨话语”的逻辑不谋而合。

尽管如此,在千叶的这本书中,还有另一条颇具历史性的线索——哪怕是一条零星出现的线索。这条类似萨义德所谓“理论旅行”的线索,涉及的正是“当代理论”在日本战后历史中的接受和流行。千叶的下面这段论述值得完整引用:
1980年代,在泡沫期的日本社会,对于德勒兹的介绍吻合当时的时代氛围:旧有的上下秩序开始瓦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发展和大众媒体的发达带来了越来越多新的活动的可能性。当时人们谈论的不再是过去那样的统治阶级·资本家与被压抑的劳动者之间的二元对立,而是如何介入更多向的、非二元对立的社会;比起单纯地敌视并打倒资本主义,人们认为有可能利用资本主义产生的新型关系,从内部对资本主义加以改变。
在这之后,进入1990年代,日本社会泡沫破裂,经济陷入低迷,不断向前的气氛结束了。仿佛与此并行的是,德勒兹热潮也结束了。比起乐观地以新的外部为目标,走到台前的是德里达式的思考,即发现微观的对立和冲突,谈论二元对立的困境。
有意思的是,千叶明确指出,上述转变在日本思想界可以归结为浅田彰关于德勒兹的畅销著作与东浩纪关于德里达的专著之间的分野。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在日本社会阅读德里达”或许从来不是一个中性的问题,而必定会在充满了“误读”、“误解”和“误配”的交流过程中,以及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条件下,产生种种始料未及的混合、污染和变化。不过,通过这一常识性的论断,我并不是想说,必须将德里达和福柯等思想家的著作还原到某个特定的语境下,才能“正确地”理解它们;而是想说,在1990年代的日本社会被阅读的德里达,不仅不同于1970年代的法国语境下的德里达,也必然与在2020年代的日本社会被阅读的德里达之间,有着重要且不可忽视的差异——而如何对这种差异进行勘测、分析或(用杰姆逊的术语来说)“认知测绘”,关系到我们对自己时代的理解,以及对于自身所处的历史处境的总体性理解。
千叶在书中另一处提到东浩纪的德里达研究的地方,无疑暗示了这种历史性的差异或差异的历史性。在强调日本当代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梅亚苏和马勒布等人未加重视的“否定神学批判”时,千叶再次从东浩纪所采取的“从单数的否定神学式的X向‘复数性的超越论性’转变”的思考路向那里,看到了一种新的“有限性”,它既非强调人对于无限之上帝而“有限存在”,亦非强调人的有限的“在世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千叶进一步将这种“有限性”和“人生哲学”联系起来:
这种淡淡的有限性不纠缠于谜一般的X,而是着眼于在生活中完成一个个的任务。
可是,我们真的需要德里达所代表的“当代思想”和它们的当代发展,来告诉我们上述“人生哲学”吗?无法以否定神学式的、将意义系统整合起来的那个“缺席的X”为中心来构想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各个领域呈现出彼此独立乃至断裂的重层格局,以至于每个人都必须精神分裂一般地应对特殊领域的特殊任务——这不是当今时代给予我们的最基本的现状吗?
王钦,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准教授,著有Configurations of the Individual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0),译有德里达《野兽与主权者I》、《赠予死亡》等。
文/ 王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