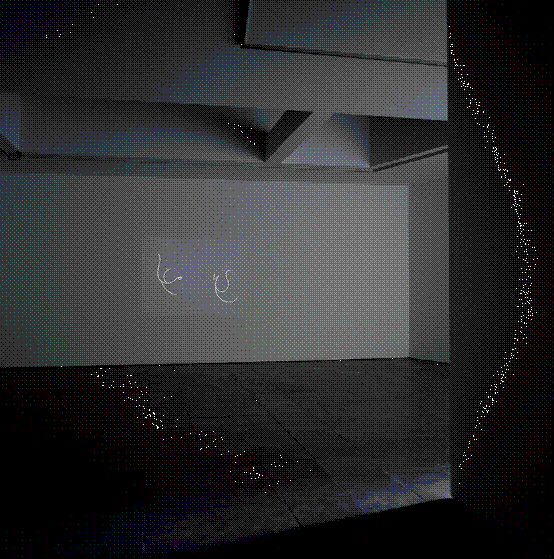
弗洛里安•普豪森
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标志着西方现代主义乌托邦梦想和普遍主义事业失去了最初的合法性,随之丧失的还有过去几十年间对欧美艺术生产和批评至关重要的媒介具体性(medium-specificity)。定点观念艺术实践和早期的机构批判拒绝艺术品的自我指涉,转而分析现代展览惯例(及其背后起支持作用的意识形态),指出该惯例不仅是美学体验无法回避的背景和前提,也是探索艺术与大众文化代码之间复杂关系的工具。然而,对现代主义独立性声明和霸权如此激进的揭露到今天本身也变成了大学本科生教科书里的内容。用艺术史学家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的话说,现代艺术原本坚固的经典体系已经不再是“需要猛攻拿下的街垒,而更多像成了供人拾荒的废墟。”(正如福斯特指出的,今天的艺术已经不光是处于“现代主义绘画和雕塑之后,而是处于对这些形式进行解构的后现代主义之后了。”)即便如此,回顾过去十年艺术创作中对这一后续状态的具体质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美学上的现代主义与整体上的现代性,艺术家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处理方式。一方面,大量历史主义色彩浓厚的作品挪用、模仿现代主义经典作品的发明和理念,或者单纯对其进行神化,加以膜拜,以便把它们作为品味和情调的合法象征献出(或者只是用它们制造一种复古的氛围,比如某些所谓的关系美学艺术家的装置作品)。另一方面,一些新观念艺术家开发出一种媒介自省式(media-reflexive)的处理方法,努力对现代主义衣钵进行批判性的重建。他们不去刻意宣告现代主义形式语言和野心已经过时,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其内部矛盾上,特别关注那些地理层面和社会政治层面上被边缘化的创作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