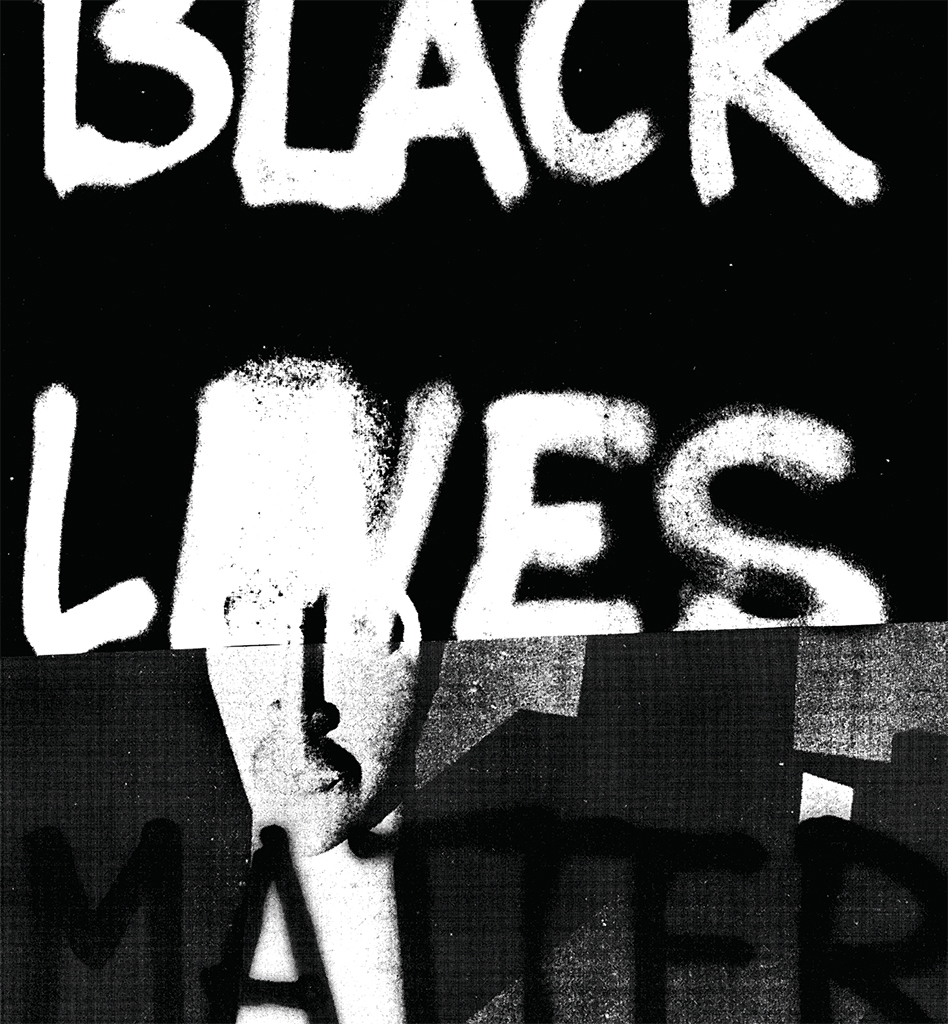
新野蛮:启蒙的身体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1984年讨论启蒙问题的文章中,以他典型的热忱呼吁一种“对我们所处历史时代保持恒久批判”的态度和精神气质。虽然整篇文章充满各种大声疾呼的反抗语气,但其立场却有点奇怪:除了原教旨主义者——如教条主义者、极端分子、狂热分子、信徒——谁会反对批判和温和实验呢?除了一点点修辞上的激进,福柯对启蒙的想法并没有涉及历史事实,他主张的是一种自我创造的美学和纯形式的批判伦理。我怀疑他这么做是怕万一有一天启蒙也被证明是一种历史错误、一种退步,或另一种教条主义——我忍不住猜想,可能福柯最大的恐惧是蒙受历史尴尬(historical embarrassment)。
当然,福柯知道的不止这点。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1975)中,他提出,经过启蒙的现代性的诞生包含了惩罚措施的急剧转变。七百年来,在欧洲,野蛮酷刑不但是审判前一个重要的司法审问环节,也是一种最主要的处罚机制。前启蒙时代的刑事司法系统从始至终都是以酷刑为主。然而在十八世纪后三分之一至十九世纪初的短短几十年内,酷刑迅速从欧洲大陆上消失(福柯忽略了其在殖民地的存留)。他以优雅和准确的语言描述了这一非同寻常的变化:“肉体疼痛,即身体本身的疼痛,不再是刑罚的一个构成因素。惩罚从一种制造无法忍受的感觉的技艺转变为一种暂时剥夺权利的经济机制。” (斜体是我加的)就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