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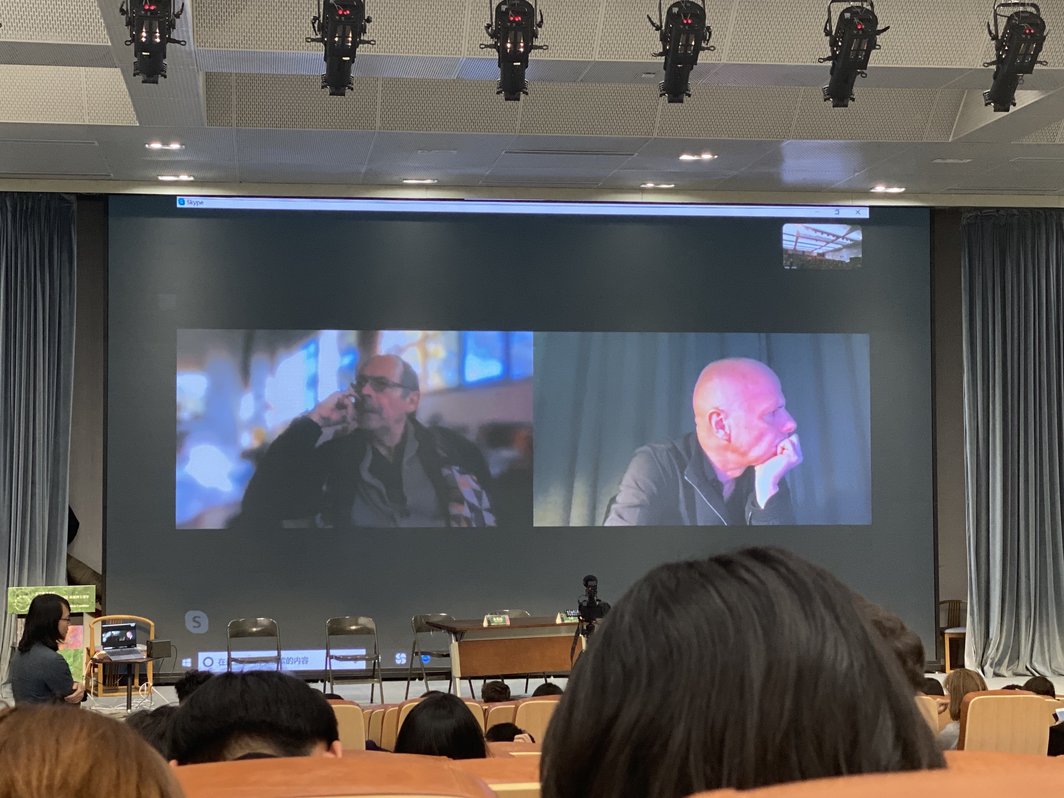
“Inter-World-View”,顾名思义,代表了不同世界观之间的交流。这场由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发起的跨学科交流活动被安排在一个紧凑的档期中间:前有纪念利奥塔著作《后现代状况》出版四十周年的“后现代及其后”研讨会,后接青年学者云集的第四届网络社会年会“网民21:超越个人帐户”。与前后两个学术高压项目相比,“Inter-World-View”显得更加草根、甚至野生:参与人员背景多样、报告呈现形式灵活。然而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大概在于时间线拉得够长:连续十天从早到晚、从晨读到工作晚餐的活动安排得密密麻麻,算下来所有与会人员要共处一室超过100个小时,贯彻了一种当代鲜见的肉搏交友理念。
早在九月份发出的活动招募公告中,主办方就明确提出与会人员要保证至少十天的在地参与,以确保每个小组在完成自己为期半天的展演之余,还有九天半的时间为其它小组充当观众。这与“后现代及其后”研讨会上日本学者东浩纪(Hiroki Azuma)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他看来,要改变游戏规则,观众至关重要。在我们向垄断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单一优化逻辑发起对抗的过程中,如果想让小到体育竞技、大到政体模式的“语言游戏”能够以真正多元的形式存在,就必须正视“游戏观众”在这一机制链中起到的牵制作用——没有观众督导的游戏可以任意变动规则,观众是多元世界观各自成立的前提。

在全体与会成员的见证下,“Inter-World-View”于11月11日周一一早在美院美术馆一楼大厅启动。现场被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装置空间,地上略显凌乱地铺放了一些无纺布地图。这一名为“异世界”的展览版块收集了从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蓝图、爱尔兰传说中的世外桃源(Tír na nÓg)地图、罗伯特·史密森的《螺旋形防波堤》俯视照,到更多说不上来故事的地形图像。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地图代表了人类历史上对乌托邦的探索与想象,也承接着对于今天宏大叙事的重新构想。诚然,利奥塔所谓的“宏大叙事的终结”并不代表一切总论的终结。“我们也通过在历史中寻找可能,来完成对今天当代艺术现状的批判和反思。今天的斗争更多的可能性是存在于形而上领域。”执行策展人刘畑说。
对历史的反思似乎无处不在。大堂旁边的漆黑的投影间里正播放着去年逢中国美院建校90周年校庆,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组织举办的“世纪:一个提案”的演讲录音集锦。另一相关活动则延续了2013年国美85周年校庆时的“85·八五”主题,追溯了那个林风眠和潘天寿还活着的年代,围绕他们书写的现代主义叙事如何在今天被单一的中国前卫艺术运动史所遮蔽。将中国现代主义与前卫运动并置的策展角度近来备受青睐,联想现代性在全球语境下不尽相同的阐释和名声,大概也是区域特殊历史背景的一种体现。九点没过多久,十五组与会人员纷纷就位。大家先轮番上台进行简短的自我介绍,之后本组对接的策展人会从地上挑选一张主题适宜的地图,交给小组成员,再由成员们再颇具仪式感地将地图在空中舒展、平铺在地面上,以完成“铺设蓝图”的象征动作。仪式感是否为知识带来合法性的依据?

周一下午,我们在既是与会成员,又担任整个项目展陈设计的“九樟学社”小组带领下走入散发着新鲜丝网油墨气味的地下一层展示空间。展厅内处处留有未完成的痕迹,大概是等待着被未来十天的活动记录逐渐填满。我和其他观众一起饶有兴致地穿梭于展厅中,时而提鞋光脚踩过热带病小组铺有长绒毛白地毯的展厅,时而吸气收腹钻入狭窄的通道,眯眼从墙上随机钻出的孔眼中窥视“家园计划”小组的拼贴墙画。展示空间不规整,但无疑多样,且巧妙迎合了每个小组的项目特点。唯一带天窗的明亮空间被分给了“北国项目”,这个由律师、程序员构成的组织在山西临汾自行圈地“开国”,甚至还有自己的象征符号,出于实际原因无法在现场展示。阳光透过天窗照在瓷砖地上,通道两旁还洒了一层泥土烘托气氛。当然,脚踏实地的田园牧歌乌托邦背后是土地明确的政治属性;更不用说,在中美贸易战尚未和解的今天,农民还处在战斗的前线。
下午第二场活动由以“万物需有寄托之地”为口号的“九樟学社”呈现。也许是因为上午晨读会上从“巴别塔”引出的关于方言与个人生活经历的话题还没聊完,下午的对话开始没多久也转向了谱系、祠堂,以及个人历史考古的方向。小组成员拿出一张巨大的世界地图(为什么又是地图?)在观众间传递,让大家用不同颜色的笔标出自己人生中曾经居住过的城市。“我们从哪一刻开始意识到故乡的概念?”主讲人问道。我坐得腿麻,决定站起来走走。看到一旁“重庆工作研究所”的组员还在布展,便凑上去攀谈。听董勋和吴剑平介绍,他们将通过回顾卢作孚指挥的宜昌大撤退,并以我国首个称得上规划设计的城市——北碚为例,设想一种以重庆为参照的未来主义解决方案。

到了晚上,“熟道”小组在一张颇具“曲水流觞”意味的轨道状长桌上摆出了精心准备的工作餐,听说每天的食谱选择与食物发酵程度挂钩,腐烂程度与日俱增,以呼应展厅空间思考不断发酵和生成的过程。我赶上的第二天工作餐里的食品包括乡村面包、桂花糖蜜和培根——相当友好的入门级别。在等待晚上“Passepartout Duo+AnyOne”小组根据一天的讨论而作的即兴音乐表演时,我被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小组的展示空间吸引,忍不住上前与对方组员探讨起“为什么十一当天有雾霾”的问题。对方态度专业地向我解释,当天只有早上出现轻微雾霾,不巧赶上了阅兵直播。对方接着说:“雾霾相较之前两年已经在逐步好转了,我们目前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计、控制污染源。当然,这个问题也有其道德上的复杂性,你说美国在中国投资建厂产生雾霾,应该算谁的?”我点点头,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尚不能被取代的今天,这样的问题一时半会儿不会消失。
作为一名不合格的观众,我没能按要求待满10天,但经过短短两三天的参与和观察,还是不难感觉到各组之间细微的坐标差异。如果如主办方所言,“Inter-World-View”的宗旨在于促成某种“未来导向的合作网络”形成,那么大家对于到达“未来”的路径显然还未形成统一的认知。英国艺术史学者莎拉·威尔逊(Sarah Wilson)在“后现代”研讨会上倡议将同在蓬皮杜举办的两场展览——由利奥塔策划的“非物质”(Les Immateriaux)与马尔丹的“大地魔术师”(Magiciens de la terre)——放在同一语境下解读;再没有比这两个相隔四年、面貌却截然相反的主题展更能佐证“后现代”时态与语系的高度混杂。如何在设想未来时有效地调动现有经验?在同一场研讨会上,菲利普·帕雷诺(Philippe Parreno)提议将目光投向诸如“阳光朋克”(Solarpunk)之类的替代性乌托邦设想。未来主义与乌托邦无疑是这十几天活动的高频词,然而乌托邦与“逆托邦”(Retrotopia)仅一字之差,后者隐形的陷阱也许每个探路者都不得不加以警惕。




文/ 杨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