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2010年10月23日下午,出门去上海美术馆的时候,下着濛濛细雨,杨福东说:“这场雨是笼罩在高士明心头的一块阴霾。”如果这是真的话,至少在人头攒动的第八届上海双年展开幕式上,我没看出来。作为本届展览的三位主策展人中最年轻的一位,高士明脸上洋溢着的更多是意气风发。他同时还担任上个月于杭州新成立的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的常务副院长。这个学院由原先的三个较为“当代艺术”的系:新媒体系、综合艺术系和艺术策划系,整合而成。外界普遍看好高士明的仕途。他要足够机智才能想出“巡回排演”这样一个时髦、国际化、有丰富可能性的主题。双年展的另外两位主策展人是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和上海美术馆馆长李磊。
这届的双年展,没有了恐龙、火车这类出现在零八年双年展上的吸引眼球的大作品。这些象征着艺术市场鼎盛时期的傲慢与自豪、追求体量与一掷千金的大型装置,像那个“什么都能卖”的时代一样,一去不返。如果说那种独特的趣味还遗留下一丝余韵的话,那可能是张洹从浙江衢州搬至一楼展厅的有着450年历史的木结构明清老祠堂。这是他一年前为比利时皇家歌剧院导演的歌剧《塞魅丽》的舞美主体结构。穿行在基本按原样布置的古老祠堂内,我似乎懂了为什么有人称张洹为“艺术圈的张艺谋”。

五十多位艺术家/组合瓜分了这幢优雅的英式建筑——前“上海跑马总会”大楼。一楼的主要空间被“胡志明小道”所占领。这个由长征空间“外包”的项目,作为第八届上海双年展的第一幕,集结了一批艺术家、新左派知识分子和策展人,较早前完成了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的“行走”和在北京“长征空间”的展示。艺术家徐震担任法人代表的“没顶公司”的小幅油画装置,蔓延在展厅里,像黄梅天墙壁上的水渍。以至于一位业内人士指着地上吴山专的装置说:“这是‘没顶’效仿吴山专的作品,学得真像。”
距离杨福东的十屏录像装置《第五夜》不远的展厅,是艾萨克.朱利安的录像作品《浪》。猜猜我在银幕上看到了谁?杨福东。根据片尾演职员表,他饰演的角色是“情人”。 促成业界和公众难得达成共识的是挪威戏剧团体“世界剧院(Verdensteatret)”的《然后所有问号开始高歌》。双方都对它表示了喜爱之情。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艺术家们,合作演出了一场集机械装置、表演和声音艺术于一体的戏剧。这场声色并重的表演,被称为“器物剧”。轮子在音响配合下像向日葵花盘一样转动,想象力美妙的翅膀阴影掠过了幽暗的展厅。开幕式下午五点结束,意犹未尽的观众被请出美术馆。“巡回排演”远未结束,双年展的第二幕“指路明灯”将与Performa(纽约表演艺术双年展)合作,11月初在纽约以肥皂剧的模式展开,思考和讨论上海双年展提出的若干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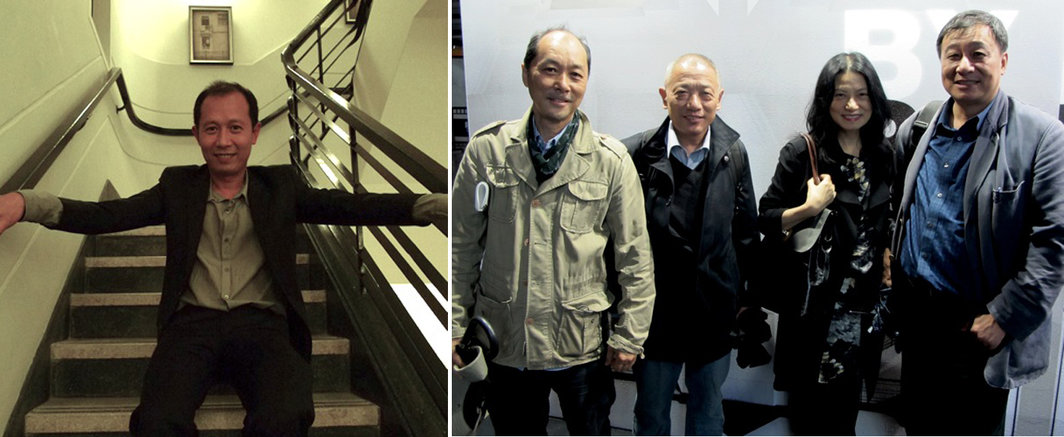
同日开幕的,还有双年展的另一单元“从西天到中土——时.地.戏:中印当代艺术展”。展览衍生出来的“印中思想对话”系列被认定为“巡回排演”的第五幕。曾和高士明共同担任过第三届广东三年展策展人的张颂仁是展览的项目总监。他另外的广为人知的身份是香港“汉雅轩”画廊的老板,坊间传说他持有张晓刚等人相当数量的早期作品。
我在雨中钻进艺术家杨振中的车子,奔赴“中印当代艺术展”设于外滩美术馆附近的一个展场。先参观的是原来的联合教堂,这座有144年历史的巴洛克建筑里,曾梵志的个展尚未撤展。身穿暗红色莎丽的印度艺术家尼丽.玛谢克(Nilima Sheikh)一脸愁苦地徘徊在教堂里,她的十四幅绢本蛋彩画经幡,从正中的天花板上垂挂下来。窗边矗立着曾梵志用金丝楠木制作的覆盖在布下面的“哀悼基督”雕像。

更多的作品放置在相邻的原教会宿舍里。这栋四层小楼的整修好像尚未完工,使用简陋的日光灯照明。一个海外评论家对着邱志杰的装置作品《拉萨到加德满都的铁路》一边拍一边摇头说:“太过分了。”他对汉族人运用西藏唐卡这种艺术形式来创作很不满,但他好像并不反对中国人创作油画。四楼展厅一片漆黑,画已经挂好了,我们用闪光摄影拍下画面后欣赏,邱志杰猜测道:“这应该是那个印度的细密画大师的作品——”我摸索到角落,用手机照亮作品标签,答案是:(上海艺术家)刘大鸿。
从顶层阳台上眺望雨丝笼罩下的英式庭院,邱志杰指给我看:“那就是以前的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这一片正在开发中的外滩地块,是洛克菲勒集团有份投资的“外滩源”项目。它是上海外侨最早涉足之地,也势必成为下一个热门地标。这时,从“中印展”南京西路展场传来的消息说:那里的作品大都还没有拆箱。事后得知主办方签约的那家施工队,在最后一刻背弃了他们,转而去做一个上海世博会的大项目去了。在今年十月的上海,什么都跟世博会有关。

双年展开幕的前一天傍晚,我们在莫干山50号,胡介鸣个展《一分钟的一百年》在香格纳画廊H空间的开幕式上。他将1100个美术史百年来的经典图像经过动画处理,投影在并排放置的IKEA储物袋底部。在院子的另一头,王劲松的个展《天问》也在开幕,“7艺术空间”像一块飞地,充塞了来自北京的业内友好:“当代艺术教父”栗宪庭和艺术家叶永青、杨少斌、岳敏君等。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正是批评家栗宪庭在著名的《“后89”艺术中的无聊感和解构意识》一文中将王劲松例举为“玩世写实主义”的代表艺术家之一。
《天问》并没有延续“玩世现实主义”的风格。一共660帧拍摄自全国各地俯拍的平民头像灯箱片,镶嵌在一幅舞台式的玻璃地板之下,一张张困苦焦黄的脸仰面朝上。观众容易产生一种俯首问苍生的权力感。我大致理解艺术家的人文关怀,不过我不明白一群文艺人士和抽雪茄的收藏家在劳苦大众头顶上踩来踩去,怎么就有助于体现这一关怀了呢?
上海双年展开幕第二天,是M50西部桃浦创意园区(Shanghai Top)的艺术家工作室及香格纳展库的公众开放日。TOP由开发上海莫干山M50艺术区的同一家公司打理,M50的原址是上海春明粗纺厂,TOP则改造自上海纺织系统下属的凤凰毛毯厂。在徐震助手陆平原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没顶公司”一千平方米的“生产车间”,里面堆满了布料、海绵、机器,阳光从高处的天窗洒下来。杨振中、周啸虎、杨福东、刘建华等人的工作室都设于此,他们工作室的蓝底白字的铭牌镶在各自的门首。

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整洁园区,我被告知桃浦的日租金已经从一年前的每平方米八毛涨到了两块二。与此同时,艾未未上海嘉定的工作室正面临被“选择性”拆迁,他正在借助网络准备一场事先张扬的告别演出——“河蟹盛宴”,届时会供应一万只蟹和充足黄酒。上海并非对所有艺术家敞开大门。
是日,我从桃浦转战外滩美术馆,出席他们的第一个群展“日以继夜,或美术馆可为之若干事”开幕式。夜幕低垂,雨又开始下,保安持伞逐个护送嘉宾从停车场前往美术馆。外墙装饰着葡萄牙艺术家彼得罗.加布里塔.莱斯(Pedro Cabrita Reis)的作品《里—外》,数百根点亮的日光灯管所暗示的内部平面图,荧然倒映在雨地的水洼上。包括周铁海、聂德科.索拉科夫(Nedko Solakov) 在内的九位艺术家参加了这个由侯瀚如策划的展览。展览活动由白天延伸至黑夜,晚间提供给市民由艺术家精选的电影放映、夜校、讲座等,宣称要成为“一个与永不停息的城市现实生活共享律动的事件”。从这一点来说,“日以继夜”很好地呼应了双年展的“巡回排演”主题。

外滩美术馆也是“洛克.外滩源”项目的一部分。前身是“亚洲文会大楼”的这栋Art Deco风格的历史建筑建于1932年,曾是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之一,经重新设计修缮之后,于今年五月作为美术馆开幕。原本用来陈列英国侨民从长江流域和华北捕猎的动物标本的地方,现在已展出过蔡国强和曾梵志的艺术作品。
在回京的飞机上朋友说:“世博会结束了,中国怎么办?”答案不仅仅是“接着开广州亚运会”这么简单。赶往展场时,一位上海本地出租车司机对我说:“世博会和我们老百姓有啥子关系?”忽然发现这几天以来,我一直穿梭在两类建筑里:殖民地建筑和新中国工业厂房。“殖民地”和“工业”是上海身上的两块胎记。她便在这两种记忆的牵扯下,辗转反侧。我刚刚享用过的这一轮艺术盛宴,在盛世盛会背景的烘托下,隔了点距离看,恰如民国时代的上海女作家张爱玲写过的,像这城市的“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文/ 任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