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邱志杰为本届上海双年展绘制的“重新发电地图”错综复杂,四个以Re打头的英文单词(Resource, Revisit, Reform, Republic)分别对应“溯源”、“复兴”、“造化”、“共和”四大部分。尽管中英文意义上存在微妙的出入,观众也不一定有耐心仔细考察这张像集成电路一样密密麻麻的手绘地图,今年的双年展的确跟往年大不相同。
浦西世博园区的城市未来馆(原南市发电厂)经过改造后变成双年展新的主展场,空间和规模超过了目前中国所有三、双年展,政府拨款也是往年的四倍。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晏思•霍夫曼(Jens Hoffman)和张颂仁加盟策展团队,带来不少优质的外国艺术家作品。但大有大的麻烦,新有新的问题,上双还没开展,坊间就流言四起:展场管理混乱,距离开幕不到一周城市馆还如同建筑工地,外国策展人无人接待⋯⋯最后邱志杰不得不站出来“辟谣”。如此种种,反倒让人对上双开幕充满期待:传说中的中国速度这次能不能再现神奇?
因为听说很多上海本地艺术家没有收到邀请函,开幕前一天碰到的所有熟人都在打听明天怎么混进去,为保险起见,我决定30号下午找机会溜进浦西世博园的主展场先看了再说。

一进大门就看到黄永砯的“千手观音”真的变出一千只手伫立在中庭,搞得一块儿溜进来的陆平原不停感叹“真是高富帅”。上楼发现邱志杰和许江正带领着领导看场地,为明早正式开幕做准备,于是混在公务员队伍里跟着听——明天重点看哪几件作品,从什么地方开始,到什么地方结束,计划制订得详细又周密。一位穿两件套套装的女干部边听边跟身边的人笑着说:“他(邱志杰)一直在讲艺术,而我一直都在说和谐。”在为当代艺术争取空间和资源的过程中,需要多少柔软的战术、必要的妥协,个中滋味可能只有正在滔滔不绝讲解作品的邱志杰清楚。
布展尚未结束,很多艺术家还在自己的展厅等待相关人员来协助解决各种技术问题。王郁洋说他的布展时间只有八天,我们见到他时他还在跟工人调整灯管位置。从策展团队成立到开展总共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类似的急行军情况应该还有很多。
第二天上午的开幕是市委领导专场,据说只有大约两百人参加。从宣布开馆到奏乐,再到白鸽齐飞,完全是新闻联播里的经典仪式的搬演。而下午轮到从各地齐聚上海的艺术界业内人士时,场面则陷入民间特有的混乱:门里的人拿着各种证件、邀请函、贴纸等着接应朋友;门外的人忙着打电话看认识的人有谁已经在里面。

进去后发现不少艺术家坐在一楼的咖啡馆,一问原来楼上还有保安,人多证少,所以决定先原地待命。我问蒋鹏奕借了一张艺术家工作证,上扶梯迎面碰上田霏宇(Philip Tinari)夫妇。“This is so Contemporary.” 田馆长做了个鬼脸。
二楼提诺•赛格尔(Tino Sehgal)的作品换了张黄色的面孔,几位穿白衬衣的中青年“演员”据说为此辛苦排练了很长时间。秦思源在穿过这件作品时忍不住皱了皱眉头,估计是想起了“原版”。的确,无论是作品,还是国际大展的形式,一旦移植到中国,总免不了染上股不是滋味的滋味。现实如此,可能最大的差别在于每个身在其中的人看待和处理问题的方式。
邱志杰显然属于某一类实干家,在大环境下从没放弃过主动权。今年上双值得称赞的不仅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了一个宏大的项目,还有策展团队在打破双年展常规和僵局上所做的努力。在21世纪头十年已经过去的今天,后者已经成为全球艺术界共同面对的难题。

很多中国艺术家没有看完展览就匆匆离开了,并不是因为对参展作品缺乏兴趣,而很可能是这种大面积、大规模的实体展览本身让人不约而同地感到了疲惫。展览开幕三天后,听说吴文光的“饥饿计划”被当局叫停,更让人觉得老戏不断上演,我们距离真正的“重新发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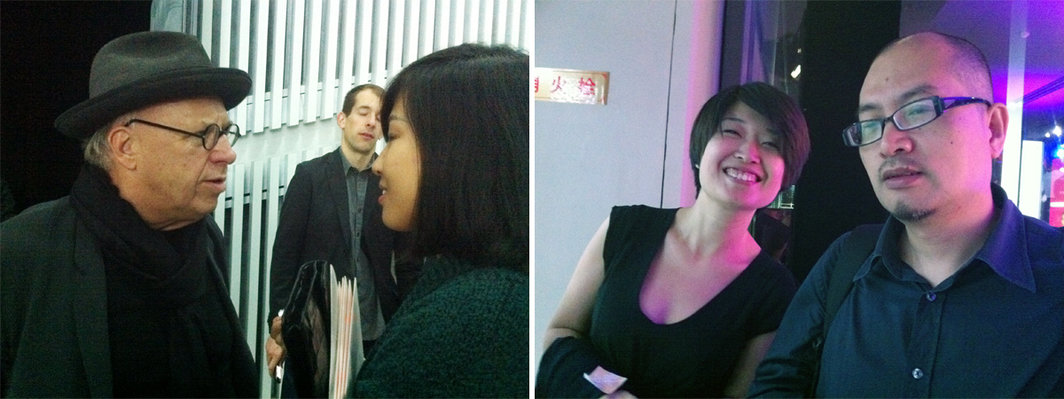
文/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