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驱车前往广州时代美术馆的路上,窗外时不时飙过一两辆自带改装遮阳伞的电动车。四两拨千斤的改装充满民间智慧:两三伞骨延长形成流线型尾部,符合空气动力学,游走于车河中又很拉风,惹得策展人侯瀚如赞不绝口:“这比扎哈哈迪的设计牛逼多了。”这样的改装和这样的赞赏都非常之广州,让我想起两天前他对艺术家陈劭雄的评价:“不伦不类”。这诚然是种嘉许,意指多种媒介和创作方式混杂的实践;用来形容陈劭雄九十年代初在广州与徐坦、林一林、梁钜辉组建的艺术小组“大尾象”十分贴切。6月10日与12日,由侯瀚如策划/合作策划的“陈劭雄:万事俱备”和“大尾象:一小时,没空间,五回展”分别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和广州时代美术馆开幕,个体与集体,边缘到机构,两番回顾,交叠出长长回响。
陈劭雄个展前的研讨会有一个颇耸人听闻的题目:艺术可以反恐吗?听下来则觉得更像是艺术家多年同行与共谋者们的茶话会,言之有物也有料。座谈嘉宾背后的投影来自艺术家2003年的作品《花样反恐》:城市中的高楼通过自变形态躲避飞机撞击—一种后911式的荒诞幽默。对艺术家多年的合作者侯瀚如而言,陈劭雄对日常政治的判断“每一次都有惊奇,是大政治中很核心的内容,但是通过细微的日常动作表达出来。”台上唯一一位非南方艺术家王功新则借题发挥出了别的意味:艺术不一定能反恐,但一定不能成为恐怖主义,例如斯大林和纳粹时代的艺术。当一场关于已经登堂入史的实验艺术在今日之“边缘性”的讨论展开时,前排一位姑娘手机屏幕上美图软件里高倍放大的自拍照牢牢地攫取了我的视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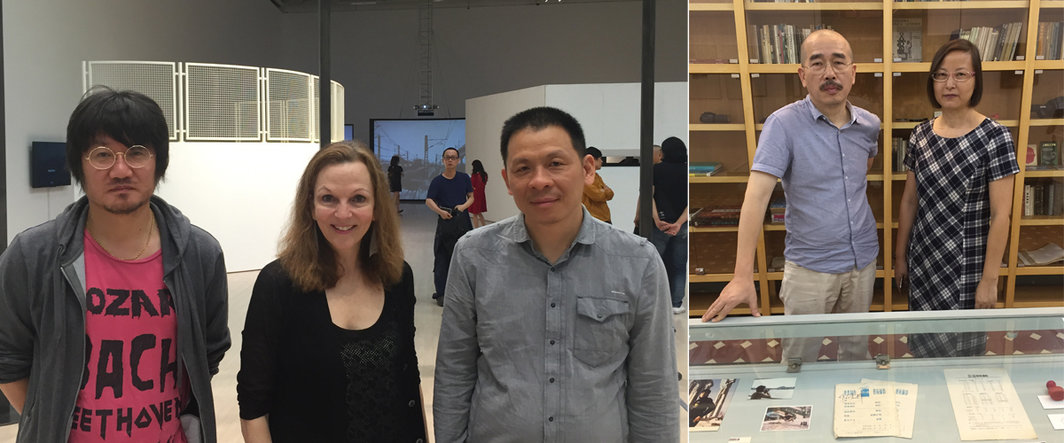
作为回顾性质的展览,“万事俱备”十分利落精简,以重要作品提纲挈领,注重观展体验和动势。观众在此次展览上可以看到摄影拼贴装置《街景》迄今为止可能最完整的版本—九十年代早期城市化的景致、能量在今日成为熟悉而陌生的标本。更多的合作者、同道人涌现到开幕现场:广州美院的老师和同班同学、2008年与陈劭雄一起组团出道的“西京人” 金泓锡和小沢刚。诚如另一位“大尾象”成员林一林在研讨会中所说:陈劭雄一直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不论创作内外。展厅中为影像《西京奥运》特意架设了体育馆式的观众席,片中的无厘头竞技项目在又一个奥运年里对民族主义与国际竞赛放出了恶作剧般的冷箭。艺术家本人因为身体状况无法到场,一切布展和开幕事宜均由艺术家的妻子罗庆珉代劳。开幕现场播放了一段他预先录好的致辞,对侯瀚如的那句“与你合作令我体会到工作的乐趣”,惺惺之情可见一斑。
开幕饭后的酒吧聚会上,林一林说起当年和陈劭雄一起在边缘“晃来晃去”的日子,九十年代广州唯一的“红蚂蚁酒吧”,中山医学院的非洲留学生和雷鬼乐,以及著名国际策展人Okwui Enwezor寻访到的“艺术现场”:因为大尾象介入停车场、工地、街道种种社会空间创作,并无工作室,展示作品的场地便选在了徐坦学生开设的舞厅里,影像作品直接打在表演的舞女旁边—“那次没有任何一个人被选上”。

虽然大批人马被恶劣天气状况困在上海,时代美术馆的开幕依然人气爆棚。拔地而起的高层露台俯瞰一片低矮的城中村,梁钜辉1995年在施工升降机里实施的作品《游戏一小时》被巧妙地装在了电梯里。开幕嘉宾们挤在溽热的户外轮番发言,已成传说人物的栗宪庭和张颂仁身边围绕着各种求合影的新老粉丝。我想起上海研讨会上侯瀚如对边缘作为态度的一番主张:“站在当代文化边上,就永远不应该站在主流里面,哪怕是跟主流机构合作。”然而,主流机构之外毕竟依然有广袤的城中村与艺术界之外的现实政治。策展人们还说,“大尾象们依然做着大尾象式的艺术”;“珠三角从来没有‘贞洁’这一回事。”于是你又觉得脚下那片城郊里可能还有类 “大尾象”的艺术发生,或者至少有着那样的土壤。
合作策展人蔡影茜出现时,脖颈上已经贴着展览的“衍生品”— 梁钜辉《生产空间与蚂蚁》(1998)装置衍生出的蚂蚁纹身贴纸。担任主要研究工作的她告诉我,这次展览几乎有百分之九十的作品与“现场”都是通过档案旧照甚至更不怎么牢靠的口述、回忆来重现的,而这往往与作品本身的时间与行为性质相关。从这个意义上看,此次回顾展更像是一次大尾象的“蒙太奇”。大尾象成员访谈与对话中的一些散句疏影横斜地贴在美术馆教育区域的地面与墙柱上,有些像判词,有些像呓语,或两者兼有,如早期成员之间对谈时徐坦所说:“梁钜辉在艺术上的堕落倾向是怀着一种美好心情。”人山人海中导览开始之时,不知道什么时候换好一身黑衣的林一林与重现的1998年装置《XX亿零一个III》合体,连青砖之间的人民币也是特意置办的复古款。虽然艺术家说他没等来策展人的讲解,不少围观群众带着“看到活的行为艺术”的欣喜之情,通过合影与自拍也把作品“看”了千百次。

当天早些时候,博尔赫斯艺术机构中的“梁钜辉档案展”和寄居此中录像局的配套录像播放开幕,为此番的回顾又添一层共振。展览由博尔赫斯机构内梁钜辉纪念室的负责人、年轻艺术家黄河策划,艺术家夫人余国庆亦参与整理梳理。许多早期影像作品在这里第一次得以转录和播放。看着《漂浮的移植 》里那些飘来飘去,最后扁平扑倒在地,层层叠叠的数码人群背影,很难不令人想到陈劭雄的《街景》以及两件作品之间的对话。大尾象回顾展的策展人们这样概括四位成员的不同侧重:梁—共享与观众;林—身体与空间;陈—城市化感观;徐—社会问题与议题。虽然从未共同署名创作任何一件作品,四人之间的映照却清晰有致。
博尔赫斯机构负责人陈侗在开幕上做了简短发言,将梁钜辉比作艺术圈的一位保护神。一来他为许多重要展览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例如九三年香港那场被不少人认为将中国当代艺术推上国际舞台的“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展(梁并未参展),二来他常以职务(广东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美术指导)之便为本地与到访广州的艺术家们提供种种帮助,在国内艺术体制发展的混乱雏形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这并不是说今天的体制就已经成熟—“梁钜辉档案展”是博尔赫斯在海珠区怡乐路现址的最后一个展览;机构本身因房屋无产权而被迫需要迁址。无独有偶,上海BANK画廊也在几天后遭遇到了同样命运。

再次回到上海当艺术博物馆的研讨会,陈侗就广州艺术现状发表过这样一段思考:“年轻艺术家也不一定知道大尾象。以后广州再也不会有(新的)美术馆了,但是上海还会有。今后大尾象还有没有展览,还真不好说,但是精神是会一直存在的。好像介绍大尾象就是在介绍珠三角的艺术,是这样一个意味”。离开广州那天,由一帮年轻艺术从业者合伙新创立的广州画廊负责人之一在微信上对我坦言:“在广州,做什么都很难”。他的意思是本地的当代艺术收藏家非常少,收本地当代艺术的藏家更是少上加少,多年未变。也许从某个意义上讲,这也是“大尾象依然在做大尾象式的艺术”的原因之一。好在依然有年轻一代艺术从业者们在自由、勤勉而笃定地推动着新的生态。比如不论在地还是在微信上都缓释着惊人能量的黄边站,又比如首届广州五家非营利艺术空间(“五行会”)联合举办的筹款晚宴。与其他裂变的一线艺术城市相比,广州的生长感更强。不过裂变有裂变的能量,生长有生长的滋养。说俗一点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文/ 王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