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FILM & VIDEO

去年,当第一波Covid-19疫情席卷印度时,各家电视台短暂地将注意力从精英阶层对沙文主义和社会名人的狂热梦想转移到了穷苦劳工噩梦般的处境上。与其说是病毒造成了这一切,还不如说是政府的应对方式带来的灾难。在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于3月24日宣布封锁后几天后,大批工人逃离城市前往农村,其中大部分人只能依靠步行。一夜之间,超过1.3亿人失业;工资如此之低,社会保障又如此稀缺,这些人往往连维持几天生活的积蓄都没有。社会学家扬·布雷曼(Jan Breman)口气尖刻地反思道:“这些动荡不安的群众的图像,至少让城市居民看到了这些劳工微弱的存在,此前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外来劳动力的庞大规模与其脆弱性。”社会活动家哈什·曼德(Harsh Mander)则评论说,这“可能会是大多数印度人有生之年看到的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
评论者用严肃的口吻谈论着“移工”的“危机”。然而这次大规模驱逐只是证明了一个以“劳动力灵活性”为重的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跨国公司太知道这一点了:印度的工作环境标准是全世界上最差的。问题不在于法律本身——尽管自1991年以来,法律就不断受到侵蚀——而是当国大党彻底甩开已经腐败不堪的国家资本主义,转而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绑定在一起(结果显然不妙)。受这种变化直接影响的工人相对较少,这恰恰揭露了真正的问题。独立七十年后,绝大多数印度人都在“非正式领域”内工作——这也就意味着,没有稳定的工资和工作场所保护,通常处于欠债状态。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了法律保护之外。
在印度工厂工作是什么样的情形?三部纪录片(目前全部免费播放)尝试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安贾尼·蒙泰罗(Anjali Monteiro)和K·P·贾雅桑卡(KP Jayasankar)的《织布机》(Saacha: The Loom,2001)是一首孟买倒闭棉纺厂的挽歌,影片围绕着两个男人——一位诗人和一名画家的生活编织而成。 拉胡尔·罗伊(Rahul Roy)的《工厂》(The Factory,2015)记录了2012到2015年在新德里附近一家汽车厂发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罢工事件。拉胡尔·贾因(Rahul Jain)的《机器》(Machines,2016)则从古吉拉特邦一家纺织血汗工厂肮脏的室内空间中展开讲述。这类作品大多是对被主流媒体忽视的斗争和不公正的记录和见证。它们提供了了解印度劳动力处境的线索。影片中出现的画面令人不安,有时甚至让人感到震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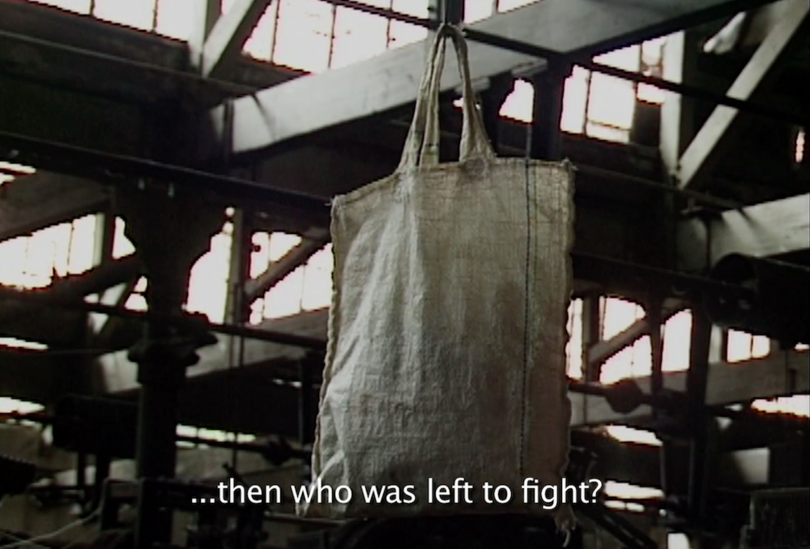
不公是这些电影的一个共同前提,重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所说的“失败的经验”。这在《织布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它回顾了孟买棉纺厂的鼎盛时期,这里曾经是一个庞大的工人社群最活跃的中心。(这部电影最近在第四届科钦-穆吉里斯双年展上放映过,我也是在那里第一次看到)。1982年,一场传奇的——但缺乏战略——纺织厂罢工被镇压,超过十五万名工人遭到解雇。今天,“从前纺织厂的土地变成了公寓、办公室和迪斯科舞厅,”电影中的字卡告诉我们。(在这些地区兴建的商场和购物中心的图像在影片接近尾声时出现。)我们透过已故的纳拉扬·苏尔维(Narayan Surve)——他是一位出色的马拉地语诗人——身处其中的视角了解这个一度蓬勃的世界。苏尔维是一名弃婴,被一个纺织厂工人收养,他从童年时代就跟着养父在纺织厂工作,后来加入了工会的文化部门。画家苏迪尔·帕特瓦丹(Sudhir Patwardhan)则提供了一个局外人的角度,镜头时不时会回到他那些色彩温暖、迷宫般的工人阶级生活区画作。
这部50分钟的纪录片结合了对两位艺术家的采访,以及仍在运营的阴暗肮脏的纺织厂内的简短镜头。其中一个镜头停在了一台废弃生锈的机器上。虽然记忆被受访者的柔情和幽默唤起,但这个行业的衰落仍像乌云一样笼罩着一切。“对我来说,这里早年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帕特瓦丹总结道,他哀叹“纺织工业罢工和随之而来的对劳工的普遍信心的丧失。”而苏尔维则表现得毫不退缩:
很快他们就要把我们在市场上强行出售
那么此时袖手旁观又有何用?
于是我起身,走出贫民窟
在工人们间低声耳语
我们现在必须向前

如果《织布机》是激进的怀旧之举,那么罗伊的《工厂》则是在变动中捕捉历史。这部电影将三年间发生的故事压缩进了两个小时。电影讲述了位于新德里郊外工业区玛尼撒尔(Manesar)的日本马鲁蒂铃木(Maruti Suzuki)汽车制造厂发生的骚乱(自新千年以来,作为全球排名第六的印度汽车制造业就普遍存在劳工骚乱的情况),叙事始于2013年年中,一年之前,这里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罢工,最终引发了暴力对抗,一名经理丧生。2400名工人被解雇,148人被控谋杀。
审判是影片展开的背景,罗伊与被解雇的员工、他们远在偏僻村庄的家人、为他们辩护的律师以及其他参与这项事业的行动主义者交谈。(玛尼撒尔罢工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他的镜头记录了示威游行和法庭会议,但他似乎更喜欢在这些事件的间歇与人交谈,此时人们往往处在焦急的等待中,不那么戒备。影片中还有一些设计过的片段,比如工人们用白板解释工厂的泰勒式管理方法——罢工正是为了改变这种制度。我们了解到汽车必须在55秒内组装完成;员工迟到一分钟就会被克扣工资;午休和茶歇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这种将工作时间切分成微小标准化模块的模式,与这场形状不明、不断推迟的审判形成了鲜明的、苦涩的对比。罗伊从始至终都对政治化时刻保持着高度敏感。在电影中一些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里,工人们反思了工会是如何改变了他们。 “从前我们的想法是,他们是所有者,是受过教育的人,所以他们有权指挥我们,”一名男子说,他蜷缩在逼仄的宿舍里,正用地板上的一个破炉子做饭。 “但是现在我们明白了,正是因为我们的劳动,公司才可能存在。”
政府干预并镇压了玛尼撒尔的骚动。警方随即发起了一场针对工会的抹黑行动,称其为“毛主义”,政界人士明确表示支持日本资本。最终,无人被重新雇用,13名工人被判无期徒刑。 “整个审判就是一场闹剧,因为结果早就预定好了,”人民民主权利联盟(PUDR)在对判决的批评中总结道。 “主要的意图是通过给予他们最严厉的惩罚来驯服活跃的工会成员。”

虽然故事以残酷的失败告终,但《工厂》在一场将劳工和公民社会团结在一起的斗争中找到了一丝希望。而《机器》提供的则是一幅全然黯淡的图景。这部70分钟的纪录片发生在古吉拉特邦萨钦的一家血汗工厂,那里没有任何安全标准或操作规定。贾因像侦探审视犯罪现场一样,在极度肮脏、灯光昏暗的空间内巡视,偶尔会停下来进行紧张的采访。摄影机大部分时候都在移动,仿佛无法忍受在任何一幅图景停留太久,不过它总是时不时地晃到一个画面——一个青少年灵活地折叠着那些从织布机中源源不断吐出的带有图案的织物——似乎被它无法解释的美丽所震撼。
工厂的轮班时间为12小时,工资为210卢比(约合4美元)。大多数人是来自北方邦、被困在奴工制度中的移民;这里还有童工,业主甚至没有隐瞒这一点。工人们看起来像是来自地狱的生物,强壮、消瘦,赤着脚,衣衫褴褛——纺织厂何苦要为制服买单?他们看上去全都精疲力尽,赤手空拳地操作着织布机,如果不是在拖拽大量的布料和染料,就是在生产线上打盹。 “神给了我们双手,所以我们必须工作,”这是电影的第一句话。 “有些工作需要体力,有些需要头脑……在这里,我两者都需要,否则就有可能断腿断手。”除了使用电力的织布机,这里没有一丝现代科技的影子,甚至连个坡道都没有。天花板上似乎有一个洞:下雨时水会从中倾泻而出。
在没有正式组织架构的情况下,移民们只能任由他们的承包商摆布。他们必须接受这种状况。“没有人在剥削我,”一名男子说,“剥削意味着我是被迫在这里工作的。” 一位更年长的雇工坐在户外似乎是一堆矿渣的地方,用令人吃惊的充满激情的演讲呼吁团结:“工人现在是羔羊,但他们可以成为狮子。” 但他也承认成立工会不太可能:“当工人联合起来时,领头的人通常会被杀。”
《机器》以一个充满张力的片段结束,其中一些工人在质问贾因为什么要拍摄他们的痛苦。一个男人甚至拿出手机反过来拍摄导演。如果说这是对艺术的怀疑的坦白,它其实也同样指向了这部电影的核心伦理——这也是罗伊以及蒙泰罗和贾雅桑卡的纪录片所共享的——影片纳入了工人的视角,这是主流媒体显然没有做到的:他们陷入债务循环,被繁重的工作折磨得筋疲力尽,对体面生活的希望几乎彻底破灭。他们用一种锐利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回视这样的目光绝非易事。
文/ 拉蒂克·阿索坎
译/ 卞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