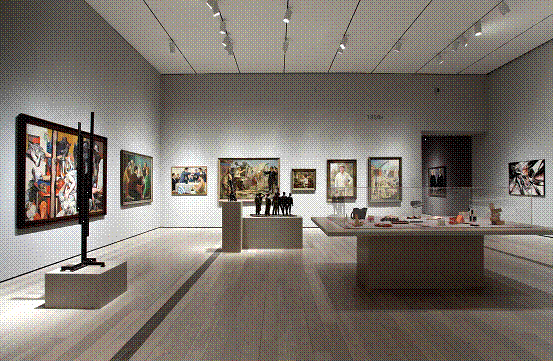
时至今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已六十周年了,而柏林墙的倒塌也恰好有二十年,西方世界还在为社会主义德国的崩溃而幸灾乐祸着,在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里,斯特凡妮•拜伦(Stephanie Barron)和艾卡特•吉伦(Eckhart Gillen)在洛杉矶艺术博物馆组织了一场重要的展览《两个德国的艺术/冷战文化》,此次展览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契机,将一直盘旋在德国不同土地上的两种民主战后史重新纳入了思考体系之中。
《两个德国的艺术》展示了1945年到1989年期间分裂的德国两种几乎完全相反的文化创作态势,它试图史诗般(有时看来不免有些愚蠢)地呈现出一种具有平衡性的记录。当对灾难与悲剧进行追踪溯源时,平衡就成为最难以处理的一种手法。博物馆现代艺术的首席策展人拜伦在这方面则一直有屡有佳绩:当前的展览,可以说是她的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第一部是1991年的《衰落的艺术:纳粹德国先锋的命运》,这场展览是对1937年慕尼黑“Entartete Kunst”展览的重构;接着是1997年的《流亡与迁移:从希特勒开始的艺术家的外逃》,两场展览都在洛杉矶艺术博物馆举行,而且和眼下的展览一样,画册的内容都非常详尽且相当有用(最新的这个是与萨拜因•艾克曼(Sabine Eckmann圣路易斯Mildred Lane Kemper艺术博物馆馆长))一起合作完成的,这些画册,对于任何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来说,都是非常有效的参考资料。
1997年,吉伦组织的《德国影像:一个分裂的国家的艺术》在柏林的Martin-Gropius-Bau博物馆举办,它探索的很多领域与当下的这场展览非常相似。当时,社会主义、苏联以及它的社会主义同盟们,依然栩栩如生地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更甚的是,这座城市在1933年到1945年期间,曾是纳粹帝国的首都,此后相继又被分成了两部分(实际上是四部分);这里在德国被盟军从自己的法西斯主义解救出来之后, 成为了新建的社会主义德国的首都,而另一半则在美英法的介入中,被瓜分成三部分,在苟延残喘中偷生。12年后,在全球的文化大都会洛杉矶,举办了又一场类似的展览,使得我们得以从另一个优越的角度去看待这两个德国充满宿命感的历史,它以对涡轮式资本主义全球性的生态破坏快速扩张的意识(这次并不是幸灾乐祸),目睹了传统定义下资本主义经济的近乎全线的崩溃。
从这个角度而言,意识到民族-国家文化的常规概念正日益变得互不相干,对于那个形成了二十世纪两场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民族—国家的战后经验的思考将不再具有同样的历史吸引力—除非它作为一种必要的提醒,提醒人们二十世纪的文化似乎恒久地被看作是一种从整体化的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经济的野蛮中的分离出来的全然解脱。《两个德国的艺术》不得不令观众直面作为野蛮记录的文化文献这一著名的辩证法,而且随着社会史和情景主义艺术史的升温,观众不得不面对一种令艺术史学家和他们的方法论都感到迷惑的矛盾:艺术作品最初是历史的产物(如,一份文献记录)还是艺术生产与接纳的自留地呢?如果有规则可循,它是否从头到尾都遵循某种规则呢?对于展览的策展团队而言,这种方法论上的矛盾似乎并不是一个问题。假设我们认为,作为记录文献的艺术作品的那种说教性的两极化原则是策展人故意而为之的运作方法。那么是否有人会觉得,为了给大家一个清晰的艺术脉络,组织一场三四十年代的法国艺术展就要展出杜菲(Dufy), 弗莱曼克(Vlaminck), 基斯林(Kisling), 富热隆(Fougeron),马约尔(Maillol)和德斯比欧(Despiau)的数件作品外加混合一些毕加索、马蒂斯和贾珂梅蒂的作品呢?如此说来,回到伤痕累累的两个德国上,国家文化上的这种病态表明采取这种呈现方式实则是很有必要的。
策展团队决定给所有种类的表达同样的分量和展示机会,而不考虑他们的优缺点和艺术上的相关性原则。结果呢,在展览的第二展厅里,就看到了赫曼•克罗克纳(Hermann Glöckner)全部的雕塑作品(这也是吉伦对斯大林主义的东德隐秘文化的一次精彩的再发现),与此相衬托的是大量的东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平庸的绘画。再或者,人们在扫过了一堆二三流的绘画后,又在某个僻静处看到了汉纳•道波温(Hanne Darboven)的一件小而优秀的作品。这其中既有约尔格•伊门道夫(Jörg Immendorff),马库斯•吕佩尔兹(Markus Lüpertz) 和乔治•巴塞利兹(Georg Baselitz)夸张的绘画,又有所谓的德国记忆文化的底层人士如鲁茨•丹贝克(Lutz Dammbeck)的作品,后者认为将巴德尔和迈因霍夫群体的图片和阿诺•布雷克(Arno Breker)的雕塑头像结合在一起是个很聪明的做法,很显然是希冀同时从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和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身上获得庇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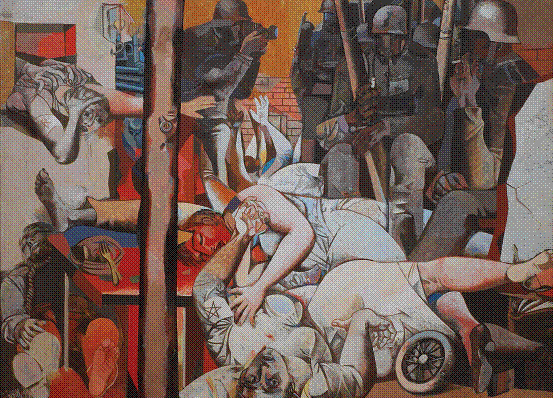
当艺术作品被缩减为记录文献时,这种缩减只在一种高度压缩的装置下才放大起来,此刻,任何一件作品很难获得充分的空间将自身展示出来(在楼上溜达,会发现昆斯的作品所占的空间是那么广阔,而德国历史所占的空间却是如此局促,这种对比不免令人痛心。很显然,博物馆的行政人员知道谁和什么是值得占有充足的空间的)。
最严重的问题是,对于审美评判的失败转为伦理上的一种不公平,如艺术家克罗克纳, 毫无疑问,他不顾一切去追求自己的作品,如今却又重新出现在一群机会主义者当中,这群机会主义者通过谄媚一个专制的政权从而获得一切他们想要的东西。在地区性的政客中间,最糟糕的例子当属西特(Sitte),德国社会主义文化最被官方所承认的旗手,原因是因为他在艺术上“更具有成就”。在关于Lidice大屠杀道德愤慨的理由下,西特创作了最具毕加索作风的作品《大屠杀II》(1959), 但当时几乎少有人知道这部作品是偷师毕加索的,因为三四十年代毕加索的作品,比如《格尔尼卡》(1937),以及《教堂骸骨》(1944-45),当时的东德只有极少数特权阶层的人才知道这些作品,这些人控制着西方绘画的流向。对于西特和这次展览的很多艺术家而言,这种偏狭的蒙蔽成为艺术上愤怒的源头。
战后两个德国最痛苦的情势是法西斯历史对民众的压抑以及人们集体对大屠杀的否定(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德国更为明显,那里,虚假地,申明自身是纯洁的反法西斯群体)。1968年前,这种情势不仅形成并且控制着德国人集体的社会政治心理,而且也控制着电线水泥墙两边的文化组织和官员们。无论是试图构建出一脉不受污染的德国文化世系的(从1912年康定斯基的抽象表现主义到1959年西德对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疯狂谄媚)威尔•格罗曼(Will Grohmann), 阿诺德•波德(Arnold Bode),维纳•霍夫曼(Werner Haftmann),还是肩扛Zhdanovian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重任要求将从阿尔特多菲尔(Altdorfer)到克拉纳赫(Cranach)的德国现实主义绘画传统继续发扬下去的那些领头军们,在两个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里,可以说处处是充满了欺骗性的阴谋诡计。
在西德重建历史的掩盖下,魏玛德国真正重要的人物和实践对于那些参加过文献一文献二的热切的民众们而言则是一无所知的,尽管他们希望以现代主义重新建立起连接。事实是是德国人自己将魏玛文化最伟大的人物逐出了他们的国土。魏玛德国,苏联先锋和法国超现实主义,产生了二十世纪最为伟大的摄影文化,而这一事实则被新艺术史和文献展所忽略。可以说,魏玛在对图片蒙太奇美学的发明中,对立体主义拼贴画进行了最为优质的再定义。植根于男性主题的绘画“表达”中的笨拙的视觉文化概念长期以来都在包豪斯和它的项目的觉醒中以及柯特•施维特斯(Kurt Schwitters)的单一成就中被省略掉。
有种误解,认为1919年之后,绘画是德国很重要的一种艺术,并且在1949年之后重生,这种看法在吉伦的“Deutschlandbilder”(略掉了魏玛时期的摄影创作,除了哈特菲尔德Heartfield的外)和拜伦的《流亡和迁移》中(在这场展览中,没有提到一个魏玛时代的摄影师)都很明显。在《两个德国》这场展览中,很明显的一个省略就是哈特菲尔德的战后作品,当好多战前画家的战后作品都被展出时,他的战后作品则完全从展览中被剔除了。令人费解的是,战前和战后德国时期一位真正优秀的画家布鲁诺•高勒(Bruno Goller), 即康拉德•克拉菲克(Konrad Klapheck)和布林奇•巴勒莫(Blinky Palermo)在Kunstakademie Düsseldorf的第一位老师,他的作品在展览中也无迹可寻。且不管上述的这些保留吧,我们还是在第一展厅看到了一组非常令人动容的作品回顾:社会主义画家汉斯•格朗迪格(Hans Grundig)(刚从Sachsenhausen返回,后来在Dresden艺术学院任教)纪念集中营牺牲者的油画,威纳•黑尔特(Werner Heldt)令人目瞪口呆的作品,弗里兹•温特(Fritz Winter)(在战后的卡塞尔及时成为了汉斯•哈克的老师)令人赞赏的神秘的抽象水墨画,在展览中都可以看得到。而 詹尼•玛梅(Jeanne Mammen)的Tür zum Nichts(ca. 1945)也仍然令人感动。这些作品都是展览中的亮点。虽然在相同的第一间展厅里,出现了理查德•皮特(Richard Peter)关于德累斯顿爆炸的纪实摄影,但很明显,从一开始,对战后文化中绘画的中心性的误解就在展览中起了关键作用。结果,在接下来的展厅里,出现了数目不均衡的、大量的不加选择的绘画,也对战后德国艺术实际上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形成了一种危险的假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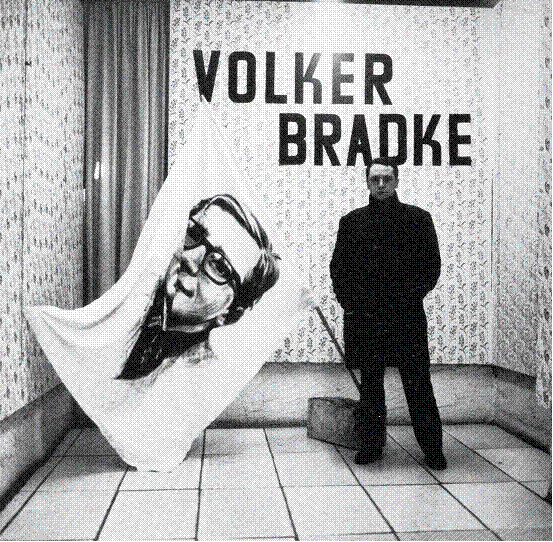
展览的“纪实”手段所引起的一个更甚的后果是决定具体艺术作品创作的艺术和政治斗争因为考虑到纪实所虚构出来的中立性而被抹掉了。策展人不仅将柏林墙两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的东西德艺术宗谱弄混弄乱,而且以同样无动于衷的曲解,采用了纪实手法,在西德那些成就瞩目和那些相对来说毫无建树的艺术家之间建立了一种天真的平等。迪亚特•罗斯(Dieter Roth)那些很棒的作品如Literaturwurst (Martin Walser: “Halbzeit”),1968,和他的《巧克力狮子塔》(1969/1993)不得不和海因茨•马克(Heinz Mack)的一件光学艺术的大型装置《浮雕墙》(ca. 1960)挤在了一起。
从六十年代开始,杜塞尔多夫的零度组织(Zero Group)的美学议题,既是衍生而出的,又毫无诚意,这一点众所周知。他们对历史真实性的唯一诉求是将德国在“零时”的假定性的新开始和他们自身对近代德国史的零度批评性反应和纪念平等化。很明显,他们缺少卢西奥•方塔纳、伊夫•克莱因更别说皮耶罗•曼佐尼的激进决绝了,零度组织将他们被压制的动觉呈现给新玩意的收藏家和莱茵河-鲁尔河(Rhine-Ruhr)工业区技术奇观的可能性支持者。在那个展厅之前,一些伟大的画作似乎是随意放进去的一样,它们的出现将观众从德国早期的“经济奇迹”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其中包括两副来自杜塞尔多夫画家康拉德•克拉菲克(Konrad Klapheck)五十年代末期的画作,这位艺术家再三地被忽视过。零度组织表演着他们的庆典,标志着莱茵河畔盛况的到来,克拉菲克描绘了一种完全另类的机械化图景:诠释了一种在国家集体水准之从日常平庸到正常化的奇特过渡和永久性的转变。
约瑟夫•博伊斯演绎了自身对祖国失败的思考,并且以具有后见之明的纪念式作品,对牺牲者们、整个国家民族以及其中的参与者们从这种失败中所承受的遭遇进行了纪念性的反思。当然,博伊斯的作品也在其中展出。他的三件中等尺寸也毫无关联的作品,随意地被放在类似走廊的一个空间里,很难令人想到他是欧洲后清洗时期的首位艺术家这一身份。不熟悉博伊斯最重要的追随者的作品的人们,将不会从两件随意选出来的布面油画中,去理解布林奇•巴勒莫(Blinky Palermo)在重构德国抽象艺术的遗产中所做的突破以及所承受的打击。
去了西德的前东德艺术家的早期作品,比如里希特和西格玛•珀尔克(Sigmar Polke), 也许会引起对两个德国创作美学上的无序的震惊,而某些作品展览空间的亏放和某些平庸作品的过量则相对地形成了碰撞。里希特的经典作品《鲁迪叔叔》(1965),是艺术家首创的一件逼真的记忆性作品,它在随后的十年里被整整一代学子们所追随。就是这么一件小小的、灰暗的、看上去很简单的作品,实际上却引起了战后德国艺术在认识论上的转变。 把这件作品塞进一面墙上一排张着大嘴、色彩亮丽的新表现主义的杂乱之中,足可以看出策展人对这件作品态度上的模棱两可。同样,珀尔克的《马铃薯屋》(1967),很清晰地体现了德国对过去的否定从悲剧到闹剧的转变,这件作品在贫穷艺术的高峰期和美国最好的后极简主义雕塑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但在此它却并未受到公正对待,不得不和别的作品拥挤不堪地凑在一起,阐述一个似乎真实的德国资本主义现实。它并不是作为一件诞生于德国的神圣的浪漫主义讽刺作品而被呈现出来,在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杯多余的残羹冷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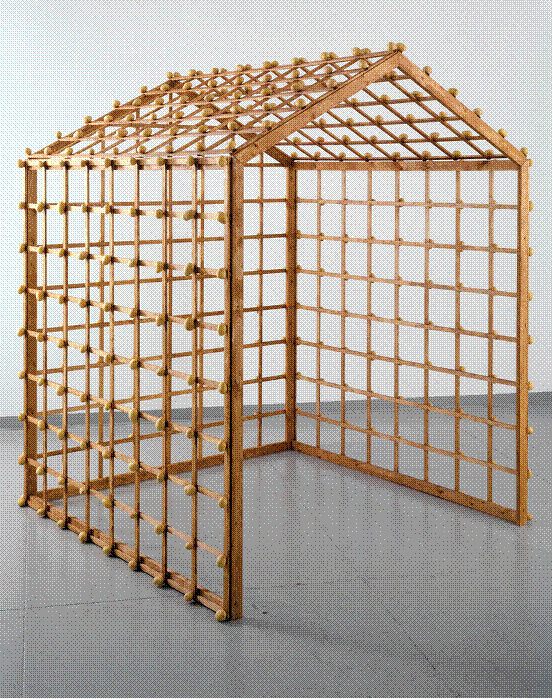
伊门道夫(Immendorff), 潘克(A. R. Penck), 基弗(Kiefer), 吕佩尔兹(Lüpertz)和巴塞里兹(Baselitz)的作品在展览中可谓来势汹汹,几乎占据了每个房间,又似乎重现在每一个可能性的议题构成中。以上这些艺术家都被同一家商业画廊代理,这势必令人感到不适,人们不禁怀疑他们的无处不在就是试图要挽救那些声誉在二十年前达到顶峰的画家们日渐式微的霸权地位。这种不平衡性,也许是因为展览的一位重要的领军人物迈可•韦纳(Michael Werner),不仅在历史准确度上,还包括相关的艺术成就上,打造了一场令人无法接受的历史曲解,最终在一些方面降低了展览的水准。毕竟,这些艺术家在《两个德国》展览中的绝对统领地位只能将天真而无知的新新观众误导。
最过分的不公体现在汉纳•道波温(Hanne Darboven)作品上,她是60年代以来西德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但展览却只拿出了她的一件作品《1983年》,被放在室内一个边墙上,几乎看不到,和汉斯•哈克(Hans Haacke)被公认的具有纪念意义却多少令人感到审美疲劳的《油画,向Marcel Broodthaers致敬》(1982)放在一起。哈克当然也被忽略了。展出的唯一一件哈克的作品,很显然是为了肖像主题而选择的,却几乎很难体现出在过去四十年里,哈克持续的创作力所突出的复杂性和激进性,以及他在面对美国式的虚伪和德国的拒绝中所表现出来的无情鞭笞,其实,德国文化传统中具有分析力的明晰性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同样荒谬的歪曲是希拉•贝歇(Hilla Becher)和她的已故丈夫贝恩德(Bernd)作品的劣质展示。贝歇夫妇不仅是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教师,同时也是六十年代末期观念主义艺术在国际上形成时的重要参与者,如今也都获得了广泛认可。展览中,策展人将贝歇夫妇的少量的一些摄影作品硬塞进了一面拥挤的墙上,这样做的结果是抹掉了贝歇夫妇在德国文化重建上所做的重要贡献。毕竟,这对夫妇不仅将战后德国重新介绍给了魏玛的摄影文化,同时也为德国和欧洲的观念主义时间的后绘画美学奠定了基础。
当面对它在《两个德国》的展览中的缺席或表现不足时,更紧迫的理由,则并非仅仅是勾起观念艺术激进的国际主义的乡愁在作祟。(我个人宁愿想起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 和贝歇夫妇之间的交流和友谊,而不是1989年之前穿越柏林墙潘克和伊门道夫之间因盲目的爱国主义纽带所形成的阶段性沟通。)如果说,历史是我们试图从中苏醒的噩梦,那么,它就是这种民族-国家的身份主义政治,这场展览关于二十世纪最恐怖的噩梦所带来的文化上的影响给我们的提醒——不可避免的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处,国家被蒙蔽的能量总是会日渐失控。无论这种身份主义议程是围绕着种族、宗教还是意识形态的概念,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现在总是再而三地发生着,它们作为政治掩饰,主张的都是民族-国家所强加的有差别性的分裂。
但是,想象一下在同一性上的文化创作,就如这场展览所做的那样,不得不说,这是一场迥异却又令人担忧的运作。它使得民族-国家的概念在文化创作中瓦解,尽管我们也许会怀疑这是策展团队们的用意所在。但它也告诉我们(也许只是暗示)先锋们(从达达到构成主义到激流派和观念主义)激进的国际主义,与他们构建后传统和后民族身份的意图,如今已经成为过去。我们面临的是一种全球化的艺术创作,它是与齐整统一的文化奇观前后相继的,其最初的野心是将主体具体化的所有形式以及做为记忆性领地的历史形成的文化创作常规的所有表达都进行彻底的去分化和摧毁。
《两个德国的艺术/冷战文化》由洛杉矶艺术博物馆组织,9月6日之前在德国纽伦堡的日耳曼民族博物馆可以看到;10月3日到2010年1月10日期间在柏林的历史博物馆可以看到。
作者本杰明•布赫洛(Benjamin H. D. Buchloh)是哈佛大学现代艺术梅隆学者教授。
文/ 本杰明•布赫洛 | Benjamin H. D. Buchloh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