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郁葱葱的棕榈树,陪衬着白色的柱廊,美丽的海景尽在眼前。古典主义的气息尽在其中,这里曾是Padiglione Italia (新命名为“展览宫”)的正门,而约翰•巴尔代萨里(John Baldessari)的作品,真是起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不禁令人想起威尼斯海滩。在丹尼尔•伯恩鲍姆(Daniel Birnbaum)超越于现代主义一度占据主导的范式上(批评性的参与,表达,不夸张,自我投射)的展览中,占主导性的概念是移位,规划预测,比喻表达法,吸收,可以说,这位老牌洛杉矶艺术家的作品(《海洋和天空》,2009),成为了大展绝佳的开门之作。
在随后的策展策略的宣言中,伯恩鲍姆否认了任何想为五十三届威尼斯双年展进行总体规划的要求。“制造世界”这一短语,言下之意表示它每次诠释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伯恩鲍姆当然知晓这一点,他明白在对大量的概念变调的证据下,每个艺术家都能通过他/她的创作形成独特的视角。在多重的平台下,没有多余的主体性或意识形态性前提得以诠释,尽管在双年展和博物馆展之间,他划出了明显的界限。由此产生的结果,如他在画册的文章《我们是很多》的题目所暗示的那样,与莱布尼茨(Leibnizian)单分体的聚合很是接近——不同的个体聚合在一起,多重多样,而不是在一个议题下群展所支撑的同类的集体性聚合。在画册的其它文章中,伯恩鲍姆质疑了文化理论学家萨拉•马哈拉吉(Sarat Maharaj)关于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的科学性哲学,他认为它们与当代艺术创作是有些关联的。对于费耶阿本德而言,科学探索的哲学性并不是对一种合理而广泛的方法应用,而是在过程中具有“偶然性,开放性,随意性,补缀性”的,通过对“推测的模式”的“未做准备的探索”而前进。言外之意是—-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为想要探索伯恩鲍姆展览的观众们提供了极佳的指示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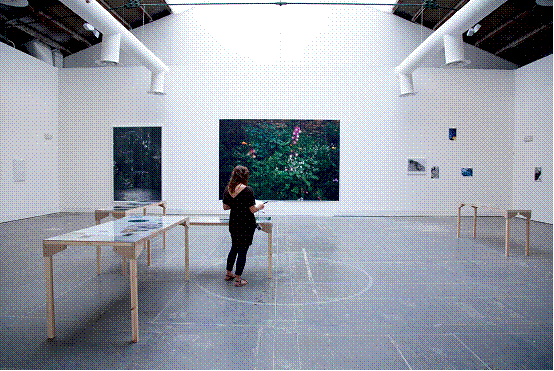
也许是偶然所致吧,展览宫错综复杂的展厅分布,更加重了策展人的这种策略,这里的房间,从大到小,有三角形的,也有别的奇形怪状的。空间的混乱很不适合刻意的规划,而这种特征恰好符合了伯恩鲍姆的想法。与任何以决定性的主题为基础的项目相对立,平面布置图形成了一种偶得的内在关系,无法预料到的关联性,散乱无章的并置,观众们不时发现他们重新走过已走的路,前后回转,在放映录像和影片的黝黑房间里迷途,陷入死胡同时,只好撤回来。策展策略引导着一些大型空间的安排,菲利普•帕雷诺(Philippe Parreno)的投射影片《某个事物的梦》与布林奇•帕勒莫(Blinky Palermo), 安德烈•卡德尔(André Cadere),沃夫冈•提尔曼(Wolfgang Tillmans)的作品谢丽•利文(Sherrie Levine)的一组单色油画放在了一起。它拒绝形式上的关联,而这种策展方案看起来既独断又孤注一掷,
在这座建筑的顶端,接近中心的某处,是作品充盈的、亮堂堂的展厅。之前,这片夹楼展出的是已故艺术家的作品;而这次是留给了一位在世的艺术家沃夫冈•提尔曼。展出的作品包括他广泛创作实践的图片,从单色画到描述随意的家庭场景的私密图,以及一些展台,这组中的《开普勒/威尼斯圆桌》(2009),里面有一篇来自三月三号《纽约时报》的关于天文学的文章,标题是《孤独的宇宙:对与我们的世界相似的世界的探索》。他自己的实践中拟想出来的世界既复杂又具有多面性,从微观和本土到抽象和广泛,从摄影技术的具体的技巧性到解惑的通俗性和拍照的看似自发的方式和表现性,都在探讨之中。提尔曼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对年轻的艺术家和观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伯恩鲍姆认为:他对于“当前的社会背景”的介入,他对于“创新性而激进的个体生活风格和一种不同的社会秩序下(或者说一种在一起的乌托邦理想)的新的性政治”的坚持,他将双眼作为“破坏性的工具”来质疑社会前景,伯恩鲍姆认为这是真正作用于艺术的“政治概念”。虽然很严肃地引用了《纽约时报》的文章,但标题的调调则较为轻松活泼,富于幽默,这正是关键所在。伯恩鲍姆的策划的其它展览中的作品,也避免了危机重重的沉重言辞。

也许大伙还不是很习惯没有指示的方式,来到展览大厦的观众们,经常是手持地图,试图找出他们所处的位置,或者想看还有哪里自己没有去到。在军械库的Corderie,观众们不得不沿着一条未离正道的路线行走,这个棚子原先是用来做绳子的。因出乎意料的状况较少,这一部分的展览和伯恩鲍姆探索性的方法论有些偏差。在利吉亚•培普(Lygia Pape)2002年的作品《Tteia I,C》 金线装置令黑色空间一亮,军械库凹凸的空间充满了环境式的、表面布景的、类似建筑的作品。与Baldessari式的闲散无序不同,每件作品似乎都是有各自运转的轨道,姆沙科瓦•兰格(Moshekwa Langa), 乌拉•冯•伯兰登堡(Ulla von Brandenburg), 保罗陈(Paul Chan), 卡斯顿•霍勒(Carsten Höller), 杨海固(Haegue Yang)这些人的作品皆是如此。军械库所有装置中高超的职业精神和技艺是史无前例的。
在军械库和罗马展览大厦的展出中,有很多是年长一代的艺术家:卡德尔, 托尼•康拉德(Tony Conrad),尤娜•弗莱德曼(Yona Friedman), 琼•乔娜思(Joan Jonas), 戈登马塔-克拉克(Gordon Matta-Clark), 帕勒莫, 培普的作品都在此展示。尽管他们创作实践不同,但共同之处是创作美学中的伦理特点,一种经济而低调的创作方式将他们的作品置于了边缘地带,而非市场的中心和学院派认可的焦点之中。他们通常最先被同辈艺术家所承认,而非主流的渠道,很多人后来成为了年轻一代的目标,尤其是那些创作上跨越行为、装置和其它观念性创作模式的艺术家们。这种即兴的精神很贴近伯恩鲍姆的所愿,也点燃了他们的创作激情,而作品累积的影响又赋予了展览以庄重性。像乔娜思的《阅读但丁II》(2009)和康拉德在军械库的个人行为《Snapping the Drone》(2009)成为展览中最值得纪念的时刻之一。
本届双年展的推广词强调的是年轻,尤其是伯恩鲍姆还是双年展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监。作为美术学院的院长,他是欧洲最活跃的艺术院校的领头人,这一机构在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的创作实验上开创了先河。但伯恩鲍姆几乎并没有指出,未来的一代将何去何从。与伯恩鲍姆同代的艺术家们如瑞秋哈瑞森(Rachel Harrison)到瑞秋•科多瑞(Rachel Khedoori), 西蒙•斯塔林(Simon Starling)到多米尼克•贡扎雷斯•福斯特(Dominique Gonzalez-Foerster),他们都出现在此,与这些人同时出现的还有其他年龄和背景不同的艺术家们,其中不乏一些近期备受瞩目的人士。在展览大厦前厅的三个展厅里,盖顿/沃克(Guyton/Walker),托马斯•萨拉西诺(Tomás Saraceno), 以及娜塔莉•余伯格(Nathalie Djurberg)的作品占据了显赫的位置。虽然它们很显眼,但是奇怪的是,产生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尽管在无经验和未尝试中,余伯格和萨拉西诺不免落入这种语境鼓励下的浮夸之中,而经证实,盖登/沃克(Guyton/Walker)就是其中的搅局者。
制造世界几乎成为了国家馆的艺术家们的命运,无论这些场所是在绿园之内还是之外。每个国家选择自己的代表艺术家,根据的是自身的一套协议和礼节,在更大的努力下将自发的参赛作品融入到一起的努力,在面对专制控制,尤其是引导每个国家的策展日程的文化政治时,通常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文化行政者们所关注的通常与本土化而非全球化议题有关, 展现的作品看上去也都具有本地化特征;还有一些则忽略了双年展的大平台所提供的参与当代性议题的可能性,因此产生了一种共同的语境和具有成效性的对话。例如,今年法国和澳大利亚选择的参展作品,几乎完全离谱;德国,丹麦,北欧国家也是令人始料未及:德国邀请的利亚姆•吉利克(Liam Gillick), 一位英国出生的美国居民;斯堪的纳维亚的Elmgreen & Dragset围绕着北欧和丹麦展馆打造了一个“跨民族的展示”,涉及了一系列的国际艺术家。

令人未曾预料的是,从国家馆开始,一个共同的主题开始得以出现,那就是对所在场所的介入干涉,淡季的绿园对此产生了影响。这一主题为迈奎因,多芮特•玛格丽特(Dorit Margreiter),罗曼•翁达克(Roman Ondák), Yang,Elmgreen & Dragset的作品提供了跳板。这些作品植根于一系列与所在地相关的具体中,虽然在某些时刻有些迷失或疏离。玛格丽特的黑白影片《展馆》(2009),是向约瑟夫•霍夫曼(Josef Hoffman)优雅的建筑致敬,作品刻画了这座位置偏僻的经典建筑之作,从而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尽管它与霍夫曼的纯粹主义式现代主义空间有着小心翼翼的关联,但玛格丽特的作品,则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附属品,充其量不过是个雅致的诠释,最差也不过是个寄生于其中的终结曲。通过慢节奏的镜头和萦绕其间的声音,产生了忧伤的冥想,迈奎因的影片《绿园》(2009),开始是深入了这片凄凉的公园中的植物群,带着哀伤的色调。结尾,影片跳入了一个更为正常的叙事体系中,从暗处出现的两个主人公以隐秘的姿态相互拥抱,改变了影片的整个调子。大自然的世界在主人公和背景之间迂回,一种不可分解的张力随之而来,成为了作品的真正主题。翁达克也是对绿园的植被感到迷恋,所以把它放入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展馆中。本土的植物群溶入其中,天衣无缝,展馆则变成了闯入者,成为了暂时停滞在田野地上的进入者。翁达克破坏了将自然和文化连在一起的正常化关系,巧妙突出了展览的功能、历史渊源、装饰的随意性,以及文化旅游固有的消费性。
美国馆策展人卡洛斯在《布鲁斯•瑙曼:拓扑的花园》文中,详述了绿园演变中的一些关键的时刻。他认为,从一开始(1805-14),绿园就是这个城市中不那么重要的附属物而已,直到1895年双年展开始,人们才意识到它的作品用,可用来做展览。即使是现在,对于它的存在—-尤其是艺术展之间的漫长的间隔时间中—-这里依然保持着一种散淡沉闷的气质,那粗糙而毫不吸引人的外观,令游客们望而却步。这种疏离感却促进了年轻一代的艺术家的创作,双年展似乎与推动威尼斯经济给这里增添活力的游客们无关,而年轻的艺术家努力为这样的活动进行一些有意义的贡献。受到这一点启迪的当属福斯特的录像作品De Novo, 2009, 她将二十多年来进行展览的五个不同场所融在一起。在各种变化中,作品忧伤而令人难以忘怀,最后以一座遥远而废弃的花园收尾。这个看上去美丽的场所,艺术家本人似乎没有对其进行任何干扰,进入了一个遗世独立的世界,远离了大多数观众们所时常光临的场所。
绿园(Giardini)非常拥挤,这里布满了历史性的展馆,所以几乎不可能再在此打造新馆了:新来者必须去外边临时安置下来。在十六世纪颓废的Palazzo Rota Ivancich,墨西哥推出的是特蕾莎•玛格勒斯(Teresa Margolles)粗粝而摄人的装置《我们还能谈什么呢?》。作品是一些浸染了血液和其他与药物死亡有关的体液的布,另外还有一面旗帜《Bandera》(2009),同样也沾满了血,挂在了正门上。展览的意义具有双重性:对于艺术家的同胞而言,法律和秩序的暴力日益失去控制与合法性的状态给他们的精神造成了创伤;而对双年展、组织者、参加者和观众而言,意义更为宽泛、明显。这样一个政府,他支持的项目是一个对本身政权和信誉度提出质疑、破坏其国外形象、影响国家市场、文化交流和旅游业的项目,虽然这件装置的某些方面过于刻板,缺少想象的余地,但是玛格勒斯的作品与所在的场地的结构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它不仅破坏了身处的环境,而且也触动了那些经验最丰富、也最随意的观众们的无动于衷的心境。玛格勒斯的作品留下来的物质痕迹是无法被完全抹除掉的:在名为《清洁》(2009)的日常行为中,水冲洗了被血液浸染的大厦的地板;风雨过后,旗子又将血滤出,渗进了下面的街道和运河里。这种记忆的痕迹难以消除,每个来到这里的参观者,都会被它所留下的鬼魅可怖而吞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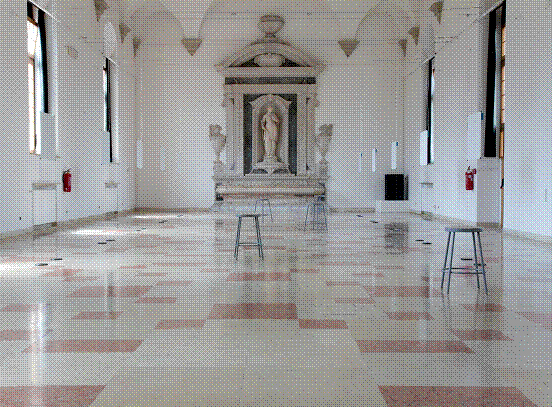
玛格勒斯的项目过于依赖了它所处的空间,它暗度陈仓般地与绿园的地理和心理距离进行了交换。她的问题是对官方论述的规则进行了戏谑。而《拓扑的花园》的组织者则完全不同,他们将作品从美国馆延伸到靠近城市历史中心的其它两个地方。围绕着三条明显的线索—-顶端与分支,声音与空间,喷泉和霓虹,这一回顾展跨越了瑙曼职业生涯的四十年。
由于每个空间都囊括了这位新墨西哥艺术家每一时期的创作,也是代表了组织的三方,展览给人的感觉是为了适应一系列有限空间而举办的博物馆展。在Ca’Foscari, 声音从一个房间窜到另一个房间,干扰着里面的雕塑作品。在Iuav, 三频录像《世界末日》(1996)是少有的抒情作品,三个艺术家演奏着吉他,几乎与旁边的作品毫无关联,巧妙地超越了学院式的疆界。《紫色和黄色的灯照走廊》(1972)将其连在一起,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期的声音作品传出“走出我的脑海 走出这间房屋”的旋律,看不见的声音从某处传来,向前递进,跳跃,回旋,就在近处,但却无法触摸。在美国馆,华美的再造之《Vices and Virtues》,(1983-88/2009), 周围打造得都很精美。
瑙曼是如今最受尊崇、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他被选为美国馆的代表,引起了巨大的关注。新的作品《Days》(2009)和《Giorni》(2009),为双年展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伯恩鲍姆无结构的策展策略,和依赖于形式化规则和协议的活动类型很不一致。
如很多国家水平的活动一样,双年展是以一系列共同的指导路线和不言自明的规则契约和习俗为前提的。瑙曼的能力是驾驭于任何游戏规则之上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为什么美国馆的委托人觉得有必要通过扩大美国作品的展览范围而改变威尼斯的场地呢?
根据画册作者们的看法,只有扩大美国馆的范围,瑙曼的作品才能充分地与威尼斯的公共和私人空间产生互动。而且,巴斯瓦多写道,“只有使观众通过运用自己对这个城市的体验,与瑙曼的作品联系在一起,展览才能对形成它的国家馆的意识根基进行挑战。”在批评构建双年展政治根基的意识形态驱动下的策展手法中,采用瑙曼艺术的愿望是具有讽刺性的,至少就是这样。在文本的别处,巴斯瓦多表示,美国的前两次参展作品都超越了国家馆的范围。而在这两次中,艺术家都获得了大奖:一是1964年的劳森伯格,一是1990年的珍妮•霍尔泽(Jenny Holzer)。似乎是对美国文化实力的回应,今年的评委们又将金狮奖颁给了美国馆。在国际和国内水平上,文化政治对马格勒斯的项目很重要,因为她那明显的主题发挥了作用。虽然是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但某些相似的状况似乎也影响了美国馆的事项。
权力是文化政治特有的表征从来都不是藏在这一大展和很多其他双年展的表面下;瑙曼作品对于当今创作的针对性也并不在讨论之中。他的全部作品的宽泛性跨越了当代艺术所围绕的两个标杆:一种是通常以唯我论和内在性构建的推测性模式(如《真正的艺术家通过展现神秘真相而帮助世界》);一种是在心理上和生理上充满威胁性的立场态度,如《南美三角》(1981)。伯恩鲍姆温和的双年展忠于了这样的方向,在威尼斯淡季的雾气和海岸线的明媚之间,迂回前行。第五十三届威尼斯国际双年展没有冒险介入的——-是更为激进的创作模式以及结构和精神上呈集体主义的世界。
林•库克 (Lynne Cooke )是西班牙马德里索菲亚艺术中心的首席策展人,副总监。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