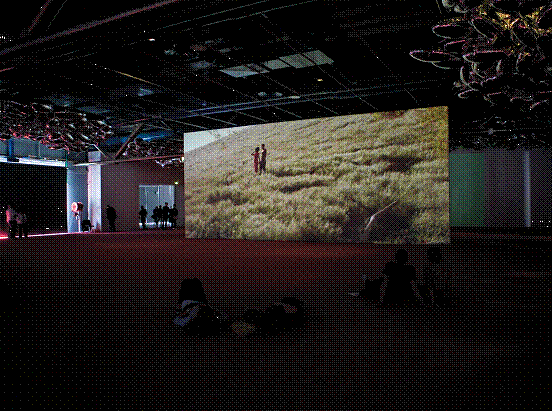
《菲利普•帕雷诺》2009展览现场、蓬皮杜艺术中心、巴黎。顶部:《言语泡泡》、2009。地面:《1977年1月31日》、2009。投影:《1968年6月8日》、2009。
菲利普•帕雷诺
有机玻璃制成的大天蓬,霓虹,一排排闪闪发光的灯泡——一般只有在影剧院入口处才能看到的陈设——宣告了蓬皮杜艺术中心菲利普•帕雷诺(Philippe Parreno)回顾展正式开始。从《遮檐》(Marquee, 2009)(该系列从2006年开始制作,这次展出的是其中最新的作品)底下通过后,观众才算真正进入巨大空旷的展览空间。但如果《遮檐》直接援引电影或电影图像作为解读帕雷诺作品的关键,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也不是普通的影剧院。门口发光的标牌上并没有显示电影片名。它既不能算严格的现成品,而不是能自成一体的雕塑,其真实作用是显示内部“布景”。灯光闪烁时,展厅内部正常照明;灯光熄灭时,空间也会一片黑暗,变成电影放映场所。因此,每名参观者都被同时赋予若干不同的观赏身份——观影者,观展者,而且有可能在虚幻与现实某种奇怪的混合体中成为表演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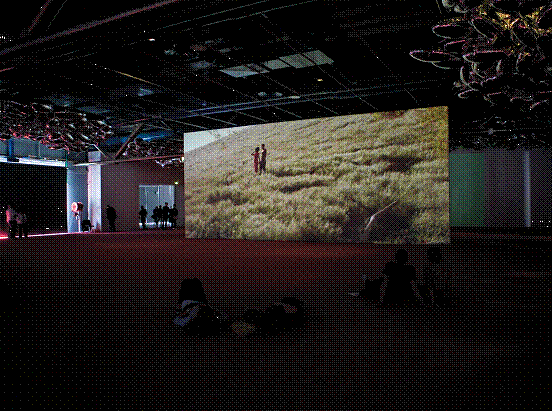
空间本身的戏剧性也加重了这种不稳定。展览所在展厅位于一楼临街,三面墙上都是落地玻璃窗,可以看到街景。慢慢地,观众留意到,街头嘈杂的市声被引入空间,把人的注意力从展厅内的作品拉到不断变化的城市景观上。而城市的车水马龙本身就变成了一场无处不在的电影,玻璃窗则成为透明的屏幕。但每隔二十分钟左右,窗帘会自动拉上,玻璃盒子变成电影院。黑暗中,一面看似空白的墙上出现了一幅磷光的丝网印画,画面里一群小孩举着好像标语牌一样的东西。同时,电影《1968年6月8日》(June 8, 1968, 2009)在一块巨大的银幕上开始放映。观众可以席地而坐观看影片,也可以在昏暗的展厅内走来走去。
《1968年6月8日》用华丽的70毫米胶卷拍摄而成,开场是无涯的铁路路轨,枕木一根一根从眼前掠过。我们坐着火车,穿过阳光灿烂的树林,穿过青葱翠绿的山丘,而铁轨边上的路人们则望着火车头呼啸而过。他们停下了手头的工作,一心一意盯着镜头。目光交汇,他们在银幕上看我们,我们在展厅里看他们。八分钟的时间里,影片在风景和城市间来回切换;唯一能听到的是火车前进的哐啷声,汽笛偶尔发出的尖利的鸣叫,以及风拂过山坡草丛沙沙的轻响。片名日期指的是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遇刺后三天,棺椁从纽约运往华盛顿的那一天。对于这段旅程,影片并没有直接描绘,而只是隐约地暗示——帕雷诺启用了演员,而且把拍摄地点选在加州,而不是东海岸。片子给人一种时空错位的感觉,过去仿佛与现在叠加到一起:车厢和服装还是四十年前的款式,但影片丝毫没有掩盖布景的当代特征,因此,六十年代末的这场文化创伤似乎又回来在二十一世纪的环境中徘徊不去。
该影片是这场充满矛盾的回顾展核心所在,而帕雷诺本人对创造持久物品从来就毫无兴趣。实际上,蓬皮杜中心的展览只是艺术家一系列全面回顾展的环节之一,首场展览已于今夏在苏黎世美术馆(Kunsthalle Zürich)举行;接下来还将在都柏林爱尔兰现代艺术博物馆(Irish Museum of Modern Art)和纽约/巴德学院赫塞尔美术馆(Hessel Museum of Art)和策展研究中心展厅(CCS Galleries)展出。苏黎世美术馆的展览结构按时间上的延迟来组织,每个展厅门口上方都安装着天蓬,让人感觉仿佛展厅内有一场视觉盛宴正等你享用,但真正进门以后,却发现只有一个基本上空空如也的大厅。观众被撩拨起来的胃口直到最后一个展厅才得到满足,这里放映着帕雷诺记录东南亚一家临时影院建设过程的短片《火星来的男孩》(The Boy from Mars, 2003)。时间上的短暂与空间上的分散(这些展览都相距遥远)互为补充。蓬皮杜中心展览新添的几件作品似乎更加突出了这种易逝临时之感:《言语泡泡》(Speech Bubbles, 2009)——灌满氦气的气球形似卡通图片里对话框,去掉了内容,漂浮在天花板上;《困扰时间:一年之中有十一个月它是艺术品,十二月是圣诞节(十月)》(For Eleven Months of the Year It’s an Artwork and in December It’s Christmas [October], 2008)则是一棵铝质圣诞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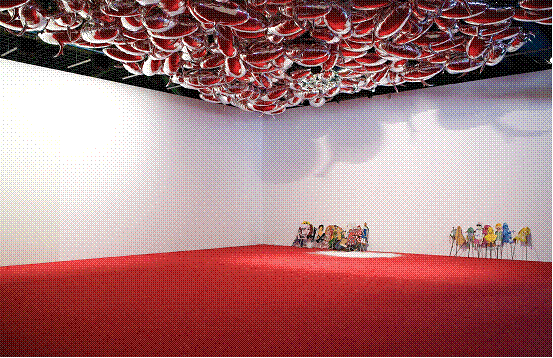
但乍看似乎没什么展品的展览其实更接近于“展览本身就是一件展品”;作品只有在特定组合下,在具体时间范围内才具有活力和意义。《1968年6月8日》暗示了帕雷诺想要追求的目标:影片让人回想起当日聚在铁轨旁边观看肯尼迪灵车经过的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更具体一点,让人联想到新闻摄影师保罗•富斯科(Paul Fusco)从列车窗口拍摄的一系列默哀民众的精彩照片。肯尼迪的棺木安放在观光车厢的椅子上,这样列车经过时人们才能看到车厢内部。富斯科的照片看上去简直像是从死者的角度拍摄的。帕雷诺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只是这一次,农民、工人、棒球球员、老人、女孩——每个人都直视镜头,但同时又似乎陷入深思,沉浸于私密的情感之中——都在扮演某种角色,我们也是。从纽约到华盛顿,八小时的车程变成了一场幽灵般的集体聚会,自发而短暂。帕雷诺用八分钟的影片浓缩展示了这段旅程:我们——零散于各地的参观者——如今也齐聚展厅,在影片结束,帘幕拉起,窗外街景人流再度出现以前,因着观看者的身份而团结在一起。
这种临时的集体性堪称本次展览的主题,不仅体现在《1968年6月8日》上,还包括《困扰时间》,毕竟,如果不能每年有一个月成为亲密群体聚会的联络点,圣诞树又何谓圣诞树呢?帕雷诺首次尝试这一理念是在1993年夏,当时他从商店买来一棵假树,挂满金属亮片、彩灯和礼物,然后放到收藏家的家里;《困扰时间》本身第一次亮相也是在他的伦敦画商皮拉尔•科里亚斯(Pilar Corrias)新画廊的开幕展上。我们同时不应忘记,头顶上的《言语泡泡》1997年诞生之初其实针对的是示威游行的工会成员,这些抗议者可以把自己的要求或标语写在泡泡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展览期间帕雷诺以《游行?》(Parade?)为题组织了一系列活动,逐渐催生出一个青年团体。《游行?》也是一本儿童图书的名字,书里充满各种妖怪形象,都是今年他和插画家约翰•奥兰德(Johan Olander)联手创作的。这些妖怪被做成皮影,随意倚放在展厅的一面墙上。小观众在参观的时候可以像举标语牌一样把它们举起来到处走。还有一些标志图像则来自蓬皮杜的艺术收藏,包括马蒂斯油画里的女人以及基思•哈林(Keith Haring)笑脸娃娃。这些好玩儿、即兴的“抗议”——帕雷诺自1991年起就以“别再谈现实”(No More Reality)为题目组织了若干类似活动——反转了围绕肯尼迪灵车建立起来的哀悼集体:彼时,集体的悲哀被图像捕捉,而此时,图像成了集体欢庆的聚合点。蓬皮杜中心为以上对集体的反思提供了绝佳的场所,因为当初之所以创立这座机构,就是因为六十年代后人们渴望建立起一种可参与的文化新模式。作品《1977年1月31日》(31 Janvier 1977)以蓬皮杜艺术中心创立之日为题,将红地毯铺满整个展厅地面,暗指建立初期的美好愿望,同时重现部分当时的那种乌托邦能量。但由此想象出来的集体性却无法在即时直接的标志下成形;在我们身处的媒体时代,图像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调解。《1968年6月8日》把富斯科拍摄RFK灵车行驶沿线的照片重新搬上银幕,让人联想到七十年代艺术团体“蚂蚁农场”(Ant Farm)对约翰•F•肯尼迪遇刺录像的重拍作品《永恒的一幕》(The Eternal Frame, 1975)。该作品是帕雷诺一帮人创作的检验标准,比如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的创作就明显受到其影响。但《1968年6月8日》几乎等于在向《永恒的一幕》致敬,赞赏它审视了媒体在构建后现代神话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以来,《永恒的一幕》似乎都被看作解构电影图像的经典之作,是对历史事件与媒体景观之复杂性的一次探索,而帕雷诺让我们留意到蚂蚁农场这段表演兼重排中更加挥之不去的一面。虽然和蚂蚁农场一样,他也启用了媒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元素,但他坚持认为,在这些景观处境当中可以实现一种真正(尽管短暂)的社会空间共享。现实不仅仅如居伊•德波说的那样在图像里被异化;相反,图像变成了真实与可能汇聚的交叉点。帕雷诺的影片就反思了这种交叉、这种乌托邦所包含的可能性;艺术家在回答一名法国记者的提问时说道:“关于这段历史,我想造出一种比CNN更真实的图像。一天之内,所有工人都团结起来,这一刻真的带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而我就成长在那个乌托邦完结之后。”
他的这番话意味深长,首先让我们想到,1968年6月也是法国工人阶级大罢工的最后一周,那次罢工几乎让戴高乐政府下台。美国的这次事件性质完全不同,意义也更加模糊:一个多种族国家的人民不经计划默默地聚集在铁路两旁,但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面屏幕,投射有关那些“所有工人团结一心”之时的回忆。当年帕雷诺只有三岁,他的确和我们一样,是在后乌托邦时代里长大的,景观似乎已经彻底拉开了现实与其图像之间的距离。但帕雷诺与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一样,拒绝将这种可能性作为放弃或听天由命的借口;相反,他坚持我们这个图像世界在情感上的潜能,挖掘它令人惊讶的感染力,以及催生新式联合体的能力。帕雷诺四展合一的结构也许为我们勾勒出了这种幽灵群体分散的边界。《1968年6月8日》并没有记录革命,但的确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今一个非实体,非强制的集体性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在蓬皮杜艺术中心几乎空无一物的巨大空间里徘徊,仿佛在等待一场集会,这时候,艺术家一直关注的中心问题也在眼前变得越来越清晰。
汤姆•麦克多诺(Tom McDonough)是纽约州立大学艺术史学副教授。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