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在巴黎的现代美术馆卷把你的皮耶罗曼佐尼回顾展的画册中,南希•斯柏特(Nancy Spector)写到了“美国学院派”对这位战后意大利天才的“一时的无知。”这种无知目前似乎已得到些改善。这位战后意大利艺术和贫穷艺术的教父,他在美国的首个回顾展(杰玛诺•切兰特Germano Celant策划)不是在博物馆举行,而是进入了拉瑞•高古轩的切尔西画廊(2009年1月24日-3月21日),这一本土画廊在展览类型上不拘一格,呈现出高水准博物馆大展的野心。(高古轩早些时候同样精彩的皮诺•帕斯卡里Pino Pascali展览和培根•吉拉科莫提Bacon-Giacometti在画廊楼上的对话表演,可以分别被认为是2006年和2008年最佳展览)。策展能力和学院力量之间的平衡似乎在近些年被冠上了商业的头衔,尽管在当下,只有资金才能维持住艺术性的知识、调解审美欲望,但这里还需要比实际更多的篇幅去分析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一个解释是,博物馆必须假装公众化,于是通俗化起来,资金与投机性的投资可以是隐蔽性的,但必须是唯一与排他的。自从杜尚以来,没有其他艺术家能够以一种相对激进的方式抽回并保留审美物体的调和性和补偿性功能了—-而这一特征在曼佐尼的创作中不时有所显现,有时很天真(就如达达),有时呈现出狂妄的反美学倾向,在艺术手法的终结中,受到贝克特的《尾声》的影响。马塞尔•布洛德特哈尔斯(Marcel Broodthaers)是首位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在1963年的文章中,他这样赞美艺术家:
曼佐尼去世了,真的走了。他很年轻。在他的终极死亡和对艺术语境所采取的态度之间,有什么联系么?在他坚持自己的那种幽默时,采取的并非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姿态,这是一定的。如果说这就应该是原因的话,那么我们对艺术活动,对所有活动的追问,必须要深入彻底起来。无论怎样,曼佐尼必将走进二十世纪的历史书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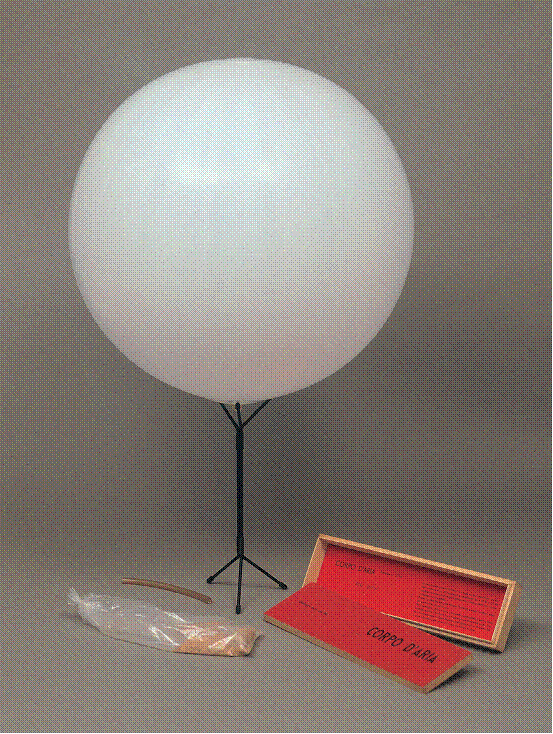
今年的回顾展之所以突出,除了完整地呈现出艺术家的作品外,就是切兰特指导性的旁白,将曼佐尼和被认为是他的同辈们的创作联系在一起,这些人有美国的德枯宁,劳森伯格,斯戴拉,欧洲的弗特里埃(Fautrier), 芳塔娜(Fontana), 克莱因,萨维奥(Lo Savio)。策展人努力构建出一个兼有美学影响和对话的广阔领地,这种比较也加深了人们对曼佐尼三十年的短暂生涯中独一无二和不可比拟性的认可(他1933年出生在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1963年于米兰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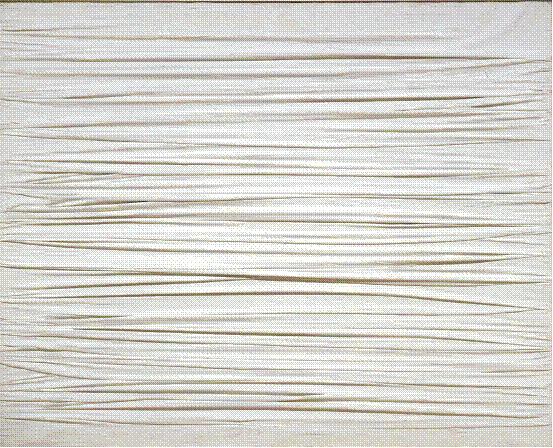
这场展览似乎表明,当人们回头去看二十世纪的时候,就会将这一时期最伟大的艺术家分成两类:那些似乎是新的发现产生的则是一个可能无穷无尽的创作(从毕加索,到劳森伯格到里彻, 那些对美学创作的定义彻底地消除了多变性,有系统地缩减了继续扩大艺术创作的选择权(从杜尚,到Cage, 到George Brecht)。本身的这种区别也许并没那么具有革新性,当然它指向的是第二个更为重要的问题:第一种艺术家带给人们的乐趣是什么呢?对一种新的范式的发现为何又成为似乎是无穷尽的创作力的合法性准则?从否定的撤回与保留的禁欲主义中我们得到了何种美学经验,对美学的反对又是如何贯穿曼佐尼的全部作品?
曼佐尼(和博伊思)是后法西斯时期拒绝乌托邦和现代主义先锋所留下来的进步性遗产的首批欧洲艺术家之一,他不仅破坏了传统的艺术分类法,而且给我们呈现出了现代主义进步性外表下的最具诱惑力的幻象:还原主义,经验主义,自我映射,单色画,视觉性,策略性,参予性。第二眼看去,或者稍后再看上去,观众就会觉得,曼佐尼的作品并不是Ryman的作品的先驱,而是以一种未知而简介的粗鲁,将这种先锋的手法进行了悲观的曲解,也许恰好解读了什么是“一时的无知”。

曼佐尼将色彩、姿态和构图从绘画中消解,就如艾特盖特(Atget)将气氛从他的照片中剥离掉一样,好似沃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无水的沉船一样。在无休止的变换中,起初,曼佐尼以有系统的折叠法来构建他的画。接着,他将简单派的单色画抽象和现成的材料结合在一起,在画上覆盖上稻草或面包卷,都浸泡在瓷土中。最终,艺术家甚至将技术上的残余抛掷脑后,转向了纯白聚乙烯泡泡,棉球堆或聚酯纤维的堆砌,将现代主义箴言放诸于材料中。
没有一个准确的理论性框架为基础,是很难准确地靠近曼佐尼的作品的,因为作品的领域将60年代不久以后出现的所有问题作为了艺术上的重要挑战和评论课题:学院派框架对美学经验和作品客观性地位的影响;传播形式和美学分配与作品的经济价值之间的对立;坚持认为艺术是私人财产与美学经验明显而广泛的可运用性之间的对立。没有人—至少从杜尚以后没有人,以一种可比较的辩证法来应对这些巨大的矛盾。

当观众被曼佐尼决然的美学经济所吸引后,大家不可避免地直面作品反美学冲动所产生的分裂性。首先是一种我们至今都难以想象的独立性(以排泄物,呼吸和血液的形式进行身体功能上的表演性展示),作为一种将自身融入美学客体实际所强调的仪式,这种态度是将自我主张最激进的姿态进行即刻的审视。对集体化美学释放性冲动的广泛性应用的冒充很快被看做是对行政控制一种不可超越的状态(在《线条,1959-61》中,曼佐尼对自动论者迸发力讽刺性重复的描绘)先锋终结后,曼佐尼的作品,早在1959年就向我们宣告,艺术否定和批评的空间,文化控制的空间和姿态,已变得清晰可辨而又不可避免地搅和在了一起。
本杰明 H.D.布奇罗 (Benjamin H.D.Buchloh)是哈佛大学现代艺术Andrew W.Mellon教授。
文/ 本杰明 H.D.布奇罗 | Benjamin H.D.Buchloh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