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既是图像,也是具体的事物,它们的意义随着自身材料的改变而发生着变化:例如数码文件,展览画册,杂志页,网络粘贴等(且不说这些形式本身的多样性以及其它的表现形式有多少了)。就如1999年罗萨琳德•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在说到沃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的文章时所写的那样—我们必须明确“媒介本身的些微差别”和“艺术必要的多重性…这种多重的状态有别于任何哲学概念里达成共识的艺术思想。”不过,重建媒介具体性这一驱动力在今天依然势头不减,其目的是找出可以将不同的图片作为艺术联在一起的相关美学元素,它以一种以有别于其它创造领域的方式而存在。
过度的比喻或纪实淹没了这场综合化的整合运动,但近来它正在日益抽象的领地里积蓄力量,蓄势待发。实际上,一批美国展览和出版物都将抽象作为摄影的终极目的来进行表现,世界似乎进入了一个后摄影的未来,真实世界的影印将被数码世界完全控制。在这一崭新的视觉领域里,抽象很快就被赞为“虚幻的艺术”并且“上升”到“视觉边缘”的前沿位置。莫里斯•丹尼斯(Maurice Denis)曾提出,绘画中,对于外在的形式上的编排是首要的,对于世界的表达则是次要的,一个多世纪后,我们对他的论断有了一个完全倒转的解读:“所有的摄影都是对现实的演绎”,因此,我们也被灌输,“现实的抽象总是出现在摄影中。”大多数德奥的信仰改变者,也是由策展人-艺术家-史学家所引导,如Ruth Horak, Gottfried Jager和Floris Neususs等人, 继续传播这一长期存在的论断,对于描述性元素的消除是保证摄影是一种“衍生性”而非“模仿性”的艺术形式的唯一肯定性方法。

但是抽象并非摄影共同的隐秘母体,也非“传统”摄影的解药。同样,如果说抽象在今日更有意义,那是因为它令人们意识到摄影的流逝。说起目前关于它业已消逝的讨论,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从最初开始,摄影就一直是处于“终结”的状态,通过经济和历史力量(真正意义上的抽象)以及消费流行习惯和社会影响的转变,它的技术基础在持续不断地更替着。无论那些个人化的作品是多么精妙而高瞻远瞩,作为图像构成的摄影,总是会深深打上工业和后工业时代陈旧过时的烙印。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要改变对摄影的历史性观点。为了理解这一观点,我们不妨看一下里兹•德舍纳(Liz Deschenes)的作品,从九十年代早期,艺术家就一直在探讨摄影的易逝性特征—它固有的、多重而易变的一面。具体讲,艺术家专注的是常规图像模式所摒弃的抽象形式:如多余的网纹干扰,电视“绿屏”,电影屏幕叠印,表示地形学高度的色彩键。
在这十年的最初的几年和2009年里,艺术家用银胶凝型,在月光下制作了一系列的黑影照片,图片的表面并未因此受到影响。近期作品更接近镜面和它的比例构成。它们镶嵌在铝面上,没有边框,所以本身就是独立的物品;如果面色的物体反射性不强,那么它们就露出很明显的单色表面。要是人凑近去观察,它就会照出你的样子来。看着这个模糊的自我成像,人们也许会觉得,之前的图像通过表面的递进银化过程已被吞噬,或者说,人们自己的映像可能正在被银盐所侵蚀。
近期在纽约的Miguel Abreu画廊的展览清楚地诠释了上述的这点。在展览中,六个这样的“镜面”设置在一个像眼睛一样的门上,每个被照到的观众,身体的不同部分都出现在里面。这件作品《Tilt/Swing》(2009),灵感源自1935年赫伯特•贝耶(Herbert Bayer)设计的一场展览,图片以360度的全景视角得以展现。而Deschenes的作品用镜子取代了贝耶当时的图片,但展现的并不是全景,而是断断续续的一圈抗图像(image resistant)物体。
它消解、偏离了主观性,为观看本身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Tilt/Swing以临界距离探讨了贝耶的光学历史模式:德舍纳的摄影抽象对现代主义单色画在绘画上的地位并不艳羡。艺术家部分的批评,实际上依赖于图像(不在场的贝耶图片)和物体(墙上、地板和天花板上狭窄的长方形)之间的辩证。重要的是,德舍纳的作品对目前围绕摄影抽象的论点进行了矫正,当前的论点在一个想象的具体媒介的自我呈现中,对仅关注自身环境的作品给予过度的赞美。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问题。在他1931年的文章《摄影简史》中,本杰明就针对“拜物而反技术的艺术观念”,批评了对摄影无休止的评估,认为摄影批评中技术和美学的混乱,“在摄影师尚未推翻他们的论断时,才承认他们。”如果说,八十年后我们业已改变的历史语境已经改变,本杰明的文章与其说是正统说教,不如说是开创了研究先例。在这一精神之下,我提议应该总结出一部抽象摄影“简史”,就如德舍纳那样,对于处于主导地位的“纯粹的摄影真实性”和“摄影中的摄影”进行挑战。这段历史中的作品强调了摄影师和观众的身体,语言、幽默和欲望将他们激活。处于危险边缘的是摄影作为图像和物体的存在性:它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被艺术家用作是补充的手段。
由于以上原因,我认为保罗•斯特兰德1916年的作品(如Bowls and Abstraction, Twin Lakes, Connecticut)并非是Jager所称道的首批抽象摄影作品,所以我要讲述的历史并非以此为开端。制作本身以及摄影对其它技术和物质支持的依赖在这场对摄影画面的精确研究中不予探讨。我认为源头还要早几年,应当是波兰作家、艺术家维特凯维奇(Stanisław Ignacy Witkiewicz)的一张图片。这件作品大约是1910年左右创作,是他最早的创作之一,体现了作者被绝望所吞噬的心情,画面中的他被朦胧的黄色光笼罩着。左边的一道光亮是一个模糊的镜子,粗糙的镜面无法照出人的原样;右下角发出了光亮,昏黄之中,艺术家的脸庞似乎因面前的那个楔子而感到了惊恐,整个照片给人的感觉是,照相机似乎将它们的拍摄对象都给吞噬掉了。为了弄出另一张更为知名的肖像图,维特凯维奇在曝光后,用锤子和钉子敲打了玻璃底片,然后在冲印前将一些碎片拿走,出来的效果就是头顶没了,脸上是玻璃裂纹。
维特凯维奇战前创作的肖像图片也许是最早的受到使用手段影响的自拍照片。材料本身在脆弱的玻璃底片里似乎可以自行伸缩挤压。这些图像(就如斯特兰德的那样)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抽象;它们只是用抽象将主体和机器之间紧张的关系进行了视觉化的呈现。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实验时期里,这种局部抽象但却有力的抽象表达运用了各种方式。其它的例子,有1922年前后拉茨罗•莫霍利•纳吉(Laszlo Moholy-Nagy)所做的黑影图片,就如策展人Leah Dickerman所说的那样,艺术家对图片进行了精心琢磨,强调了光学领域了触觉的重要性。还有艾尔•李辛斯基(El Lissitzky)多次曝光的图片,最著名的是《构成者》(The Constructor 1924),身体的部位手与眼被叠加在了一起。此外,还有亚历山大•罗德琴科(Aleksandr Rodchenko), 莫霍利•纳吉(Moholy-Nagy)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所做的那些令人头晕目眩的作品,他们改变了长久以来的观看习惯,从高楼到阳台,他们以从下往上的角度去拍楼梯,拍那些快速上升的物体。抽象于是与迷茫画上了等号:内心油然而生的错位体验令观者产生了“现场感”。

这种持续的不安感在战争时期更加抽象的摄影中表现得很明显,这些图片面向更多的媒介,强调了材料或物质的不稳定性。克里斯蒂安•夏德(Christian Schad)1918年和1920年之间的黑影图片,边上是划痕和被剪刀剪过的痕迹,画面上都是一些从垃圾桶里拾捡的宝贝。摄影成为了再循环的废弃物的照片,成为了零碎物本身;它将粪土化为金子,而自身的粗砺感却又无法抹掉。这些小纸表现出一种对“零散抽象”的达达式迷恋,这种迷恋在一些作品中都有表现,一直持续到超现实主义时期。塞尔维亚超现实主义艺术家Vane Bor1928年的黑影照片,将碎玻璃和乱七八糟的杂物作为道具,形成无明显特征的、令人不安的图案。另一个例子也是塞尔维亚的,作品同样模糊隐晦但却独具美丽,这就是1932贝尔格莱德的刊物《此刻的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 Here and Now)中的文章《在一面墙前》(In Front of a Wall)。它模仿了《偏执狂的解读》(Paranoiac Delirium of Interpretation)。用六组文字诠释了一个腐蚀的石膏表面的正面图。如果没有文字解释和达利式的题目,人们很难看清楚这张泛黄的图片中到底是什么(给这张图命名,也是用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它的晦涩难懂。作者的描述只是更加深了图片的诡异)。这里要提到的是同一年出现的摄影抽象的子类—-采用了喷溅感光乳剂的方法,这些作品体现了摄影从图像或画面构成上分离的程度,在手法上使用了感光乳剂。近期在法国的巡回展《图像的颠覆:超现实主义,摄影,电影》 (The Subversion of Images: Surrealism, Photography, Film)上,展出了罗格•帕里(Roger Parry), 莫里斯•塔巴德(Maurice Tabard)和米罗斯拉夫•哈克(Miroslav Hak)等人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摄影师可以鼓捣出完全非客观性的画面,画面上可以没有任何具体可见的事物,彻底而极致。不过,它们也可以简单地看作是用感光乳剂代替了颜料,但却并没有侵犯到颜料的范畴,而是融入了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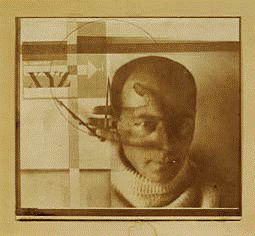
曼雷如今因一系列关于身体的抽象摄影而受到了追捧,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将用崭新的角度去重温这些曾经熟悉的作品,它们对客观存在的主体不是驯化而是操纵:通过针孔照相机产生的效果,街灯变成了朦朦胧胧、四散开来的雾;在一张布朗库西式的图片中,以软焦特写的方式勾勒了李米勒的脖颈;梅莱特•奥本海姆(Meret Oppenheim)斜倚的身体被曝光过度的手法变成了欲望之海;基基(Kiki de Montparnasse)的双臂交叉在头部,在一些更加模糊的照片中,变形成了游荡的魂灵。本杰明对1840年代摄影的看法基于的是对大卫•奥科塔维斯•希尔(David Octavius )Hill和罗伯特•亚当逊(Robert Adamson)的作品研究上,这点在此也很适用:“制作工序本身令主体以他们的方式进入了当下这一时刻,而非出离在外;在长期的曝光中,他们逐渐变成了图片。”曼雷作品里主客体的混合似乎与它在技术选择上一样完整而扎实,这些手法令身体或空间似乎游离在历史时间的内外。
二战结束后不久,曼•雷的密友马塞尔•杜尚将色欲和抽象之间的关系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地。在他逐渐完成的杰作《给予:1、瀑布2、燃烧的气体》(étant donnés: 1o la chute d’eau, 2o le gaz d’éclairage . . ., )1946–66中,抽象可谓无处不在。杜尚在早期摄影图片中拍过的那扇破门,好像柯特•舒维特(Kurt Schwitters)的《莫兹堡》(Merzbau)中残留的一部分似的。作品关键的“吸引点”是躺在门外的变形了的人体。看着这具裸体,人们不禁意识到门的存在。虚拟的人体和抽象的门绝对不可能被认为是同步的,但是在意识里它们则是一直在一起的。

在《给予》中,摄影并不是抽象的,但确是和抽象结合在一起。去年夏天在费城博物馆举办的那场精彩展览中,这一点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作为画面背景的风景图,杜尚从在瑞士山区度假拍下的照片中剪切和拼贴起来的,经过加工形成抽象的图案。这一制作程序是从最初对作品的研究中自动发展出来的,开始是一幅1942年的叫《In the Manner of Delvaux》的拼贴画,然后是1943年的《Twin-Touch-Test》, 这是与弗莱德利克凯斯勒(Frederick Kiesler)为当年的超现实主义杂志VVV所做的设计图。这些作品中的每一件,都是一张充满欲望色彩的摄影,但周边却经过了简单的抽象加工:空白处是一点打褶的锡纸,或者是细小的金属丝格。
中世纪的抽象词汇围绕的图片更适合于刊登裸体女子的杂志。这种与视觉规则相反的结合以窥阴欲影响了抽象。而它也通过人为的物质性阻止了欲望的表达:这种行为不是通过身体而是通过折叠的亮锡纸和金属格而完成的。后来,杜尚将庞大的裸体人物上蜡,让其像一具庞然大物一样横陈在瑞士瀑布前,旁边则被弄上了风景图片。
这一上蜡的摄影拼贴,约在1946年完成,与《任性的风景》(Paysage fautif)有着不可分的联系,后者是杜尚同一年用精液在一张变形纱上完成的。这是一件完全抽象的作品。就如一张摄影图片一样,它的意义由“它是由什么做的”所决定。回答这一问题,还是得提一下瑞士,这里是杜尚的印第安情人兼模特当时的居住地。此时,观看和欲望变成了抽象的根本。就如门和风景一样,瑞士和“残缺的”风景只是彼此需要而已。内在的依赖性保存下来,很难再变更,在最终版的作品里,人的视线则不停地徘徊在几乎平坦的雕塑人物和非真实的摄影背景之间。
1966年,杜尚开始为将《给予》弄到费城而做准备,而就在同一年,梅尔•布什纳(Mel Bochner)开始了对摄影的角度和规模的探索研究。这一些很快脱离了布什纳时代的再创作,照相机,感光纸,光电穿孔带等。Surface Dis/Tension, 1968,是这类作品中最伟大的一件,在这个作品中,布什纳将一个四方的桌面变成了一个垂直下来形状不规则的模糊体,上面是起伏弯曲的线条,这种变形通过拉伸,浸泡,分层,重装,压印,在一张逐渐起褶的照相纸上形成。

作品处理手法上面的特征是很明显的,即使最终的构图很难解读。布什纳在一些名为Crumple的相关作品中,强调了滤光和化学色素之间的色彩变化,对于物质性和处理手段讲述得很透彻,这也令人想起杜尚作品中的实体策略。这并非是“关于摄影的摄影”,而更是“关于”表达手段的摄影—-它作为一件艺术作品的客观化。
1970年左右的一些新作品继续了这种抽象模式,将摄影作为感知体验的类似物来进行研究。简•迪贝兹(Jan Dibbets)的经典《角度的纠正》(Perspective Corrections,1967–69), 看似长方形的几何图形实际是模糊的梯形。在指示性成为摄影的主导性理论之前,这样的作品检验了图片指示性的精确度。摄影作为对真实的印记并不是这里讨论的重点所在,关键要说的是图片与客观化之间的关系。我们窥视到的和我们正在看的之间的对比。
七八十年代大量的抽象摄影则忽略了这些发现,呈现的是大幅的、制作更精良的图像。三十多年来,抽象现已成为艺术学校的附属专业。在这种僵化的局面下,艺术家詹姆斯•威灵(James Welling)的创作给抽象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他近期在芝加哥Donald Young画廊的的回顾展。观看威灵的“Degrades,” 1986–2004, 将他的黑影图片中碧蓝的水和纽约城中冬日的蓝光做对比,或者看到他在七十年代从前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广告挪用到他对布料的长期使用,可以体会出他对抽象光谱和造型的研究达到何种程度,二者之间并没有所以为的冲突或对立。
我勾勒的历史与当代性对话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上,对于摄影抽象突然关注,也许标志着批评领域而非艺术创作上的一个转变。人们怀疑支持这一新说法的是一种老式的创作概念。调整象素似乎更像是涂抹颜料。这一规律也令人想起了抽象绘画,后者同样在创造性上达到了现代主义的高峰。如果说本杰明反对用过去的绘画去评估摄影价值的话,而如果我们意识到当下对抽象摄影的追爱令人想起二十世纪中期对绘画上“光学”的痴迷时,那么他的抗议也是有理可据的。

计算机产生或辅助而生成的摄影并不可能改变摄影规则运行的轨道,将陈旧的审美标准与新技术相结合。艺术之外的历史助力也许将完成这个工作。资本的构成在当下已变得更加抽象起来,就如乔治•贝克(George Baker)在一系列文章中所论述的那样。社会关系和方法对政治性表达也是如此。不过,正如贝克所强调的那样,表面上抽象的摄影没必要是那些最能表现历史转变的作品。在本杰明的《简史》中,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发现,二十年代的Krupp工厂摄影图片,外在的记录并没有表现出当下的功能状况,这样的图片可能会对无法做到这一点而感到羞赧。
当然这并不是说,就像贝克的做法那样,摄影作为一门视觉创作是为抽象而抽象。但也不是说摄影中真实可见的抽象就是毫无价值的追寻。摄影在艺术中的应用并非是被经济交换的变化形式牵着鼻子走,在图片与事物、图片与人的关系上,它依然可以以一直变化的方式进行。
这种改变上的努力是以摄影与它本身—它的图像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开始的,这一联系对于简史中具有突破性的抽象很重要。近代摄影中突出的例子以启示的方式表现了这种联系。莫伊拉•达韦(Moyra Davey)的Copperhead Grid, 1990,为哈佛大学Fogg博物馆的展览而再次复原,随后被带到纽约的Murray Guy画廊,作品对准了交换中不起眼的东西—-普通的美国钱币,硬币上磨损破旧的林肯像进入了我们的视线中。摄影图片约为10乘8英尺大小,密集地悬挂在展厅中,每个圆硬币都被挤压成长方形,里面是总统的肖像。这算是一种反Rushmore的举动,本国的伟人肖像不是以加上玻璃的纪念性照片大小呈现出来,却是在一百多个小长方形上被磨平后用曲别针挂在了墙上。这种做法似乎是艺术界对电脑屏幕作为生成不可触摸的发光图片这一工具的回应。达韦提升了零散小物件的价值,这些被随便弄来弄去却有价值的物品由于几易人手而被磨损。

这种手法在观念上是很精彩的:将没什么价值的纸张和金属物联系在一起,把它们的循环模式和无纸币的资本流通做了对比。Copperhead Grid也许将抽象和贝克所赞赏的返祖性的相似主题化了,在一个被金融资本和与之相生的危机所统治的时代里,作为有生产力的未来的“摄影之后的摄影”,钱也许在引领着模拟照相机的方向前进。(由此与过去再次产生了联系,1929年大萧条之后,本杰明在《简史》中这样写道:“如果摄影手段回溯到前工业时代的全盛期,与资本主义工业危机具有什么隐秘联系的话,这也不是什么令人吃惊的事。)抛开预言性的特点不说,这件作品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在个人和体系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互动,体现了技术化世界里的飞速转变。他没有用一种宏大的方式去展现,而是通过无数个细微的行动。于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转变,就这样被印刻在一张张被损毁的脸庞上,而这种结果则是在货币流动中,因人们无意间的举动而形成的,绝非有意识的刻意动作。即使它们最终并没有传播开来,抽象的终极还是很明显地表现出来,钱没有被替换,只是不见了。但是图片本身依然保持它的锐利本色,与达韦双关的题目保持一致。敏感的观众在这些有划痕的表面可以看到在现实世界中非常具有个性的可辨明的密码。
目前抽象界的明星威立德•贝西蒂(Walead Beshty),其作品将图像和人之间的关系诠释得一目了然。贝西蒂通过折叠发色的图片,将其裁成等身大小,形成了三维集合形状,创作了《多面图片》(2006-)。之后将这些面曝光,根据原色光谱(红绿蓝)或反射色(青绿、紫红、黄)确定光源。(当贝西蒂还是Bochner耶鲁的学生时,二人经常一起讨论,这些作品借鉴了后者的Crumples和其它早期作品)。
《多面图片》强调的是光和纸,但也有摄影材料和制作工序,这些观众会想到的具体内容。这些信息在冗长的描述性题目中传达出来,题目的撰写是由Beshty的洛杉矶老同事克里斯托弗•威廉姆斯(Christopher Williams)提议完成的。读到这些题目,对所用纸、颜色、张数、曝光日期和地点的这些详细描述,人们不禁感到,拍摄对象是无法用它的表现方式的标准去衡量的,无论是语言上还是作为图像本身。

贝西蒂坚持强调的是摄影图片显著的物质存在性:任何“对图片和材料之间的划分都是没必要的,是完全华而不实的,”他这样写道。这也是危险的,对于可传播图片的特殊关注,结果只突出了当今象素单位组成的图像世界的独霸性。这些作品的展览计划是要具体化的,制作上就是贝西蒂所说的“工业肖像”,近乎等身的彩色图片涉及了装裱、设置或策划作品的各种展览这些工作。但是这些肖像摄影在一些展览中是看不见的,掩盖了艺术家的不付出劳动就无法“产生”出一个图像的观点。贝西蒂在可感知的身体和无思想“大众化”的机械设备之间建立了一个辩证的交会,令人想起了瓦莱姆•弗拉瑟(Vilem Flusser)的说法——一种对于这种辨证法所做的长期先锋性付出后,依然能激发思想的努力。
“没有哪个摄影图片能比另一张更具生动性,”去年,贝西蒂在解释他的想法时这样说。达韦, 贝西蒂和德舍纳的作品都很特别,他们排除了某一范畴内对“媒介”的看法。没人声称要去给摄影、抽象或什么下定义。作为对于那种独特性的衡量,手段,由于不同的原因,每个作品都很难再制作。达韦的太大了,没法容纳在书里,Beshty的则很脆弱,很容易打卷,德舍纳的镜子则根本无法捕捉,在任何光线下都不行。它们有趣的不规则表面和处理标记在印刷中都会消失,只变成了毫无光泽的单色画,没有任何镜子般的衍生效果。
也许,不可展现的不是图像而是投入其中的劳动:人们只能亲自去看这些作品,方才能体会到其中的投入。这种图像和身体的联系是很明显的。人们是否可以说反灵氛的事物完全是由仪式般的邂逅和原初的存在所决定的呢?这似乎为本杰明以降的摄影史提出了一个难题。
马修•维特科夫斯基(Matthew Witkovsky)是芝加哥艺术学院的策展人,摄影系主任。
文/ 马修•维特科夫斯基 | Matthew Witkovsky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