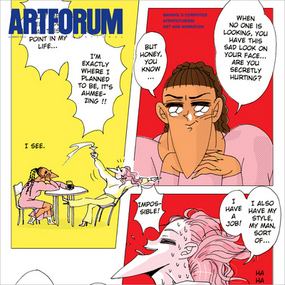3月1日,重要的左岸派导演阿伦・雷乃逝世,终年九十一岁。跟雷乃时有合作的同行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在他过世后不久发表的一篇纪念文章里写道,雷乃是一个将对电影的爱贯彻终生的电影人。的确,就在他去世前不足一个月,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纵情一曲》(Aimer, boire et chanter)还在2014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首映,并斩获阿尔弗雷德·鲍尔奖(获奖理由是“为电影艺术开拓了新的视野”)。这是他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以来整个职业生涯中创作的第十九部剧情长片。
雷乃在接受法国电影杂志《Positif》采访时谈到了他对该片原作——艾伦・艾克鹏(Alan Ayckbourn)的戏剧《雷利的生活》中忧郁情结的感受。他说,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终会发现,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是一场失败。但他最后一部影片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对生活、虚构和误会进行了一次高妙的反思,其中的自我指涉也促使观众去回忆并评判雷乃整个电影生涯。导演本人提到了他在1939年十七岁时看过的一场契诃夫戏剧《海鸥》对《纵情一曲》的影响,当然最终完成的影片充满展现了雷乃作品最契诃夫的一面。在批评家菲利普・罗耶(Philippe Royer)看来,雷乃电影最核心、最吸引人的部分就是他如何运用虚构去接近真实,以及如何在生命体中感受幽灵的存在。《纵情》片中慵懒的光线,电影布景里可爱的蓝、绿、黄色,灯光和阴影的游戏都让影片充满感觉,唯一能与之媲美的就是演员们同样精确、鲜活的演技,尤其是萨宾・阿泽玛(Sabine Azéma),她把虚荣、脆弱和人性的软弱演绎得丝丝入扣。
生死之间的过渡长期以来都让雷乃着迷。他对死者及其在生者生活里执拗的存在一直有很强的意识,同时也认识到电影在这一交流或负债中起到的中介作用——这一点也许是他对世界电影最突出的贡献。说到这里,我们立刻会想到他1955年极富争议的大屠杀纪录片《夜与雾》(Nuit et brouillard)。批评家赛尔日・达内(Serge Daney)对该片赞不绝口,称像这样的电影(也许是电影本身)能够接近扭曲人性的极限。而在历史学家西尔维・林德沛格(Sylvie Lindeperg)看来,雷乃的影片开启了对“大屠杀孤儿”的哀悼进程。正是该片的剪辑,其在静止图像和活动场景之间富有说服力的转换,及其对规模大小、活动事物与静止事物之间区隔的打乱使得影片对种族大屠杀的反思能牢牢抓住观众。如果说雷乃对文献资料的使用方式自有其批判者——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便是其中之一,那么《夜与雾》也被视为是在无数有关身体、折磨和亵渎的图像中对于真实之证言力量的怀疑和追问。
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在雷乃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无可指摘又令人动容的《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1959)中也有所体现。该片由雷乃和小说家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合作完成,杜拉斯浓密厚重的剧本使导演能够将他关于核爆炸的电影放到一个讲述情欲以及来自占领下法国之哀悼的故事中实现。雷乃多年以来的剧本指导西尔韦特·博德罗(Sylvette Baudrot)捐给法国电影资料馆的文献材料里包含了他从日本寄给杜拉斯的信件和明信片。当时雷乃正在日本为杜拉斯在巴黎想象出来的场景寻找真实的对应物,两人的通信让我们对影片的诞生过程有了新的理解。最终成片在两个广岛恋人相拥相依的怀抱里开场,放大变形的肉体图像宣告了接下来影片的感官强度和现代性。如果说雷乃回溯的是超现实主义摄影作品的形式以及阿贝尔・冈斯(Abel Gance)和默片里的官能性,他的电影在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的作品中便能找到同时代的回应。《广岛之恋》里的法国女主角(埃曼纽尔・莉娃饰)回忆起战争期间在法国小城韦尔自己和即将死去的德国爱人相拥躺在一起,当他的呼吸停止时,自己竟不觉得两人的肉体有任何不同,有的只是相似性。《广岛之恋》是一部关于生与死的电影:被投下原子弹的日本和被德军占领的法国,两个饱含创伤的语境被并置在一起,按照德勒兹的说法,影片最终表明两者完全不能相容。雷乃对固定的答案或已知的关系不感兴趣;相反,他为感觉,为敏锐的意识和反思打开空间。这部影片考察了广岛的一男一女能够在何种程度上通过他们在做爱时说出来的和没说出来的故事与死亡、暴力和遗忘达成和解。
《夜与雾》和《广岛之恋》都是在部分意义上关于法国,关于占领下合作方式的电影,同时也深深笼罩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阴影之下。它们与雷乃的另外两部杰作密切相关:晦涩优美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L’Année dernière à Marienbad,1961),尖锐到近乎野蛮的《莫里埃尔》(Muriel ou le temps d’un retour,1963)。从他早期跟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合作拍摄的《雕像也会死亡》(Les Statues meurent aussi,1953)(这部关于非洲艺术的短片因深入分析了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而长期被禁),到他关于国家图书馆的纪录片(1956),再到有关聚苯乙烯塑料厂的短片(1959),雷乃一直在从部分意义上用电影揭露嵌入法国社会和文化结构内部的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正如批评家Edward Dimendberg和Steven Ungar所讨论的那样)。但他的目光不仅仅局限在法国一国,和马克一样,雷乃可以说也是具有全球视野的电影人之一,他始终部分国界地关注他者性、错位、奇特、恐惑以及作为陌生人的状态。在有关毕加索的短片《格尔尼卡》(Guernica,1950)中,他第一次处理了艺术和战争的话题。而在充满了各种提前叙述镜头的《战争终了》(La Guerre est finie,1966)里,他进一步关注了西班牙内战及其战后状况。《马里昂巴德》里自我封闭的镜像和安静本身就是对影片制作时在法国无法公开讨论的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评论,而疗养院似的酒店以及慕尼黑周边不同宫殿的图像以其终极的不确定性充分讲述了二十世纪遍布欧洲的各种错位和流离。雷乃的影片以各种形式反映了变换的地图和错位的领地。他曾经说过,每次到某个城市旅行,他总喜欢去那些最没有本土特色,最容易让人误认为是其他城市的地方。他尝试制作的科幻片《我爱你,我爱你》(Je t’aime, je t’aime,1968)背景设在格拉斯哥,拍摄却在布鲁塞尔完成。《天意》(Providence,1977)里的地点也同样不明确。在这部美丽而荒凉的电影--该片讲述了小说家克里夫・郎汉姆(约翰・吉尔古德饰)脑子里有关死亡和解剖的各种幻梦——中,雷乃进一步转向了他后期创作中标志性的内面和人工模式,从这之后,片厂室内布景和风格化的表演在他片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雷乃与左岸派其他同代电影人(瓦尔达和马克)不同,随着工作进行,他的注意力开始明显偏离(外部)世界和政治。他总是比他的左岸同行更加关注心灵状态、认知模式以及知识和情感里最细微的变动。到八十年代,这种关注已经开始变成几乎排除所有外部世界噪音的专注。他对内面性的兴趣在有关神经系统和人类行为的电影《我的美国舅舅》(Mon Oncle d’Amérique,1980)中得到了最有意识的展现:三名主角的故事,三段个人历史,他们交织的生活就像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海浪》(1931)里的独白一样彼此触碰。尽管雷乃关注人性的内面,但他影片中的出场人物却是你无论怎么仔细观察研究也无法真正了解的:我们从不曾听到《广岛之恋》里男主人公的故事,也许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莫里埃尔在阿尔及利亚遭受的暴行让我们直面了未被记录、不能触碰的一切;而《马里昂巴德》里的爱人始终没有退出他们若隐若现、反复进行的虐恋游戏(正如电影史学家Keith Reader所指出的那样),去年到底发生过什么,没发生过什么,到最后我们也无从知晓。雷乃影片中挽歌似的情绪和人工感令人回想起马克斯·奥菲尔斯(Max Ophüls)的作品,同时也预示了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作品中虚构的游戏。
雷乃的电影无止尽地探寻人类心理最细微的层次,处理我们对自身以及他者的不透明性,捕捉我们可能拥有的另外一段人生、可能做出的另外一些选择中所包含的魅惑和恐怖,在这个过程中,导演渐渐发现了能够为情感赋予形状的电影表现手法。也许最富代表性的就是雷乃对推轨镜头的使用:镜头的移动是为了载我们启程,让现实从我们眼前滑过,充盈我们的感官。雷乃电影里标志性的镜头暗示着过渡和穿越——比如,《广岛之恋》女主人公在讲述自己希望被吞噬和毁灭的欲望时,镜头横扫过广岛境内;又比如,《我的美国舅舅》结尾部分镜头毫不留情地从南布朗克斯区的废墟上掠过。雷乃电影对节奏的关注在我看来是无人能出其右的。他总能找到从一个图像到下一个图像之间所需的准确时间,进而从身体上打动观众,让我们臣服于影片迫使我们感觉和想象的一切。
高度的敏感,对场面沉稳的把握,明确的艺术完整性贯穿了雷乃整个职业生涯,也保证了他留给后世的遗产。借用《电影手册》杂志最近一期的标题:永远的阿伦・雷乃!
艾玛・威尔逊(Emma Wilson)剑桥大学法国文学和视觉艺术教授,发表过若干本有关法国电影的著述,包括《阿伦・雷乃》(2009)。
译/ 杜可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