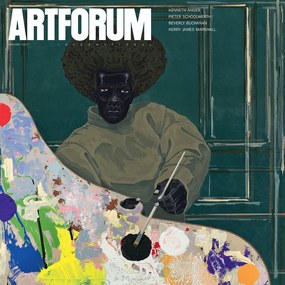耶稣死后不到两个月,基督教的全球野心被点燃。“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cloven tongues like as of fire)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于是信徒们获得了一种能力,那就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他们都能被理解。圣灵降临节的使命反转了巴比伦塔摧毁的神话——那描绘的是人类散落成不同语言族群的故事,将福音所至之地的人再次团结起来。使徒安德鲁去了小亚细亚传教,而且据说还去到了格鲁吉亚;詹姆士去了西班牙;而托马斯则远赴印度马德拉斯(Madras),并且埋葬于此。
即将于今年4月在柏林开幕的“路德效应:新教——世间500年”(The Luther Effect: Protestantism—500 Years in the World)是包括德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纪念奥古斯丁修道院修士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向罗马天主教廷发起挑战五百周年的展览之一。德国历史博物馆(The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将在马丁-格罗皮乌斯博物馆(Martin-Gropius-Bau)内汇集数百件绘画和工艺品,旨在对路德派——或者更宽泛地来说是新教——在四个大洲的“效应和反效应”进行重新评估。
路德反赎罪券(indulgence)的五十九条论纲——于1517年10月31日张贴在德国维滕贝格(Wittenberg)一个教堂的大门上,掀起了对教廷不满情绪的浪潮,并且最终导致了教会的永久性分裂。但是路德并没有将他的眼光投射到欧洲以外的地方。他指出基督教在全球的传教是失败的:“魔鬼将永远不会令其通过。”(The Devil will never let that come to pass)同时他也确信,末世迫在眉睫,改变人类所余部分信仰的时间无多。所以在整个16、17世纪,未经宗教改革的罗马天主教会开始在世界各地的传教活动:耶稣会(Jesuits)去了中国、日本、印度和非洲;多明我会(Dominicans)、方济各会(Franciscans)以及耶稣会的传教士开始在墨西哥和巴西兴建教堂。路德派在这场改变异教徒信仰的游戏中的起步无疑是落后的,直到1705年,丹麦王室才派传教士从德国哈雷出发,前往马德拉斯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特兰奎巴建立前哨。与此同时,英国新教徒开始向美国的土著传教,并且随后在非洲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柏林的展览聚焦在代表了这一信仰全球性抱负的五个篇章——1450-1600年的德国和欧洲;1500-1750的瑞典;1600-1900的北美;1850-2000的朝鲜;以及现在的坦桑尼亚。基督教的传播范围和活动力不是开玩笑: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基督徒生活在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地区。新教日益壮大,尤其是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穆斯林世界。据估计中国有约两千三百万到四千万新教徒。
传教士的目标是实现精神上的解放。但从16世纪到19世纪,传教活动是和欧洲的商业及军事征服紧密相伴的。在现代世俗视野中,基督教的传教活动是打了致命折扣的。早在1802年,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就曾说,传教活动和殖民主义是无法脱离开的。在赫尔德关于改宗的虚构对话中,一个亚洲人向一个欧洲人提问:“如果一个人跑到你的国家,告诉你你们的至圣所、法律、宗教、智慧以及政治体制都荒唐不堪,你会怎么回应?”欧洲人答道:“那跟这儿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有权力、船队、钱、大炮和文化。”
“路德效应”似乎希望给出一个不那么偏激的重估。展览明确的主题是新教的去中心化,将重心转向某一教义在适应不同地区差异时所做的调整,并指出传教活动促发了人种学研究。在劝服斯堪的纳维亚土生的萨米(Sami)和拉普人(Lapps)皈依时,瑞典的传教士们也开始渐渐了解这些种族。在特兰奎巴,传教士巴塞罗缪·契根巴格(Bartholomäus Ziegenbalg)编纂了一本泰米尔语辞典,并且梳理了南印度地区的众神谱系。
什么样的物件能够说明这些过程呢?这是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因为改革派神学家在传统来上说就对图像充满质疑,他们更偏向说教,而对艺术的感官吸引力采取沉默甚至是审查的态度。路德派相信,一幅绘画或者木版印刷应该尽可能地保持简洁清晰。新教徒不鼓励对描绘出来的图像的情感认同。一些教派甚至十分极端地规定在神圣空间内只允许书写这一行为存在。
有观点认为,尽管新教对图像充满质疑,但却对欧洲艺术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偶像恐惧(iconophobia)促进了小的艺术门类如风景和静物的发展。而偶像图像清空后留下的心理空间则由礼拜音乐来填补。新教徒对传统宗教图像的疑虑给新的主题腾出了空间,比方说像贵格派教徒爱德华·希克斯(Edward Hicks)画的《和平王国》(The Peaceable Kingdom, 1830–32)这样的民间或者非教徒图像。
“路德效应”承认新教制造了冲突,但同时也激发了创造性的抵抗。和任何一种文化转译形态一样,改宗也同样是一个充满模仿和反转的模棱两可的过程。展览的目标使得路德的改革意图退回到它们所触发的多元和丰富背后。但我们也同样很容易得出一个关于该展览不同的结论,从维滕贝格发散出去的冲击波不断引发回响,同样也证实了路德原初行动的力量。
“路德效应:新教——世间500年”,由安娜·卡特琳·齐叶莎克(Anne Katrin Ziesak)策划,展览将于今年4月12日到11月5日在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举行。
克里斯托弗·S·伍德(Christopher S. Wood)是纽约大学德语系教授。
文/ 克里斯托弗·伍德 | Christopher S. Wood
译/ 郭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