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费耶丽·巴耶茨(Firelei Baez),《献给Marie-Louise Coidavid,亡命者,秩序守护人,阿库迪亚》,2018,布面油画. 展览现场,德国艺术研究院. 摄影:Timo Ohler.
第十届柏林双年展

第十届柏林双年展的题目“我们不需要另一个英雄”(We don’t need another hero)取自蒂娜·特纳(Tina Turner)1985年的一支热门单曲,但同时也让人联想到海伦·德威特(Helen DeWitt)2000年的小说《末代武士》(The Last Samurai)里的一段话:“我们需要的不是用来崇拜的英雄,而是钱。有钱的话,我们可以想去哪就去哪。把钱给我们,我们就能变成英雄。”
由纽约艺术团体DIS策划的上一届柏林双年展因其高大上的挑衅内容而饱受批评。很多观众从中只看到了自鸣得意的虚无主义和带着特权意味的犬儒态度。因此,今年的柏林双年展明智地选择了一种更安静的处理方式,将展览设计交给了以盖比·恩科伯(Gabi Ngcobo)为首,由五名泛非洲策展人组成的策展团队。在该团队的运作下,一共四十六名艺术家及艺术小组参与到了这场优雅、节制的展览中来。
双年展展场分散于三家主要的艺术机构。空间感觉非常充足,而且开放。单个艺术家的作品——比如卢贝娜·希米德(Lubaina Himid)致敬黑人知识分子的绘画——常常在多个展场出现。这样的重复是令人愉快的,就像在新街区碰上老朋友,为整个双年展带来一种连贯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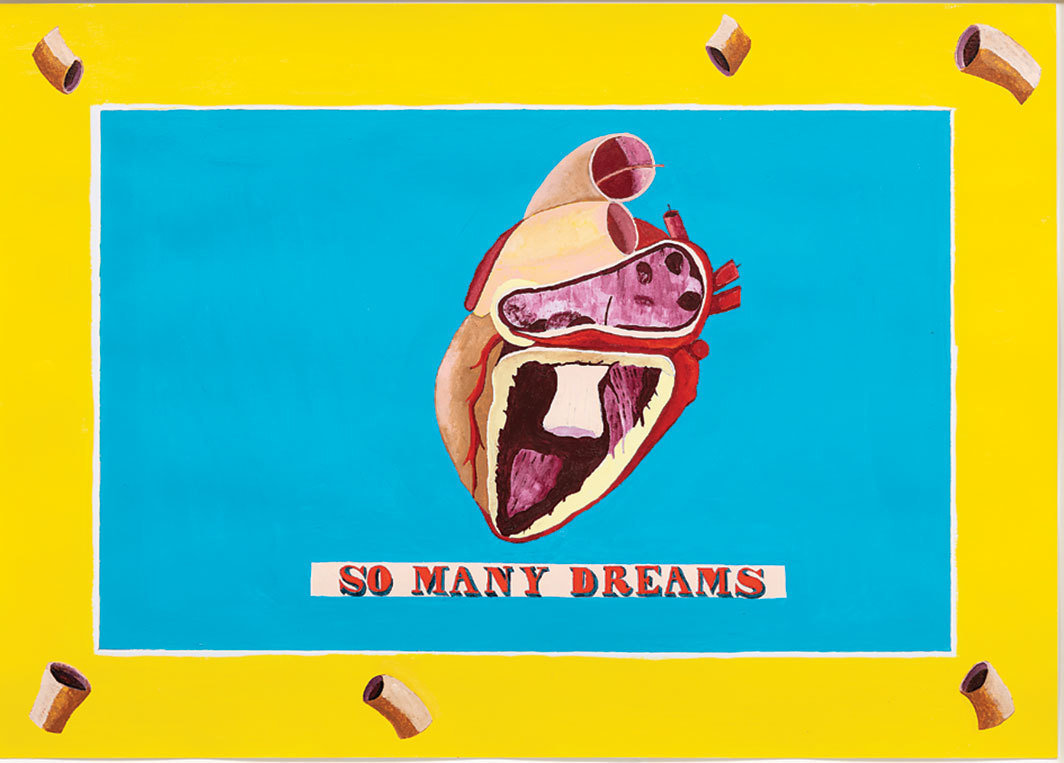
很多参展作品处理的都是历史记忆。在位于莫阿比特区(Moabit,柏林永远“即将到来”的街区之一),由老火车站改建的ZK/U艺术与城市规划中心(ZK/U Center for Art and Urbanistics),祖利凯·肖德赫里(Zuleikha Chaudhari)将纳粹同谋、印度民族主义者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的文章跟最近政府官员在新德里的宣传演讲放到一起。表演在一间黑暗的录音棚里进行,鲍斯人生故事的重现与演讲片段互相交织,让观众见证了对历史记录的再度记录。该录像阐述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似乎难以根除的特性,展示了该意识形态如何轻易就能变形发展,以不同的伪装、在不同语境下再度复活。阴冷的地下室里,托尼·科克斯(Tony Cokes)的作品一边大分贝播放着流行歌曲,一边放映关于美国不平等现象和政治迫害的事实。所用素材大部分都是我们熟悉的(谁不知道共和党想取消医疗保险?),但是比如《Evil.27.Selma》(2011)里放了莫里西(Morrissey)1994年的歌曲《你越无视我,我靠得越近》,这就是一次对流行的双重利用:一方面以其魅力与文本的阴暗形成对比;另一方面也提醒观众,最受追捧的偶像破坏者往往最容易变成排外运动的仆从。
德国艺术研究院(Akademie der Künste)里展出的作品更加多样化。在这座对德国艺术教育至关重要的粗犷主义风格的建筑里,费耶丽·巴耶茨(Firelei Báez)用一道横在入口外的巨型拱门,将德国王宫“无忧宫”(Sanssouci)的故事与海地一座同叫“Sanssouci”的城堡以及一位同名革命领袖糅合到一起。萨拉·哈克(Sara Haq)的芦苇从展场各处的地板下“破土而出”,它们温柔的侵蚀令人联想到废弃大楼里植物的蔓延(这件作品有个好玩儿的名字,叫《移:植》[Trans:plant, 2018],同时它也呼应了巴耶茨作品中的建筑主题)。在《再次》(Noch einmal,2018)中,马里奥·斐弗(Mario Pfeifer)重现了2016年5月发生在一家德国超市里的治安小组袭击事件:几名白人抓住一名患有癫痫病的难民,并用扎带将他绑在一棵树上。名叫沙巴斯·阿尔-阿齐兹(Schabas Al-Aziz)的这名受害者后来被人发现冻死在一片树林里。该案件不到四个小时就被驳回;辩方认为加害者一方的行为是出于“公民勇气。”斐弗在一群陪审团成员面前,用典型德国犯罪类节目的表演手法重现了事件前后。他主要的优点在于他讲故事所花费的时间。四十五分钟一步一步的讲解逐渐展开了不公正的程度。来自陪审团令人感动的诚挚回应更是进一步突出了罪行的严重性。其中一名本身就是德国移民的女性对着镜头说:“这些男人的脸让我充满恐惧。”
![迪妮欧·塞舍·波帕佩(Dineo Seshee Bopape),《无题(关于神秘的不稳定性)[感觉]》(局部),2016-18,砖头、灯光、声音、录像、水、餐巾纸、Jabu Arnell, Lachell Workman, Robert Rhee的作品. 展览现场,KW当代艺术中心. 摄影:Timo Ohler.](http://www.artforum.com.cn/uploads/upload.000/id11645/article02_1064x.jpg)
KW当代艺术中心(KW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五层空间的展览在呈现上更加碎片化。迪妮欧·塞舍·波帕佩(Dineo Seshee Bopape)的装置占据了一间大展厅。橘黄色的灯光照在一堆砖头上,一台小小的监视器播放着妮娜·西蒙(Nina Simone)的演唱会录像。这件作品暗示了我们所处时代遭受的破坏,但造成这种破坏的力量却没有看上去那么强大;贾布·阿内尔(Jabu Arnell)用硬纸板做的一个拆迁球悬挂在装置当中。在《幻想第二卷,俄狄浦斯》(ILLUSIONS Vol. II, OEDIPUS, 2018)中,格拉达·吉隆芭(Grada Kilomba)巧妙地将俄狄浦斯的故事重述为对殖民主义的评论。其他作品则是看展签比看现场更精彩。表演艺术家奥奎·奥库珀克瓦西里(Okwui Okpokwasili)以尼日利亚一种叫做“坐在男人头上”(Sitting on a Man’s Head)的抗议舞蹈为原型,编排了一场表演,这种表演原本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一群妇女聚在殖民地官员的院子里唱歌,一直唱到该官员出面解决她们的问题为止。即便有一组起“活化剂”作用的舞者在里面跳舞,为该作品搭建起来的简单空间与作品描述相比,还是让人感觉太过空旷和清淡。
策展团队反复强调本届双年展既不说教,也不说明。“我们正在经历战争,”恩科伯在开幕式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然而,战斗性并非此次展览背后的驱动原理;相反,某种学院式的羞怯笼罩了一切。展出的作品完全跟不上门外现实事态发展的恐怖与紧迫。在双年展开幕头几个星期,德国内政部长开始对移民进行一系列露骨攻击,同时加强边境管控,基本等于终结了德国对地中海地区难民的救助政策。在KW的展厅内,空气是平和而冷静的。
玛德莱娜·施瓦茨(Madeleine Schwartz)为《纽约书评》以及其他刊物撰写欧洲政治及文化相关文章。
文/ 玛德莱娜·施瓦茨 | Madeleine Schwartz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