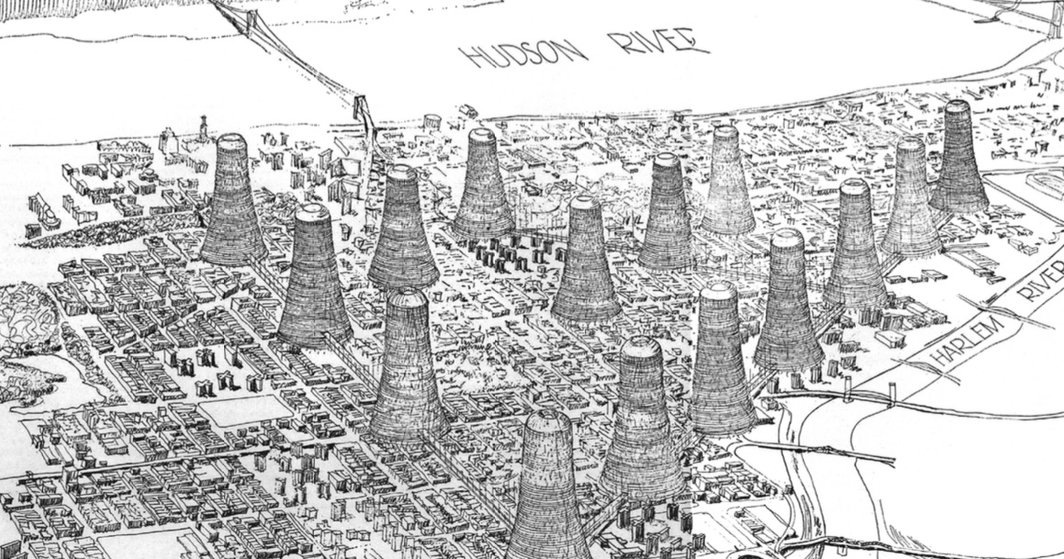
所有的暴乱都闪耀着世界-历史的光芒,但因乔治·弗洛伊德而起的反抗则格外耀眼,因为它们打开了世界的大门。暴乱通过证明其可能性从而拯救了社会生活,我们在户外戴着口罩站在一起,并没有被疾病击中。这些暴动重建了居所的“外部”,同时也激活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部”。在暴乱前,甚至在疫情前,我们的生活与他人的生活似乎是完全隔离开的。
外部的打开是抗议活动的一个偶然效应。尽管这些抗议是一种悼念,但一场暴乱也是一个人群不受控的互相作用的力量,这在大量的人聚集在户外时就会产生。通过创造公共空间的新用途——通过破坏街道设施,通过将玻璃窗击成碎片,通过让高速公路瘫痪——这些暴乱证明了,所有的物都可以因集体行动而彻底改变其性质。一场暴乱无法让死者复活,但是它却可以让城市死寂的空间重生,让街道重新充满活力——“我们的街道!”就像是那些高呼里所说,这种民权-无政府主义的陈腔滥调在此刻是有意义的,街道的确被用作了他途。那种占领街道的生理性冲击甚至在日常交通恢复后仍然挥之不去。
到外面去是重要的,因为当你直接触碰到空气,当你看到人群,你的感受会不同。社会生活恰恰是革命应该处理的问题,所以警察短暂而肮脏的历史不仅仅因控制奴隶而出现,也因控制人群而出现。不同于暴乱或是艺术的想法,警察是专门用来消灭的,在他们作为警察行使权力时他们根本不是作为人存在的。他们反对逃脱,反对聚集。街道是劳动阶级社会生活的框架和脉络,而警察限制了他们可以在那里获得的愉悦。警察的工作就是粉碎“非正式”的街道生活及其所有表现:街边摊、游荡,所有对他人无害的“罪行”,而警察将种族主义投射其上,并且给予其合法性。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自焚点燃了阿拉伯之春,他是一位街边小贩;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也是。禁止游荡也是同样的规则,这使得身处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是一种犯罪。
在纽约,六月的第一周,市政府规定所有人必须在晚上八点前回到室内,于是一到八点钟,所有人都开始高呼“去你妈的宵禁”。那些没有回家的人就留在户外。没有人有意表现勇敢;他们仅仅是被集体的力量赋能了,这形成了勇气。警察想要阻止成千上百的人无规律地在城市各处聚集,但他们失败了。那个月,纽约市民差一点就击败了纽约警察。没有人使用武器,我们有的仅仅是个人的在场,还有火。
在暴乱之后,冬天到来之前,纽约一片沉寂。结果在外面,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夏天时,公园里充满了人和喧闹的音乐。烧烤的烟,叶子的烟,还有Pop Smoke的音乐勾勒出了纽约社群幽灵般的存在,在被政治抹除后如同鬼魅一样的第二人生。我与在app上结识的人一道在夜间散步,突然之间突破了触摸的神秘界限。在雅各布里斯海滩,我们在深夜游泳,打扰了某些人的交欢。看到人们进入彼此是浪漫的。在展望公园,我们躺在洼地上,仰望天空被日落吞噬。“我每天都在外面”,我的一个朋友在10月的时候告诉我,“从暴乱的第一天开始。”随着冬天的来临,我们又发现了火,这就如同回到了最原始的状态,历史尚未开启之时。我对暴乱的记忆即是人类超级强大的适应性的一幅图景。
共产主义是一种远离政府而亲近彼此的运动。街上发生的所有一切都是一种学习,因为这造就了人的接触。无论是对话还是对抗都是真正的教育。征兆和奇迹都还在,死去的人的名字被涂鸦在建筑物上,破碎的窗户就像是一个令人窒息的世界的呼吸孔。政府所做的一切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有些时候,你甚至觉得政府可以在一夜之间蒸发殆尽。当年轻人们说,纽约会呼吸,或者,现在就要废除警察,他们是认真的——他们走到外面去,待上几个钟头,他们即是当下自由之处境的形象。
汉娜·布莱克(Hannah Black)是一位居住在纽约的艺术家和作家。
文/ 汉娜·布莱克
译/ 郭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