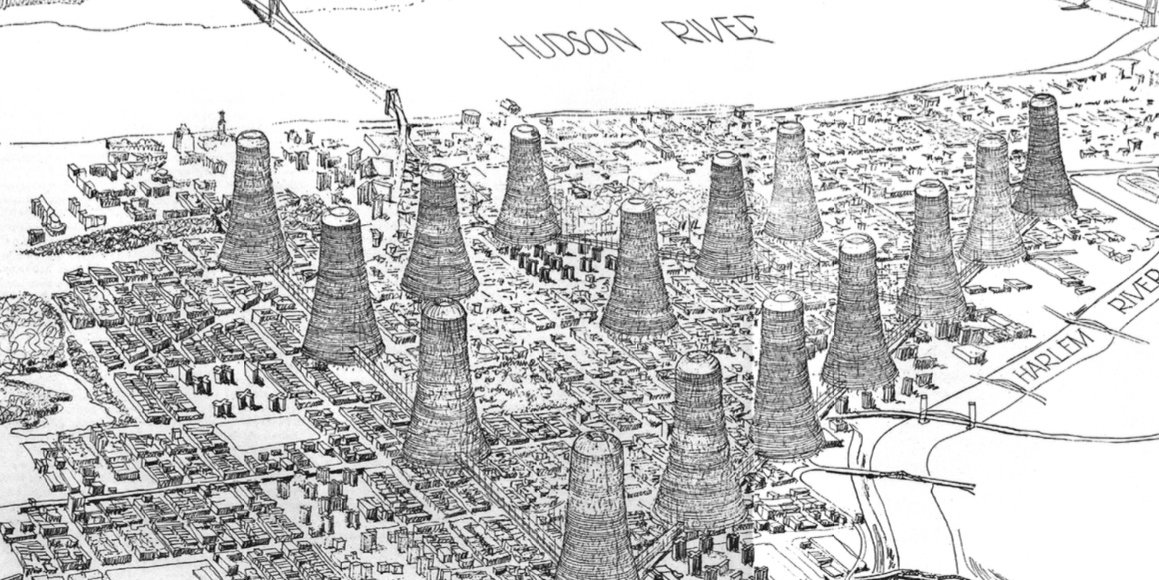超能力
电影《黑豹》(Black Panther)于今年二月上映。也是在二月,赫尔曼·贝尔(Herman Bell)——他是前黑人解放军(Black Liberation Army)成员,黑人解放军是由黑豹(Black Panthers)成员组成的一个地下黑人权力组织——在度过了45年的牢狱生活后获准假释。《黑豹》在上映的一周内票房达到二亿四千一百九十万美金,这对于迪斯尼公司来说可谓不薄的利润。而贝尔的听证会则经历了延期和一个无比漫长的审议过程,不过最终还是迎来了结果,他于三月中旬获得了假释权。另外仍有15位前黑豹成员目前尚关押在狱中;一些人已经在服刑期间去世,他们所有人都经历了虐待和折磨,包括关禁闭及拷打。在写作这篇文章的同时,纽约的警察组织纽约市巡警福利协会(Patrolmen’s Benevolent Association)还在竭尽全力地对贝尔的案子提出异议,希望能够撤销判决结果。
警察和政客们搅合在一起,仅仅因为对黑人暴力的抽象恐惧而力图剥夺一个七十岁老人的自由,这等诡异景观在《黑豹》上映的背景下看起来更加鲜活生动。两个事件的巧遇惊动了那些古老的鬼魂,如果说我们此刻还算不上鬼魂缠身的话。《黑豹》的导演瑞恩·库格勒(Ryan Coogler)的处女作《弗鲁特韦尔车站》(Fruitvale Station,2013》是关于加州奥克兰的奥斯卡·格兰特(Osc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