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摄影作品也许永远会受到尺寸调整的左右,但《忐忑》(Apprehension)是那种无论在哪看到都能够保持同样强度的图像之一。画面中央是一个放大的年轻亚洲男性的脸,他像握住一根短棍一样握住电话听筒,额头上有深深的抬头纹,一绺头发垂在眼前。两根延伸到眼角的凌乱发丝看起来像是裂痕,仿佛预示着某种即将发生的解体或破裂。被来自画面下方的不明光源照亮的脸庞呈现出强烈的光影效果。他的肌肤是充满戏剧感的玫瑰色和金色,让人想起二十世纪中期艳丽色情的通俗插画,或是与世俗戏剧融合的巴洛克宗教绘画。“过熟”,我想到了这个词。有什么东西即将坠落。

创作于1942年左右的《忐忑》出自西雅图的美籍华人艺术家杨超尘(Chao-Chen Yang)之手,他曾在1940年代担任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外交官。这张照片的构图与他第二年拍摄的一张题为《年轻中国游击队员》(Young Chinese Guerilla)的作品相呼应,后者是经过精致的好莱坞式改造的政治宣传图像,是“高昂士气”的电影表现:一个电影演员长相的年轻东亚裔男子转过头,将目光投向一个看不见的更高的权威。杨超尘曾在RKO电影公司当过学徒,期间掌握了电影摄影,并希望能在电影界有所作为。也许是受这段经历的影响,《忐忑》中充满黑色电影(film-noir)的表演性[1]。照片定格在主人公(或嫌疑人)在一个不正常的时间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的时刻。他赤裸上身,耳朵紧贴听筒,摄影机也以同样的方式贴近他的脸,距离如此之近,以至于他的脸似乎被推进了镜头里。血液涌向男人的脸颊,他的表情似乎凝结成悬而未决的情绪的集合体,用“忐忑”这样模棱两可的词来描述似乎刚刚好。
即便冒着过于接近低俗封面照的风险,杨超尘在表现黑色电影的情感张力上确实抓住了某些关键问题。年轻男子始终未能完全从阴影中浮现出来。这也是关键点之一。他总是会被怀疑的黑暗拉回去。两年前,杨超尘在温哥华拍摄当地名胜时因为被怀疑是“日本”间谍而遭到加拿大警方盘问[2]。1942年,罗斯福签署的第9066号行政令导致成千上万的日裔美国人遭到大规模拘禁,更让他多年之后仍然记得上述经历。当时的西雅图市长厄尔·米利金(Earl Millikin)曾经表示,这些“外国敌人”将“带来比珍珠港更为严重的破坏”,以此为背景,作品标题其实是个双关语,因为“忐忑”往往是因为担忧在法律规定下被逮捕或是被扣留(原文apprehension既有忐忑、担忧,也有逮捕的意思)。在很多方面,这件作品都预示了1950年代新中国成立并参加朝鲜战争之后席卷美国的反华情绪。最终离开外交部门成为全职摄影师的杨超尘必然深深卷入了当时移民政策的漩涡中。他曾是众多中国海员的中间人,他们在美国移民官那里的种种遭遇既如同黑色喜剧,也代表了最严重的心理折磨[3]。这些海员虽然被许诺能够以多年的政府服务换取美国永久居留权,但他们一直生活在被驱逐出境的恐惧中。如果说把《忐忑》中的年轻男子视为这些海员的化身有点牵强,但说他预示了1949年杨超尘自己的心理状态也许并不为过。当时他也面临被驱逐出美国的命运,而且因为新中国的成立,他这样背景的人如遭遣返无疑难逃一死。

撇开对其隐含意义的猜测,《忐忑》直观地表现出处在难以避免的伤害来临前的不确定状态中的感觉。而且,这幅画的展览尺寸介于中型和大型摄影肖像之间——这通常是夫妇合影或小型全家福的最佳尺寸,但在这里取而代之的是一名男性的单人肖像,他的身边既没有其他家庭成员,也没有朋友。男人头发的黑曜石光泽和背景的暗黑色之间有足够的差异,能够区分出人物和背景,但环境的黑暗并没有完全与这个男人的身体分离,两者之间的一层薄薄的阴影对于描画轮廓来说过重了,它提醒的是黑暗对身体的索要。此外,这张照片紧凑的裁剪既可以被解读成一种封存行为,也是一种叙事手法,诱使我们看到这个人从夜幕之中小心翼翼地浮现。
早在1970年代关于彩色摄影的艺术地位的争辩达到顶峰之前,杨超尘就已经开始尝试用色彩将照片中的光线与绘画及其他艺术媒介中对光线的处理方法联系起来。(原本的底片是黑白的,杨超尘用当时新的Flexichrome工艺对照片做了手工上色。)我们在《忐忑》中看到的饱和光芒可能只是来自一个电灯泡,但画面中的颜色让它看似来自实际意义以及比喻意义上的爆炸物。我不禁想起了古元《人桥》(1948)右半部分仿若珊瑚的爆炸场景,这幅广为人知的木刻作品描绘了解放战争中军队从浮桥上渡江的场景。 虽然在世界的另一端的杨超尘并没有参加从1927年持续至1949年的国共内战,但他或许同样见证了足够多的战斗,以至于他能够让橙色看起来不再是简单的橙色。强烈的光线将杨超尘模特的肉体变成黑暗和明亮相交的斑块,宛如古元画中火光映照下地狱死亡图景的镜像。我这样说也许有些僭越,但上述共鸣已经强到足以让人发问,亚洲的身体是否只有在紧急状况下才会被看见:令人目眩的闪光灯、残酷的炼狱、炸弹下的地狱之火,甚至是审讯室的头顶强光。

我认为,杨超尘之所以用光在年轻男子脸上打出一片半月形阴影,是出于一种对不确定的未来的担忧。男子的嘴唇微微张开,似乎要发出一个声音或一个音节。但我们听不见他。他不说话,所以是一个合适的猜测对象,就像珍珠港事件后几周《生活》杂志上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如何区分日本人和中国人》中出现的图解面孔。《生活》杂志的图片试图告诉美国人如何认出“真正的”敌人,《忐忑》却尖锐地提醒观看者,美国的亚裔群体在铁一般的沉默中独自面对危险。这件描绘了“听”这一行为的作品凸显了道听途说和含沙射影如何能变成伤人的武器。图像提示了可见性如何依赖于什么被听到,谁在说话,以及为何目的。

2008年,《忐忑》在旧金山德扬美术馆(de Young Museum)举办的重要展览“亚洲/美国/现代艺术:潮流转移,1900-1970”(“Asian/American/Modern Art: Shifting Currents, 1900–1970”)中占据了显著的位置。我认为博物馆这么做是因为它接近那种以明暗对比(chiaroscuro)为核心的绘画;《忐忑》应该归属于将时间具现为一系列分开的、不规则发生的时刻的图像创作的脉络。但作品在展览里的显要位置也强调了焦虑是亚裔美国人的决定性状态,鉴于今天的反亚裔暴力事件,当时将其选为展览核心作品的决定非常有预见性。2021年,《忐忑》再次凸显出住在美国的亚裔人群因为持续不断的对亚洲人的盲目指控而一再面临的困境。杨超尘的作品成为另一段针对亚裔暴力的艺术参与史的重置点。《忐忑》中盯着画外某处的年轻男子就像1964年平静地坐在舞台上的小野洋子,男女观众走上台剪下或者撕扯下一块她的衣服,法律学者伊克斯塔·玛雅·莫瑞(Yxta Maya Murray)称之为“一种‘证明’形式”,证明那些尚未被法律承认的攻击形式,但无数女性为此付出代价且无望得到救济[4]。年轻男子的眼睛也为谢德庆睁大,后者在进行《一年行为表演1981-1982》中被纽约警察逮捕后紧闭双眼与之对抗,并成功抵挡住暴力业主的攻击。当年轻男子拿起电话时,他被车学庆(Theresa Hak Kyung Cha)1982年遭恶性强奸和谋杀的消息所震惊,谢德庆也是在同年遭到袭击,这一事件既是对过去暴行的提醒,也是对尚未发生的悲剧的警示。而模仿抛光木头效果的电话听筒的表面质感与形状都让人想起法官的小木槌,这个物件既象征了仪式的开始,也代表最终的决定。听筒过大的影子刚好触及模特的下巴,这不仅意味着迫在眉睫的判决,也暗示着其后果将在亚洲人的身体上上演:他们将永远被困在宣判为有罪的炼狱之中。让这些身体无罪释放,从而将我们自己从互相怀疑的折磨中解脱出来——这就是《忐忑》敦促我们要做出的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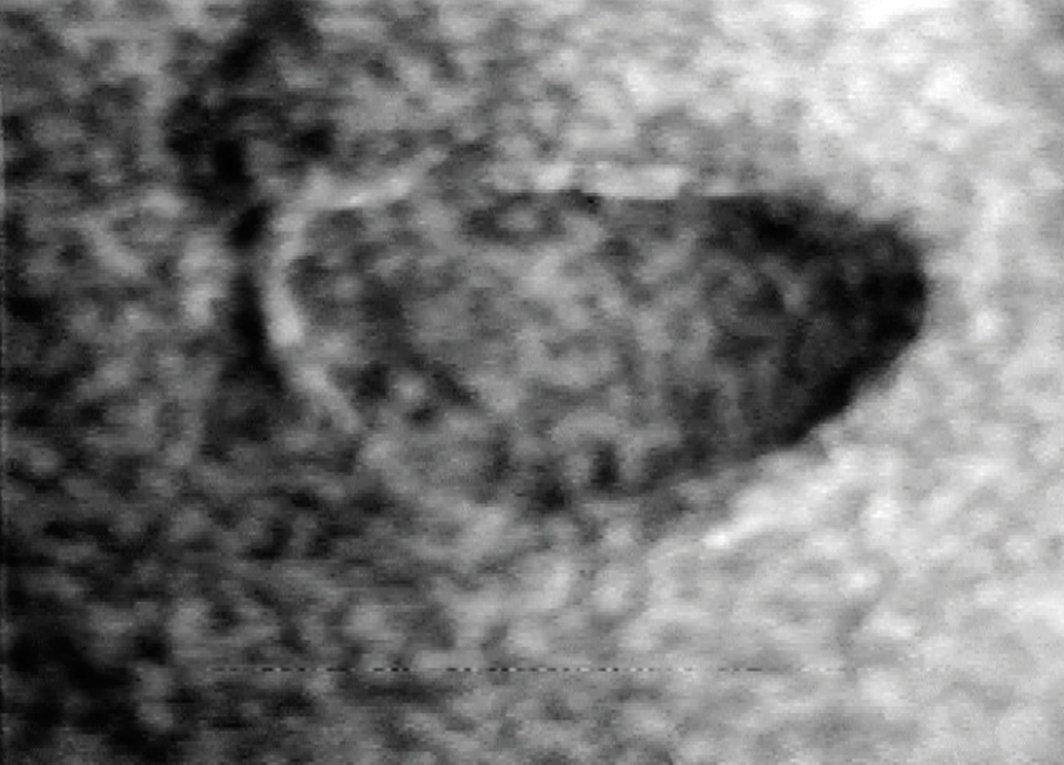
奇廷泫(Joan Kee)是密歇根大学艺术史教授和威廉姆斯学院罗伯特·斯特林·克拉克访问教授,她也是《Artforum》杂志的特约编辑。
作者感谢西雅图卡斯卡迪亚美术馆(Cascadia Art Museum)策展人大卫·马丁(David Martin)的协助。
注释:
1. Kazuko Nakane:《交织光与影:太平洋西北地区地区的早期美国亚裔摄影师》(“Interweaving Light with Shadow: Early Asian American Photographers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见《他们用心作画:美国亚裔艺术家先驱》 (They Painted from Their Hearts: Pioneer Asian American Artists),Mayumi Tsutakawa编,西雅图:Wing Luke Museum, 1994,56页 。
2. 杰克·莱特(Jack Wright):《来自东方的艺术家》(“Artist from the Orient”),见《Camera 67》第8期,1945年8月,19页。
3. 第85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参议院报告254,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Shao Fong Sha》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57,2-5页
4. 伊克斯塔·玛雅·莫瑞(Yxta Maya Murray):《切片:小野洋子的艺术以及美国强奸法》(“Cut Piece: The Art of Yoko Ono and the Law of Rape in the United States”),见《法律与文学期刊》(Law and Literature Journal,即将出版),ssrn.com/
文/ 奇廷泫
译/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