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卫艺术博物馆(Avant-garde Museum)这个概念有一些令人挠头的矛盾之处——因为前卫运动不是想与机构背道而驰,直接与生活接触吗?(但与此同时,为何人们会认为机构是与生活相悖的东西也一直是另一个让我挠头的问题)。在1909年发表的未来主义宣言中,F·T·马里内蒂(F. T. Marinetti)承诺要摧毁博物馆和其他布满灰尘的知识场所(“图书馆和各种学院”),以便为速度和活力腾出空间。但十年后在俄罗斯,卡西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用了和马里内蒂类似的语言(“我们要行动起来反对旧事物,将它们永远埋在墓地里,把我们脸上任何与过去相似的东西擦掉”)来想象一种“博物馆网络”,使“最好的创造性作品”能够“深入国家内部”,并“为重塑生活中的形式和工业中的艺术形象提供动力”。是的,马里内蒂和马列维奇都同意艺术必须摆脱历史的阴影,但至少对马列维奇来说,现代性并不意味着夷平过去,而是要重建机构以传播当下的信息。

《前卫艺术博物馆》(The Avant-Garde Museum)讲述的就是这个奇怪结构的故事,这是一本最近由Agnieszka Pindera和Jarosław Suchan编辑的文集及展览图录,由波兰罗兹艺术博物馆(Muzeum Sztuki)出版,这间机构本身也是这本书试图记录的前卫运动的产物。(相关展览将于今年10月在该博物馆开幕,以庆祝“波兰前卫艺术一百周年”)。这本六百多页的书包括12篇学术论文,以及大量的原始资料和彩色复制品,研究案例涵盖了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收藏机构,从收藏家兼画家凯瑟琳·德雷尔(Katherine Dreier)和艺术家杜尚及曼·雷创建的“无名社团”(Société Anonyme),到俄罗斯构成主义艺术家柳博芙·波波娃(Lyubov Popova)和亚历山大·罗琴科(Aleksandr Rodchenko)参与领导的“艺术文化博物馆”(Museums of Artistic Culture)。虽然国际主义是前卫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它关于传播的梦想是其使命的一部分,无论是以独立杂志还是示威的方式——但因为前卫艺术博物馆是实体化的,于是所处国家和政治背景的问题变得很紧迫。比如,人们不禁会问,由美国钢铁巨头继承人支持的“无名社团”是否真的能够与后者这个受苏联国家支持、试图将权力转交给“工人和农民”并将博物馆改造成“艺术发明”实验室的项目相提并论?而这两个项目又与卡塔日娜·柯布罗(Katarzyna Kobro)和瓦迪斯瓦夫·斯特泽敏斯基(Władysław Strzemiński)在波兰创办的国际现代艺术收藏(International Collection of Modern Art)——汇聚来自四面八方的的现代主义作品,以塑造现代波兰民族身份——有多少共同之处?所有的政治都是在地性的吗?所有的艺术也是如此吗?我们在这本书中看到的就是,当一个共同的想法、共同的理想主义落到实处时会是什么样子。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现代主义历史越来越多地透过展览的视角被讲述。这种方法使学者们能够通过将艺术品回溯到对应的时间和空间里,加上特定的公众群体和展示系统,从而对有关艺术自主性的普遍观点进行反驳。当然,展览对现代性来说也是一个很合适的形式,因为现代性与沙龙一起出现,还常常与贸易展览和世界博览会交织在一起,它必然是一个不纯的集合体,骨子里带着短暂性和场景性。但对展览的强调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对现代机构的调查——也就是说,问题不仅仅是展出什么,还有保留什么。展览史已经做了很重要的工作,但我们今天需要的(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是机构史。虽然已经有一些针对机构的专题展览和图录,比如充满唯心论气息的“非客观绘画博物馆”(Museum of Non-Objective Painting,即现在的纽约所罗门·R·古根海姆博物馆)和本身就是神智学产物的“无名社团”,但前卫艺术博物馆这种类型还从未被有力地理论化处理过。这本书就是一个完美的开始。

虽然书中讲述的历史大多已成为经典,但这本书的优势之一是它能够重塑我们自以为已经了解的艺术家和艺术实践。比如埃尔·利西茨基(El Lissitzky)的《抽象柜》(Kabinett der Abstrakten)就是一个关键例子。在汉诺威和德累斯顿的博物馆中,利西茨基通过在展厅墙面安装金属条和可移动组件创造了运动空间,从而引导观众参与到艺术品的布置中来。对作品布置的关注也体现在罗兹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作——斯特泽敏斯基1948年的红、黄、蓝色的《新造形空间》(Neoplastic Room)中,这是一个蒙德里安风格的空间,与其中展示的艺术作品相呼应。这两个项目都让人想起“珍宝柜”传统,这种前启蒙时代的展示模式对现代博物馆的理性秩序进行了反击,但很多前卫艺术博物馆的支持者们寻求的是更加未来主义的模式,比如委托利西茨基制作《抽象柜》的亚历山大·多尔纳(Alexander Dorner),现在他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展览形式的伟大创想者之一。虽然大多数前卫艺术博物馆都是由艺术家运营的,但多尔纳属于少数偏爱大胆新颖风格的管理者之一,他首先在德国汉诺威领导那里的州立博物馆(Provinzialmuseum),后来移居美国,成为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博物馆馆长。在他1947年出版的《超越“艺术”之路》(The Way Beyond “Art”)中,他宣称现代博物馆是“一种发电站,是新能量的生产者”,由“轻型现代材料”和“道德力量”组成。然而,像很多前卫项目一样,多尔纳的理想博物馆只停留在了纸上,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想要在一间新博物馆中结合新艺术形式和新视野的愿望开始显得过于英雄主义,或许也过于夸夸其谈了。
每一种宏大的创想,都对应着琐碎的现实。而且,不管你喜欢与否,当你开始研究博物馆时,你必然会进入官僚主义领域,可能会接触到相当世俗的东西。因此,也许这本书被设计成类似电话薄的样子正是恰到好处的。书中很多文本包含了非常细微的细节,几乎传达出一种法医式的严谨。例如,我们了解到,利西茨基指定要用1.5 x 0.04英寸的铬镍合金条。但也许这些看似晦涩的细节提醒了我们,建立机构的工作无论多么激进,都难以避免地会包括乏味的部分,在白立方背后的隔间和会议室里发生的事情与白立方中的内容同样重要。(“创造一件好的艺术作品还不够,” 斯特泽敏斯基写道,“还必须创造合适的条件,让作品能够产生影响。”)事实上,随着今天各种博物馆工会的成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艺术机构不一定需要成为一个牺牲的空间;相反,它可以是一个权利得到保障的地方,一个资源被集中和分配的地方。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新一代艺术工作者们对流程图、工资单和资金筹集的仔细检查,就像前人在争论艺术媒介特殊性、创作方法和“表征危机”时的态度一样严谨。当他们的斗争之后被书写和历史化时,他们会不会突然感到不好意思?他们会不会反而希望“作品”——他们组织的演出和展览——被放在首位?也许并不会。我们对艺术机构的理解正在往更为全面的方向迈进,展览场所与背后的工作区越来越不可分割。(黑格尔的图式已经取得了进展:今天的艺术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制度化的。)就像对待咖啡一样,我们想让艺术既是富有创意又是“公平贸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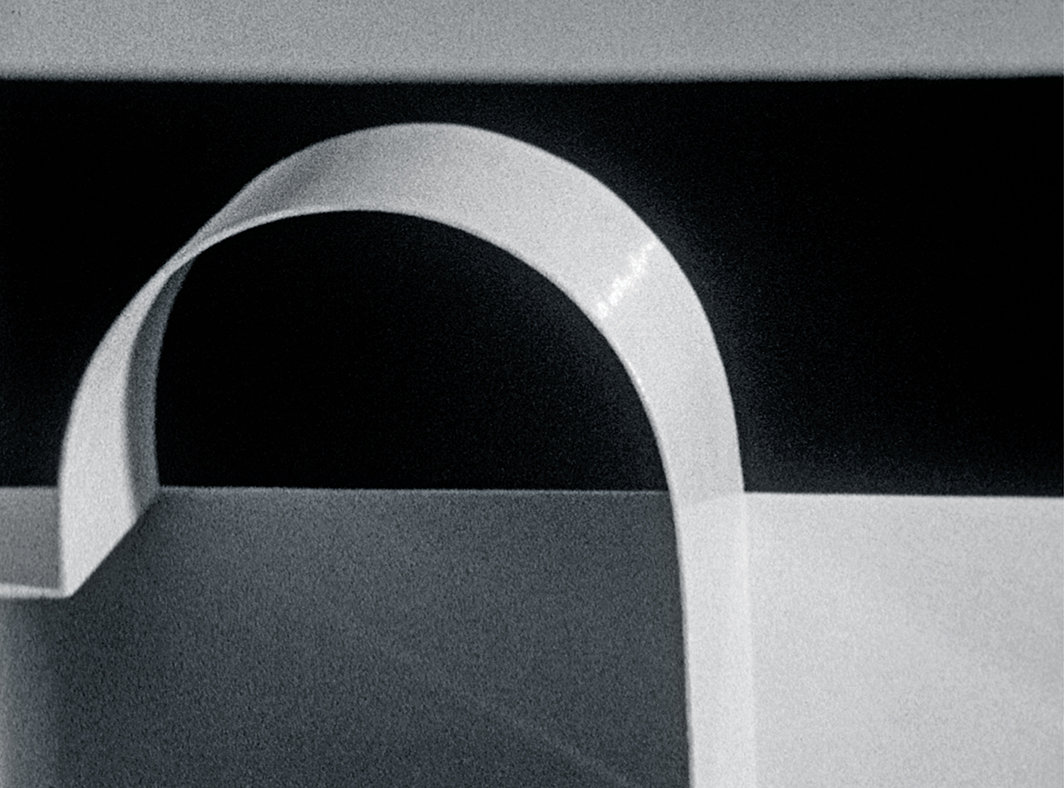
虽然这本书关注历史上的前卫运动所塑造和培养的机构网络,但时间范围并没有超过战后,也没有涉及欧洲以外的地方,这让我好奇接下来的篇章会怎样。书中记录的一些机构已经不复存在,并捐出了它们的作品(比如“无名社团”的收藏在1941年转交给耶鲁大学),仍在运作的一两间则通过反复的怀旧、自爱和革命热情来试图重新点燃它们的遗产。它们也成为有档案情怀的当代艺术家的朝圣之地——比如R·H·奎特曼(R. H. Quaytman)2019至20年的绘画系列“第35章:不动的太阳”(“Chapter 35: The Sun Does Not Move”),以及Union Gaucha Productions在1998年创作的影片《幻肢》(Phantom Limb),两者都关注了罗兹艺术博物馆中柯布罗和斯特泽敏斯基的作品。但总的来说,就像“艺术文化博物馆”的梦想一样,成千上万前卫艺术博物馆的梦想(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真正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遗忘中,这也正是这本书的重要之处。这是一个尚待挖掘的档案。

这本书也要求我们对那些可以称之为新前卫艺术博物馆——也就是追随这些已经成为神话的博物馆的脚步的机构进行思考。虽然20世纪60年代的梦想之一是离开博物馆,到外面的环境中去,但狡猾的艺术家主角们也有一个与此相反的趋势,那就是炮制出对艺术机构进行隐晦反思的假博物馆。比如,想想马塞尔·布达埃尔(Marcel Broodthaers)从1968年开始创作的献给鹰的博物馆,全是标示和木箱,但没有固定地点。或是克劳斯·欧登伯格(Claes Oldenburg)1965年的《老鼠博物馆》(Mouse Museum),这个有着米奇耳朵形状的独立结构中装满了奇形怪状的小玩意(在1977年芝加哥的展览中还增加了射线枪侧厅)。但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些项目在规模和野心上都比之前的要小很多——这些都是自觉的反英雄式博物馆——回过头看,我们很难不在研究它们时感到一丝失落。虽然它们非常聪明且富有敏锐性,但它们也展现出战后时代急剧减少的激进实践可能性。
但也有一些例外。比如,我们可以将位于纽约哈勒姆的工作室博物馆(Studio Museum)置于前卫艺术博物馆的传统中进行思考。工作室博物馆被设想为一个生产、存档和展示的空间,它成立于布达埃尔创作鹰之博物馆的同一年,最初位于纽约125街一家酒类商店的楼上,试图为艺术家群体以及更大的社区开辟一个空间。博物馆创始人认为,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实际上,进步的机构正是其门外的所有进步可能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很多在前卫谱系下运作的博物馆都继承了这一遗产,无论是洛杉矶的地下博物馆(Underground Museum)还是纽约的艺术家协会(Artist’s Institute),或是荷兰乌得勒支的卡斯克艺术机构(Casco Art Institute)。(在2013年出版的《激进博物馆学》中,克莱尔·毕晓普认为位于埃因霍温的Van Abbemuseum和位于卢布尔雅那的Metelkova当代艺术博物馆也是先锋机构候选人。)这些小型机构在历史前卫运动的英雄主义和新前卫派的机敏之间分庭抗礼,以谦逊、敏锐和真诚的态度面对现实。虽然书中有一篇文章设想当代博物馆应该有“社会行动主义”部门,但并非所有这些机构都会如此有规划地定义它们的使命。也许,艺术中一些东西最好还是保持模糊。

也许今天更为紧迫的问题是,人们想知道传统的博物馆能否变成前卫的,私有化资本能否像格林童话里的侏儒斯蒂尔金的稻草一样变成公共资源,永久收藏能否真正以公共信托的形式存在。很多人现在都在努力尝试,不论是从内部(比如策展人为非常规公众群体策划项目)还是外部(社会行动者们要求机构重新评估它们的资金来源),老问题再次出现:哪里才是最有效的行动场所?现在已经很清楚,答案并不是非此即彼。这种关系是共生的。机构及其外部形成一种呼唤和回应的关系,就像博物馆众多组成部分(策展人、清洁员、教育工作者、董事会成员)也形成了自己的生态系统,会有不和谐、冲突、妥协和竞争的时刻。所以我们不要放弃这个梦想。前卫博物馆已死,前卫博物馆万岁!
亚历克斯·基特尼克(Alex Kitnick)在纽约州巴德学院教授艺术史。
文/ 亚历克斯·基特尼克
译/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