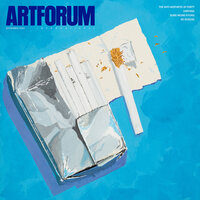1977年,我第一次见到伊利亚·卡巴科夫(Ilya Kabakov)时,他已经是莫斯科体制外艺术圈的核心人物。他不仅是受人敬佩和仰慕的艺术家,也是对艺术发生过程深具洞见的评论家。他的工作室位于莫斯科市中心斯雷滕斯基大道(Sretensky Boulevard)一栋六层楼房的顶层,这里也经常举办哲学和艺术史讲座、读诗会,是艺术家和文人们的非正式聚会场所。要去他的工作室,必须从一楼一直爬到顶楼(没有电梯!),楼梯灯光昏暗,有些地方还堆满了垃圾。但是,通常紧张任性的莫斯科艺术家和诗人们却很乐意付出努力,因为等待他们的是卡巴科夫的热情招待——以及马上可以加入的亲切交谈。卡巴科夫经常邀请朋友们来看他的新作。他不仅会展示作品,还会发表评论。他也欢迎来自参观者的评价——这甚至是一个隐含的要求。
卡巴科夫在西方世界认知度最高的是他创作的大型装置作品。这些装置都具有一些可辨认的共性特征:通过动用大量图像和关于这些图像的评论,在结构上建立起叙事性,将观众置于某种必须接受和遵守的秩序中。我认为,如果不考虑艺术家在苏联解体和移民美国之前创作和展出作品的语境,就很难理解和正确评价这些装置的独特性。在苏联时期,卡巴科夫曾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儿童图书插画家。他绘制了150本在全国广泛发行的插画书,但却不能公开展示他自己的艺术作品,因为后者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惯例。当时,体制内和体制外艺术圈之间的界线十分明确:艺术家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遵循官方格式要求,要么不遵循。选择后者的艺术家可以创作作品,但不能公开展示作品。这条分界线将卡巴科夫的创作一分为二:作为一名图书插画家,他接受了官方许可的标准;但作为一名独立的体制外艺术家,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自己的工作室内。事实上,卡巴科夫的插画是相当迷人的,并且绝对不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但他始终否认插画是他“自己”的作品。对他来说,只有那些在私人空间中向客人们展示的作品才真正是他自己的创作。

卡巴科夫的“总体装置”(total installations,他这样称呼它们)是他试图在西方艺术机构的无个性的空间中重构其私人空间的成果。1988年,他告诉我说,纽约画廊和美术馆中性、通用化的设计以及均匀的照明让他感到震惊,说他想把交与他的空间改造成他的私人领地。事实上,参观者在进入卡巴科夫的装置时,往往会产生一种步入陌生领地的感觉,它允许你迈入它的边界,却以一种令外来者费解的规则保持运作。这些装置常常生产过犹不及的视觉和文字信息,将观众置于铺天盖地的图像和文字中,导致他们在标准的观展时间内根本消化不了作品。巴洛克式的照明使观看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装置的某些部分光线非常微暗。观众面对的是一个不会被他们的凝视所完全征服的空间。有关艺术家个人空间的私密性与机构语境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卡巴科夫于第九届卡塞尔文献展在弗里德里希美术馆院落中创作的那件著名“厕所”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一个设置在公共厕所内的私人寓所。显然,它是弗里德里希美术馆的一个缩影,在这里,每个艺术家都有他/她自己的空间,参观者可以进入其中,满足他们的审美冲动。

虽然卡巴科夫总在试图构建他自己的世界,但他从不执着于图像和文字在风格上的原创性。相反,在苏联时期,他将自己的工作室变成一个反思的空间,反思自己生活其中并以一名书籍插画家的身份参与其中的日常现实和大众文化。作为一名体制外艺术家,他分析着自己作为体制内艺术家的角色。1970年代初,他通过一组名为“十个人物”(Ten Characters, 1972–78)的系列图册,确立了他的个人艺术问题意识。该系列的每本图册都像一本活页书,用文字和图像讲述着一个生活在社会边缘、其作品既不被认可也不会被保留的艺术家的历史。这些据说由每一个艺术家人物所创作的图像,都配上了他们的朋友或亲友对其作品的评论。每本画册最后均以一张宣告主人公死亡的白纸作为结尾。图册主人公所痴迷的现代主义想象,在很多方面都指涉了二十世纪现代艺术的辉煌历史。但是,画册本身的艺术表现却令人想到卡巴科夫的苏联儿童书插画美学;主人公的现代主义理想就这样被浅白的视觉语言所颠覆。文字评论见证了艺术作品必将遭受的所有可能的误读。这些图册极富诗意,浸透着真挚的艺术感染力。然而,它们也透露出主人公和卡巴科夫本人的恐惧,即:他们的作品将继续被轻视,被扔进垃圾桶,被从文化记忆中抹去。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其《论艺术作品的本源》(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1936–37)中表述了艺术作品的创作和保存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现在看来,卡巴科夫尽管希望、却从未真正相信过他的作品会被保存下来。这种害怕被遗忘背后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作为一个体制外艺术家,他是游离于苏联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博物馆系统之外的。但他更强烈地感觉到,大众社会、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在全世界的发展,已经让个体艺术表达越来越难以维系。
![伊利亚·卡巴科夫,《厕所[厕所生活]》,1992,综合材料. 展览现场,弗里德里希美术馆,卡塞尔. 第9届卡塞尔文献展. © Ilya Kabakov/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VG Bild-Kunst, Bonn.](http://www.artforum.com.cn/uploads/upload.000/id14721/article03_1064x.jpg)
卡巴科夫来到西方后创作的第一件大型装置,也被标志性地命名为《十个人物》。在这件于1988年在纽约罗纳德·费尔德曼美术馆首次完整展出的作品中,卡巴科夫将之前几十年在苏联创作的大部分作品分配给了十个不同的虚构作者,他们被描绘为孤独和离群索居的人,在苏联集体公寓的小房间内从事着各自的艺术创作。对他们来说,日常生活中拥挤的共处和彻底的内心封闭是相互并存的。在此,图册变成了房间——但却是废弃的房间,参观者面对着属于过往生活的残迹。装置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一个收集各种垃圾的男人的房间:磨损的日常物件已然无用,亦不具备任何美学吸引力。后来,卡巴科夫在他的《学校6号》(School No. 6,1993)中,再次描绘了这个苏联文化“变成垃圾”的状态,该作品曾在德州马尔法的辛那提基金会(Chinati Foundation)展出,是艺术家为数不多的仍在展出的装置作品之一。
装置作品的时间性总是让卡巴科夫恼火。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晚年越来越多地转向了绘画,因为绘画的生命可能更长久——虽然他仍旧创作装置,其中一些特定场域装置是由他和妻子艾米莉亚·卡巴科夫(Emilia Kabakov)共同创作。然而,他的绘画同样揭示了前苏联的痕迹: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政治宣传,而是一种美学和风格上的特殊共性,将苏联视觉文化中的不同方面统合起来。在苏联时期,卡巴科夫曾经不断搬演苏联文化的象征性解体和消失。但当这个文化真的消失了以后,卡巴科夫的作品却成为对这段过去的一个难能可贵的纪念。如果今天要让人们描述一下苏联的空间,那么最好的答案便是:像卡巴科夫的装置一样。
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是纽约大学俄罗斯与斯拉夫研究教授。
文/ 鲍里斯·格罗伊斯
译/ 钟若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