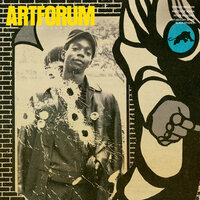去年夏天,全世界都在关注“海洋之门”(OceanGate)公司的“泰坦号”(Titan)潜访泰坦尼克残骸时消失于深海的悲惨故事,这时候,我想到了艾伦·塞库拉(Allan Sekula)。他曾在本世纪第一波泰坦尼克热时写道:“大海会回归,以哥特般的面貌出现,它被铭记又被遗忘,始终与死亡相连,但以一种奇异的无形方式。”他指的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被压抑者的复归”(return of the repressed)。塞库拉惊叹于詹姆斯·卡梅隆1997年的《泰坦尼克号》大片中的“阴郁的傲慢”,这部影片不遗余力地复活一个注定不幸的主题,构建了镀金时代的傲慢与恐怖的终极银幕形象。同样深受泰坦尼克号吸引的“海洋之门”公司创始人斯托克顿·拉什(Stockton Rush)试图将这场探险之旅打造成一场精英联谊仪式,但却拒绝对“泰坦号”廉价的船体进行安全检查。这艘注定要失败的潜水器发生了灾难性内爆,包括拉什在内的五名船员全部遇难。在深渊地带,压抑只能让你走这么远。
在塞库拉去世十年后,他的作品再度回归:他的代表作《鱼的故事》(Fish Story, 1988–95)目前正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沃克艺术中心(Walker Art Center)展出,这也是该组作品二十多年来首次在美国举办完整展览。对于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佩德罗(San Pedro)俯瞰洛杉矶港长大的塞库拉来说,新自由主义对于无摩擦无滞后经济的梦想遮掩了对海洋的持久(但被否定)的依赖。这就是《鱼的故事》的论点。这是一项在冷战结束后、在全球远洋航运扩张推动下的资本主义重建时期开展的摄影研究项目。作品以两种形式呈现,包括照片、文本和幻灯片组成的展览和一本长篇出版物。《鱼的故事》带领观众走过数十个不同地点,从韩国的造船厂到鹿特丹、香港、韦拉克鲁斯、巴塞罗那和格但斯克等港口城市,间中回到洛杉矶。这个项目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贸易路线之旅,而是从“一个加速流动的社会在某些关键方面也是一个故意放慢速度的社会”这一论点出发,探索低技术、低速度运输在全球经济中的生存问题。
虽然海洋对于数字经济来说至关重要,支撑着零售商品看似瞬时完成的传输,但也构成了塞库拉所说的“被遗忘的空间”——一个看不见也无法再现的盲点。《鱼的故事》开头的一张照片就体现了这一空白,在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渡轮上,一个小男孩站在投币式望远镜前,他的身体转向船内,似乎不知道该怎么看,也不知道该把望远镜朝向哪个方向。为了回应他的不确定,项目中最早的照片看起来就像出自一位乔姆斯基风格的私家侦探之手;仿佛用一台没拿稳的相机迅速拍下来的这些快照风格的照片揭露了通常在紧密协调下进行的美国军事和经济力量的集结。比如在鹿特丹拍摄的一张有关“沙漠风暴行动”备战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陆军第七军团的装甲车队停在一艘从斯图加特驶往波斯湾的商船甲板上。和弗洛伊德一样,塞库拉将遗忘视为一种有动机的行为:在这个例子中,关于一种新的闪电战的神话——一按按钮即可发动战争——掩盖了背后庞大的海军装备的部署,这是美国在软实力时代中的硬杠杆。

狭隘目光是《鱼的故事》的一大主题。塞库拉回忆说,“过去,港口居民被他们的感官所蒙蔽,以为可以通过视觉、听觉和嗅觉感知全球经济。各国的财富都会从航道上经过。”集装箱船的出现让这些财富得以隐姓埋名,它们全部装进不透明的金属箱中,整齐地堆叠起来运输,形状就像是“稍微拉长的纸币”。不透明权力也扩展到船舶本身,货船经常悬挂“方便旗”运营,这种法律手段允许船东将其所拥有的船舶登记在监管政策宽松的国家,从而确保了进入优质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如今,一艘船可能归日本租赁公司所有,但正式运营地在台湾,由迪拜的代理商管理,配备印度籍官员和船员,同时悬挂巴拿马、利比里亚或马绍尔群岛的国旗(这三个低监管辖区占全球商船队的40%以上)。学者拉莱赫·哈利利(Laleh Khalili)为最近再版的《鱼的故事》撰写了序言,她指出,这些船只上的海员面临着被遗弃、被不在场的雇主抛弃、被海岸警卫队拒之门外,或是“被留在海上,没有燃料、电力或饮用水”的巨大风险。
如果说海洋在可见性的边缘闪烁——如塞库拉所言,“它被铭记又被遗忘,始终与死亡相连”——那么海上无产阶级也是如此。海员和码头工人是《鱼的故事》中的集体主角,作品描绘了他们在面临自动化、港口关闭、工会密度下降以及其他职业危害的代际斗争中的苦痛。比如,1990 年 11 月,艺术家前往巴塞罗那,会见了码头工人合作社“La Coordinadora”的成员,他们设计了一种抽签系统来分配工作,从而打破了基于资历的等级制度,确保所有成员都能得到一定的报酬。一张特写照片展示了工人的抽签工具:木质代币,每个代币上都有相应码头工人的编号,以及一个用来抽签的简陋葫芦。这种DIY系统背后是一段更长的历史,塞库拉指出:在二十世纪初的革命动荡中,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曾设想建立一个“由各国海员和沿海无产者组成的庞大无国籍协会,称之为‘海洋工业共和国’,或者是工人的‘七大洋专政’”。受这一劳工激进传统的启发,他拍摄的“La Coordinadora”的照片捕捉了码头工人对资本主义抽象化的抗拒和颠覆,并将他们的团结表现为一个民主集合体。

在其他章节中,《鱼的故事》讲述了无产阶级的困境——尤其是题为“中段航程”(Middle Passage)的章节,记述了塞库拉1993年乘坐“海陆质量号”(M/V Sea-Land Quality)集装箱船从新泽西州伊丽莎白港前往鹿特丹的航行。这是船上的美国官员和船员第一次在鹿特丹新建成的ECT海陆码头(ECT/Sea-Land Terminal)靠港,这是一个自动化码头,由机械龙门起重机和计算机控制的无人驾驶穿梭车提供服务。在“海陆质量号”上,塞库拉记录下了工人们的不安情绪,他注意到,随着航运业不断收紧,工人们“普遍感到……忧郁,疲惫地等待着失业”。张贴在机房内的一张手写纸条以一首诙谐讽刺的短诗表达了船员们的焦虑:“问题?/除旗。/海陆公司真的会/使用俄罗斯员工/和越南船员吗?/ . . . 他们无法击败我们 / 所以他们会解雇我们!/ 上帝保佑美国经济。”
“中段航程”的标题唤起了种族资本主义的血腥起源,这组作品将集装箱船塑造为一座漂浮的监狱,在那儿,抵抗是在逃跑和叛变之间做出选择。在一张从集装箱舱之间异形般的缝隙内拍摄的照片中,我们看到大副爬上一排被雨水打湿的集装箱,就像翻越监狱围墙的囚犯一样。下一张照片展示了一件脏兮兮的白色连体工作服,它被扔在一扇敞开的门前的地板上,仿佛穿着它的人已经升天消失了。在这组照片的稍后部分,一张在机房拍摄的照片聚焦于一名工人的护耳罩,上面印着一句标语:“我不能被解雇/奴隶是被卖出的。” 塞库拉将这一画面与机房的另一张特写照片配对:一个来自《星际迷航:下一代》的克林贡人玩偶。这个挥舞着战棍的玩具代表船员们发出警告,承诺要以牙还牙地报复那些企业霸主。这一章让我们陷入对这个象征着孤身对抗老板的标志的思考:这是一个注定没有机会的反抗者。

如果集装箱船是一座监狱——用塞库拉的话说,是“绝对主义最后的明确堡垒之一”——那么被囚禁者如何才能获得自由?随着《鱼的故事》的展开,塞库拉似乎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记录了在韦拉克鲁斯(Veracruz)与墨西哥失业码头工人的一次谈话,其中一个人开玩笑说,他们应该招募萨帕塔主义者(Zapatistas,正在邻近的恰帕斯州进行叛乱活动的原住民组织成员)来对港口进行“财务审计”。这个提议的确切含义并不明确——我们只能靠猜来想象萨帕塔审计员会如何处理港口的账簿。而且这段故事并没有对应的照片,在《鱼的故事》中成为一段难以形象化的幽灵般的插曲。
![艾伦·塞库拉,《等待催泪瓦斯[白色地球到黑色地球]》(局部),1999-2000,墙面文字,81张35毫米幻灯片投影,彩色无声,时长13分30秒.](http://www.artforum.com.cn/uploads/upload.000/id14767/article04_1064x.jpg)
虽然萨帕塔主义者从未抵达过韦拉克鲁斯港,但他们的反抗预示了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全球反资本主义示威浪潮,即“占领华尔街”的前身。塞库拉也是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和观察者,他在数个不同的项目里都记录了这一运动,包括彩色幻灯片装置《等待催泪瓦斯[白色地球到黑色地球]》(Waiting for Tear Gas [white globe to black], 1999–2000)。这组群像记录了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抗议活动上的示威者——也被称为“西雅图战役”。终于,自请上阵的资本主义审计员们来了,他们直面被军事化的街道上的警棍和催泪瓦斯弹,他们的口号借鉴了恰帕斯州的运动。2013年8月,在谋杀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的凶手乔治·齐默尔曼(George Zimmerman)被判无罪释放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几周后,塞库拉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如果他活得更久一些,他或许会为2020年六月节发生的码头工人罢工行动感到欣喜,这次罢工导致美国29个港口关闭,以声援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抗议。资本主义和帝国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仍是一个不透明的企业,被钢铁和沉默所包围。即便如此,一个民主幻影——安那其的“七大洋专政”——仍呼之欲出。
由威廉·埃尔南德斯·吕格(William Hernández Luege)策划的“艾伦·塞库拉:鱼的故事”正在明尼阿波利斯沃克艺术中心展出,展期持续至2024年1月21日。
文/ 丹尼尔·马库斯
译/ 冯优